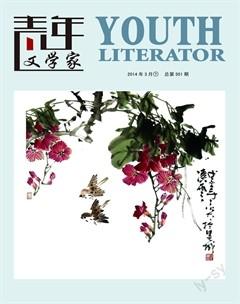花开并蒂 各表一枝
杨瑞
摘 要:对孟浩然的研究历来都倾向于把他归为“清淡”一派,但细细研读孟浩然的诗歌,我们常会发现他的感情并不平淡。平静的外表下流动着飞扬的意兴, 清淡的意象中贯注着狂放的情感。这种二元统一,恰似尼采笔下节制宁静的日神精神与奔放升腾的酒神精神的统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多元立体的盛唐“隐逸诗人”的形象。
关键词:孟浩然;日神精神;酒神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9-00-02
一
当我们用尼采的日神酒神二元理论研究孟浩然诗歌时,首先应当明确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涵义。在尼采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中,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是一对核心概念。他曾说:“《悲剧的诞生》是我的第一个价值重估:我借此又回到了我的愿望和能力由之生长的土地上。”[1]二者都植根于感受者的情感本能,却不为人的理性所支配。酒神精神是对人生原始苦难的承担和体认,表现为狄奥尼索斯式的沉醉。日神精神是在静观中把苦难的人生幻想为光辉明丽的形象,表现为阿波罗式的梦感。日神精神产生造型艺术,它通过完美形式的展现,肯定个体存在的价值;酒神精神产生音乐和抒情诗,它展现原始意志的本质——在个体的不断毁灭和再生中展現生命的永恒力量。尼采认为人生从本质上说应是一出悲剧,他在解释古希腊艺术的起源时强调,希腊人之所以需要以奥利匹斯众神形象为主要内容的史诗和雕塑艺术,是为了给痛苦的人生罩上一层美丽神圣的光辉,从而能够活下去;之所以需要激发情绪陶醉的音乐和悲剧艺术,是为了产生超脱短暂人生、融入宇宙大我的感觉,从而得到一种形而上学的安慰。在两种情形下,人生的悲剧性都被默认为前提。而酒神精神的本质就是生命力的勃发,用生命力的蓬勃兴旺战胜人生的悲剧本质,这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从孟浩然的人生际遇来看,他的一生无疑是一出悲剧,而他的诗歌艺术风格恰恰是把强烈的感情流借助宁静疏淡的意象表现出来,通过这种二元统一形式,在激烈的感情漩涡中保持克制。以此,今人论孟浩然诗, 经常征引“冲淡中有壮逸之气”的评语[2]。我们欣赏孟诗的平淡率直,但在冲淡的意象、简约的手法中蕴含着诗人饱满的情感、飞扬的逸兴。这恰恰就是孟浩然诗歌中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统一的体现。
二
翻看孟浩然的履历,无论是“数入京都”还是“隐逸襄阳”,他的用世之志都是无可辩驳的。“冲天羡鸿鹄” [3]“忠欲事明主”,还有其名篇《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人以开阔的胸襟、雄浑的笔力抒写秋日洞庭撼城动地的气势,诗歌意境开阔, 映照出创造者的博大胸襟。“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斗丽搜奇者尤众……未若孟浩然‘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 则洞庭空阔无际、气象雄张如在目前。[4]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诗人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的努力也不能被否定。
在孟浩然身上,他的那一股进取精神,丝毫不逊于李白,那对于生命升腾的渴望,亦不输于其他任何一位豪放诗人。且看《早发渔浦潭》中的“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以及《送告八从军》中的“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被誉为“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以清言目之”,处处洋溢的开阔壮远之气正源于诗人本身的进取精神与豪迈情怀,即使是在失意时仍能“壮怀激烈”。在孟浩然身上,痛苦已经成为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面对苦难所表现出的情怀正是他昂扬生命力的体现。生命力取决于所承受的痛苦的分量,生命力越旺盛的人越是在大痛苦袭来之时格外振作和欢欣。英雄气概就是敢于直接面对最高的痛苦和最高的期望,与人生的痛苦抗争。“笑一切悲剧”,酒神精神才能真正地从哲学层面流溢到人生的舞台上来。华兹华斯曾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情感的饱满源于内在生命力的勃发,这种精神恰恰与酒神精神的内在律相契合,那就是:肯定人生,连同他的悲剧性,实现个体痛苦的超越。
三
如果说,直言其志的诗歌体现了孟浩然内心强烈的酒神精神,那么诗人在际遇坎坷时的愤懑之作就更能体现两种精神在他身上的统一。《宿庐江寄广陵旧游》系怀友之作,其中也流注着羁旅异乡的客愁。“山唉闻猿愁,沦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猿啼之哀,江流之急, 风拂木叶,月照孤舟, 四句景烘托出一种浓郁的悲愁氛围。人们往往引这四句作为孟诗“清淡”风格的代表,大概仅就写景而言,未曾考虑到其中浓烈的悲情。用“愁猿”“急流”“孤舟”等意象表现的离别之愁,开头稍稍用力,而后半段诗歌恰似与友人谈心一般,丝毫不见用力,却隽永深长,意境高远,这正是日神精神对于形式和谐的考量。而从孟浩然最具代表性的田园诗看,其语言更是清逸非常。清翁方纲曰: 读孟公诗, 且毋论格调, 以其清空幽冷, 如月中闻罄, 石上听泉, 举唐初以来诗人笔虚笔实, 一洗而空之, 真一快之!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 把酒话桑麻!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都不事雕琢, 娓娓道来, 宛若口语, 写得俨然如画。此之谓平常的句子,却显出不平常的诗意,着实达到“淡到看不见诗的境界”。在一片明丽光辉的诗境中,诗人潇洒豪迈的一面亦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创造一种意象玲珑的审美世界,这便是日神精神的体现。
在情感与形式的统一中,两者绝不是平分秋色,正如在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二元统一中,“酒神最终占了上风”。“孟浩然的诗常常是静掩盖着动, 动是诗的基调。”[5]这样的诗清而激、峭而劲, 暗流奔腾的酒神式情感借助日神和谐形式的反作用力喷薄欲出。“酒神说着日神的语言,而最终日神说着酒神的语言”,[6] 这是在肯定两者在悲剧艺术中的作用,而在孟浩然的诗歌中,酒神状态的显露和形象化,但是借助于日神的手段而已。孟浩然正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看似冷静淡泊的外表下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情感。“孟浩然是一个不掩饰感情也不节制感情的诗人。杜甫《遣兴》说他‘作诗何必多, 往往凌鲍谢,将他比为鲍照和谢灵运, 看来并非泛泛的推许。”[7]
四
孟浩然的一生有着强烈的悲剧性,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完全内化统一从而达到超越。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是在承认人生悲剧性的前提下,如何肯定人生的问题,最终实现人生的超越,但孟浩然似乎在遇到人生挫折之后便把人生付于了放纵。“孟浩然的人生悲剧正在于,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出仕与归隐,他都找不到一个安顿心灵的居所。”[8]在他身上,固然有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相统一的一面,但他的放浪任纵至多只是仕途失意后的愤激与不平,这样的人生必然会在悲苦中消解,难以感受到从痛苦深渊中升腾起的生命之大欢欣。在《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中,一方面是“尝读《高士传》,最喜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一方面是“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十上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诗人反思自己半生的所为, 在理性上认同了陶潜的选择,但这种反思是在“栖栖徒问津”归来之后面对失意的压力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是暂时的, 未能形成理性的调节身心的力量。欲进不能, 欲退不甘, 他的心情始终在矛盾状态摆动,为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对于人生悲剧的超越性,雅斯贝尔斯指出:“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9]实际上,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超越”,就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悲剧英雄与一般人的差别仅在于“进行纯粹的存在观看的努力”的程度,亦即取决于对现实是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还是采取超越的态度。“最富精神性的人们,他们必须首先是最勇敢的,也在广义上经历了最痛苦的悲剧。他们正因此而尊敬生命。”[10]在孟浩然的悲劇人生中,他没能成为悲剧英雄,最终湮没于个体的痛苦中未能实现超越,让后人为之遗憾。
参考文献:
[1]尼采著,周国平译:《偶像的黄昏·<我们应该感谢古人什么>5》,《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修订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贻焮:《孟浩然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版.
[3]佟培基:《孟浩然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凡引孟浩然诗, 均据此本.
[4]吴文治:《宋诗话全编》[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刘文刚:《王维与孟浩然诗歌艺术比较》[M].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6]熊希伟 译:《悲剧的诞生》[M],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7]孙学堂:《孟浩然诗情的浓与淡—兼与王维比较》[J].兰州大学学报第33卷第6期,2005年11月.
[8]蔡阿聪:《孟浩然的性格与其人生悲剧的关系》[J].中州学刊2004年3月第2期.
[9]雅斯贝尔斯著,亦春译:《悲剧的超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10]尼采著,周国平译:《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17》,《尼采全集》第8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