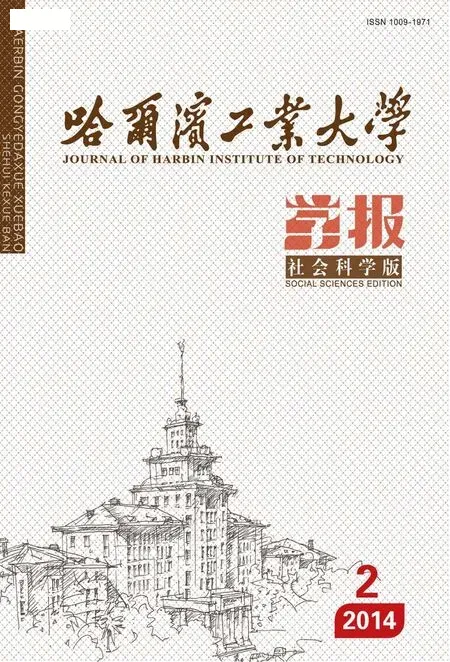异质性社区的社会交往与社区认同
——北京沙村的个案研究
狄 雷,刘 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异质性社区的社会交往与社区认同
——北京沙村的个案研究
狄 雷,刘 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通过对北京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田野调查,基于本土居民适应的视角,讨论分析了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在共居状态下日常交往的内容与层次,并进一步阐述了外来移民对本土居民的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以及社区认同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在客观层面还是主观认同上,“社会距离”真实地存在于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社会交往中;同时,由于与外来移民打交道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本土居民之间的互动和社区参与受到制约,邻里社会资本这类传统的社会连接纽带遭到破坏,本土居民的社区认同与归属感降低,社区整合与秩序受到了挑战。
流动人口聚居区;共居;日常交往;社区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与影响,这类特殊群体只是城市的“过路人”[1]、“准市民”[2]状态。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群体具有典型的“边缘性”特征:一方面,他们被局限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属于非正规就业,其表现形式为临时工[3];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居住地的选择需要同时考虑经济上的可负担性和文化上的融合性,因此城市边缘地带的租赁房屋便成为他们落脚城市并开始城市适应的首选之地[4][5]。在很多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本土居民出于利益而积极地开展房屋出租,吸纳了大批的流动人口,这些传统的农村社区逐渐转化为异质性的流动人口聚居区。
从社会交往的视角考察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与融合问题一直是社会学与人口学的经典问题,大多数的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的研究方式,从“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的概念出发,讨论和分析影响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社会交往的因素[6]。这些研究认为,由于流动人口还没有实现向城市居民转变的“本质城市化”,所以在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距离”。这些社会距离客观的体现出流动人口在所居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和他们的市民化、城市化水平。
上述研究有两方面的不足:首先,他们在研究中一般都借鉴了鲍格达斯(Bogardus)的社会距离量表,将社会距离视为主观变量,如将“社会距离”操作化为“本地居民是否愿意与农民工交友”[7]。然而,这一概念测量的是人们的交往态度或意愿,而不是真实的交往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被调查的城市居民即使表现出交往态度和意愿,也很可能没有与外来移民有过接触与交往。上述研究对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交往情况缺乏细致的考察。其次,这些研究主要基于流动人口适应与融入城市生活的单一视角,事实上,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实际的社会交往是一个双向的互动与适应过程,流动人口在城乡结合部地区的空间聚集,也对本土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本土社区的社会整合带来影响和冲击。
基于社会交往的研究视角,本文通过对北京郊区一个异质性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田野调查,刻画了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日常交往的内容与层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外来移民的进入对本土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对社区的认同与整合问题所提出的挑战,并进一步对异质性社区的本质进行讨论。
二、研究资料的获取过程
产业的扩散、土地出租目前成为沙村村集体的支柱产业,商业服务业的活跃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到这里来寻求机会,本土居民逐渐将自有的住宅出租给外来移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市沙村出现了零散的出租户,到2008年,75%左右的村民开始出租房屋,随着房租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沙村村民开始充分利用自家的宅基地建房甚至盖楼出租。出租房屋村民与可供出租房屋数量不断增加,增加了对外来人口的容纳能力,沙村逐渐转化为一个异质性的流动人口聚居区。
本项调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08年1月对沙村房东和外来租户的摸底调查,收集了本地住户问卷168份、外来租户问卷489份;二是问卷设计前的试调查,对16户外来租户和5户本地住户进行了结构式访谈;三是正式的问卷调查,共收集本地住户问卷119份、外来租户问卷203份。文中的数据来自课题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对本地租户的问卷调查;访谈材料主要来自第二阶段对本地租户的结构式访谈。
三、“共居”状态下的日常交往
在沙村,由于本土居民主要利用自有住宅的空房进行出租,这意味着房东与房客处于一种共居状态,即在一个居住空间内共同生活,因此沟通互动就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作为房东的本土居民的家庭生活与日常交往在很大程度上都变得与租房相关,房屋出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时间安排与活动空间,这对房东的作息时间、公共社交生活的参与度及家庭生活的完整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租房契约达成:互动的开始
租房契约的达成,是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最初接触和沟通的开始。契约达成本来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对于房东来说,是愿不愿意接纳这个房客,而对于房客来说,则是接不接受房东条件,包括房租、其他费用和居住规定等。在调查过程中,笔者了解到,绝大部分房东和房客之间没有书面合同,双方基本上是一个口头的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房租、水费、电费等费用分别是多少,什么时间收取,住在本家应该遵循什么规定等等。在和房客达成契约后,房东一般会对房客做一些交待。
由于沙村租房市场的透明度较高,房租价格也是相对公开和透明的,所以租金和费用问题,在契约的达成过程中不是问题。可见,租房契约的达成过程,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房客口头上接纳房东所提的房租、费用条件和入住规定的过程。同时,与房客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在沙村比较少见,大部分房东认为签合同没有用,因为如果房客不给房租了,房东也不会让房客继续住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房东一般都会收取一些押金。比如,HH家会收房客200元押金,住满半年退100元,住满一年退200元。另外,如果房间有损坏,房东也会扣下这部分押金。
出于安全的考虑,房东一般会记录下房客的基本信息,如籍贯、年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等,同时,房东会主动对房客进行筛选。在正式的问卷调查中,我们询问了房东最愿意接纳的房客类型与最不愿意接纳的房客类型,数据显示,村民最愿意接纳的三类房客是白天上班族、小两口家庭和带小孩的小家庭,分别占总比例的41.9%、34.2%和16.2%。这三类房客在村民心中都是相对安全的人。另外,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房东倾向于选择那些收入稳定、不吵闹的人。村民不愿意接纳的房客类型是:来自特定地区的租房人(如河南、新疆和东北人)、单身房客、酗酒者、无固定工作者、暂时失业者和蜗居者(整天呆在家的)。在沙村村民看来,这类房客是潜在的危险人物或麻烦制造者。可以看出,对于外来者,本土居民有较强的戒备心理,并排斥特定类型的外来者。
(二)日常交往的内容与层次
在共居状态下,房东与房客的角色定位是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最重要的关系,这是一种因租房而产生的经济契约关系,双方其他的日常交往,都是在这个关系之上发展起来的。在问卷调查中,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四分类的互动模块用来测量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日常交往情况。
在双方的交往中,诸如聊天等日常互动是这一共居状态的伴随性产物,这些表面层次的互动、互助是维持双方间的契约关系所必须的,除此之外,双方缺乏更深入的交往及情感交流。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日常交往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社会交往的表层性上,他们之间缺乏深入交往的支持点。
在心理层面,绝大多数的沙村房东都不愿意与自家的房客交往太深。在问卷调查中,对于“我觉得应该和房客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这个问题,有90.8%的房东选择了肯定的回答;换句话说,绝大部分沙村房东都认为应该与房客保持一定距离。可见,即使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区,并拥有大致相当的背景知识,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仍然因其在契约关系中的地位不平等而在日常交往中存在“社会距离”。在调查中,笔者还发现,在很多房东家庭中会有一个“内门”,居住空间的进一步分割把房东的生活世界和房客的生活世界切割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会对房东与房客的互动频率和交往程度产生影响;同时,内门是一种符号,不仅是房东采取自我保护策略的一种象征,同时也表征了房东对待房客的一种态度——房客是被防范的对象。这对房客也有一定的心理暗示作用,这种心理暗示也会影响房客与房东的交往主动性。
这种日常交往的局限性是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房屋出租的契约关系决定了双方很难深入交往,或很难发展成为一种亲密关系,为了维持这种契约关系,最好就是“公事公办”;其次,如前所述,沙村村民在做出租房决策的时候,大都有安全方面顾虑的,所以他们本能地会对房客有一个戒备心理,这也妨碍了房东和房客的深入交往;最后,在访谈中,笔者发现,随着房客数量的逐渐增多,会影响到房东与房客间的交往,例如,HH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在盖楼前,HH家只有6户租户,而且房东与房客共处于一个院落内,对彼此的活动都能看得见、听得着,因此,那时候与房客的关系比较亲密;在盖楼以后,房客人数增多了,有20多户,房东很难和每一户都很亲密,按照女房东的讲述,是亲密不过来了。
(三)房东对房客日常行为的管理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同样测量了房东对房客日常行为的管理状况。

表1 房东对房客日常行为的控制力和管理概括(N=119)
如表1所示,对于大部分沙村房东来讲,是否“在意房客太吵闹”等问题,绝大部分房东都选择了“同意”的选项。也就是说,房东对可能破坏家庭生活安宁或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的房客行为都非常在意,并会积极的加以约束。
同时,房租管理是对房客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数据显示,69.7%的房东不允许房客拖欠房租。很多房东有没有收到房租的教训:“2008年,有一个河南人拖欠了我们家2000元的房租,一直没有还,我就扣了他一些东西并把他赶走了。自此之后,我一般不允许房客拖欠房租”(HH)。当然,房东对不同的房客,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立场,这取决于双方的了解程度和关系的密切程度。
可见,在实际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房东对房客的日常行为有着较强的约束,这也反映出由于租房契约的存在而导致双方在交往地位上的不对等性,这种约束与管理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双方发展出更深入的交往。
社会交往必须依托具体空间才能发生与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沙村的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在居住安排上处于“共居”状态,这直接影响到了双方日常交往的形式与内容。基于租房的经济契约关系,“房东”与“房客”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双方缺乏深入交往的支撑点;同时,居住空间的分割特征使得双方的社会交往呈现出闭合趋势。可见,大量异质人口在社区内聚集和共处,加深了社区内部异质性,并进一步对本土居民的社区生活造成冲击。
四、异质性社区的认同问题
毫无疑问,外来移民的不断聚集对社区的承载力、卫生、安全等都提出了挑战。在访谈中,村委会的潘主任从村集体的角度特别提到了这些负面影响:“首先,公共费用增加了,水、电的压力非常大,以前村里两三台变压器就够用了,现在每年都增容、增加变压器,这样增加了村集体的负担。其次,外来流动人口产生了更多的垃圾,每年垃圾外运与保洁费的开支就有几十万,而且村里每年都得修路、补路,每年在这方面的投资都非常大,这些都是无形中增加的。再者是治安管理,村里现在有二十多个联防队员,包括建站、设备以及工资开销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村里的社会治安也不如以前好,村风民风也不像以前那么淳朴了。”
同时,传统农村社区转化为异质性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对本土居民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HH家,女房东放弃了在小区做会计的工作,成为一个“职业房东”,家里一切和租房有关的事务都由她负责:成为职业房东后,她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作息时间的改变与行动自由的减少上。
像HH家的情况在沙村的出租户中较为普遍,房屋出租对本土居民的家庭生活与社区参与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一方面,房客数量的增多使得房租收益成为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相伴随的是与房客打交道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这对房东家庭生活的完整性与时间安排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很多房东的活动空间受到了约束,邻里间的互动以及对社区生活的参与相应地减少了。在外来移民数倍于本土居民的背景下,社区的“异质性”不断增强,使得本土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也大大降低。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对沙村村民的内部团结程度和社区认同感水平进行了测量,结果如下:
在对本土居民当前社会团结程度的测量中,设定1分代表“沙村人越来越团结了”,9分代表“沙村人越来越不团结了”。数据显示,只有27.7%的村民认为本土居民越来越团结了(选择1—4分者合计比例),有47.1%的人认为沙村人越来越不团结了(选择6—9分者合计比例),这表明了沙村人的团结程度在下降。在访谈中,很多村民都表示沙村人不如外地人团结。伴随着租房市场的发展,本土居民提供产品的同质性使其在租房市场中形成了竞争关系,相互之间日常交往的减少削弱了邻里社会资本,传统的社区连接纽带受到挑战。
在对社区认同感的测量中,设定1分代表他们认为“沙村已经是外来人的沙村了”,9分代表他们认为“沙村还是本地人的沙村”。数据显示,有33.6%的本土居民认为沙村已经是外地人的沙村了(选择1—4分者合计比例),而另有63%仍然认为沙村还是沙村人的沙村(选择6—9分者合计比例)。可见,沙村村民在对沙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上出现了分化,本土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危机。可以说,随着沙村逐步转化为一个流动人口的聚居区,其作为一个边界清晰的本土社会的地位受到了冲击。
五、结论与讨论
传统上关于城市化进程的微观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外来移民在城市社会的适应问题,而对外来移民对城市社区所造成的冲击以及本土居民的适应问题则缺乏相应的关注与讨论。本文通过对北京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田野考察,基于本土居民适应的视角,讨论分析了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在共居状态下日常交往的内容与层次,并进一步阐述了外来移民对本土居民的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以及在社区认同上的影响。
在本文的案例中,本土居民开展的租房实践以及外来移民的不断聚集,促使沙村从一个传统的农村社区转化为异质性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在共居状态下,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首先是房东与房客的“纯化”关系,基于这种租房契约关系,双方的日常交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呈现出表面性的特点,缺乏深入交往及情感性交流,这种表面性的交往维持双方契约关系所必须的,因此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而且,由于双方在契约关系中地位的不对等,本土居民在心理层面也不愿意同外来移民深入交往。可见,无论在客观层面还是主观认同上,“社会距离”真实地存在于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社会交往中。同时,在多数沙村的家庭中,与房客打交道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对他们的其他社会活动形成了较强的时空约束,相应的后果是,本土居民的邻里互动和社区参与减少了,邻里资本这类传统的社会连接纽带遭到了破坏,降低了本土居民的社区认同与归属感,这对社区整合提出了挑战。
沙村外来移民数倍于本土居民,并在居住安排上与本土居民处于共居状态。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类型,沙村在社会属性、区位分布、居民构成等物理表象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边缘性和异质性。更重要的是,人口构成的异质性与高流动性对本土居民的家庭生活与社区参与造成了冲击: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交往停留在非人情化、表面化的层次,对于双方来说没有发展出新的邻里社会资本;相反,本土居民间的邻里互动和社区参与减少了,邻里社会资本作为传统的社会连接纽带遭到了削弱。也就是说,居民构成的异质性使得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以及本土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本身也具有异质性的特点,即传统社区整合机制遭到了破坏,新的社区整合机制还没有形成,这是流动人口聚居区作为一个异质性社区的本质所在。在实践层面,对于异质性社区的社会管理问题,也值得人们进一步关注与研究。
[1]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107-122.
[2]朱力.准市民的身份定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6):113-122.
[3]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J].社会学研究,2002,(6):13-25.
[4]吴晓.城市中的“农村社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现状和整合研究[J].城市规划,2001,(12):25-29.
[5]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2,(3):92-110.
[6]郭星华,储卉娟.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江海学刊,2004,(3):91-98.
[7]王桂新,武俊奎.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1,(2):28-47.
Ordinary Contacts and Community Identities of a Heterogeneous Community:An Empirical Study of Sha Village,Beijing
DILei,LIU N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Through the field work at a popular site settlement for lower class,and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local residential adaptation,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ontents and level of ordinary contacts between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migrants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co-habitation,and then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migration on the local citizen's daily life,social contacts and community identities.The research result indicates that social distance does exist between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migrants both in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layers.For the local residents,contactswith themigrants has become the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everyday life,therefore the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local residents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has been restricted so as to destroy the tradit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local community and reduce the community identity of the local residents,which brings in a great challenge to community integration.
Site of Settlement for Lower Class;Co-habitation;Ordinary Contact;Community Identity
�献标志码:A
1009-1971(2014)02-0025-05
[责任编辑:唐魁玉]
2013-06-12;
2014-01-12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外来流动人口城市适应模式和社会控制对策研究”(06AaSH001)
狄雷(1981—),男,山东莱芜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城市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刘能(1970—),男,浙江舟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