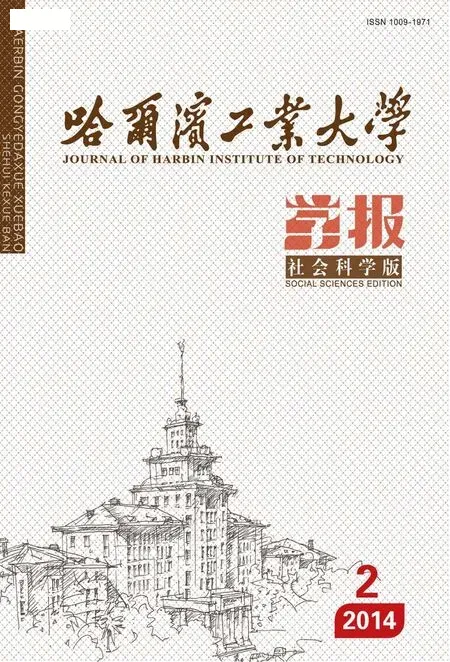对生命资本的伦理审视
于江霞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生态文明建设·
对生命资本的伦理审视
于江霞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人的肉体存在为关注起点,以异化为中心概念,以对物质性与抽象化辩证关系的考察为重要方法,对资本进行了一场深刻的伦理批判。伴随着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由于资本更多地投向身体,“生命资本”这一原本隐而不显的资本形式日渐突出而重要,并可能导致愈加深层的生命异化状态;这就需要从“身体”反观资本——对资本的抽象物进行物质性还原,并以一种强调身体在场性的伦理,尤其是将资本和技术具身化的伦理,对生命资本进行有效的伦理规约。
劳动;异化;生命资本;伦理
随着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兴盛和科学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个普遍的社会和思想共识是,身体已经更多地由劳动的身体转向欲望的身体,由生产的身体转向消费的身体;身体由此成为当前资本投资和利润生产最重要、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进而最大程度地延伸了现代经济活动的空间。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以资本和技术作用下的肉体存在为关注起点,以异化为中心概念,以对物质性与抽象化辩证关系的考察为重要方法,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资本批判,同时亦是一场围绕生命之存在境遇的伦理批判。其核心关注则是如何将感性的人从泯灭人性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赋予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并复还劳动以自由本质,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高度统一。由于在市场经济、生命科学和消费文化所表征的现代社会,身体成为价值创造与知识生产的共同源泉,一种本源地秉有强烈伦理性的资本形式,即“生命资本”正日渐突显,因而有必要将马克思对资本的伦理批判推展至对生命资本的伦理检视,并在整合其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比较,揭示生命本身的当下境遇及其可能遭遇的伦理困境。
马克思对劳动的反思与批判是《手稿》资本批判的核心要义。劳动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以及工人这个靠抽象劳动为生的“肉体的主体”。资本在运动中贬低了人,却造就了工人这种会劳动,但仅存最低肉体需要的动物[1]19,一种作为贫困的可变资本的奴隶。由于劳动是人之生命的根本表达,而生命已沦为商品,因此劳动的异化即是生命的异化。显然,劳动异化学说是基于社会的、历史的人的肉体性存在而展开一种类似现象学的考察的。作为自然现象与社会产物的统一体,身体是人之存在的基础,是人占有自然的条件,也是劳动异化的前提。
实际上近代以来,除了政治经济学,生物学(拉美特利)和哲学(笛卡尔)等都致力于从不同角度将身体规定为机器。因此,身体的机器之喻并不是思想家主观设计和想象的结果,而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客观现实的真实揭示。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总体诉求下,这种现代医学式的身体观念是反抗神权的需要,是科学理性的体现,更是资本的逻辑要求。以增值为本性的资本已被社会普遍奉为最高的、无条件的善,但在理性及其制度建制的辅助下,这种最高善只是在禁锢欲望与激发欲望之间游移却永远不提供人之内在目的。作为积累的劳动,或人感性力量的集合,资本本质上只是一种以具体的物为媒介的社会关系,一种对现实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1]21。因此在追求不断增值中将人、技术、机器和工业都抽象化,以物的关系代替人的关系,并把丰富的人的世界抽象为可以估算的符号世界,是资本的本性使然。正是资本这种扩张和增值的本性推动其摧毁一切文化、地理、身体的障碍而将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资源抽象化、祛魅化,同时作为“一切纽带的纽带”而将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界联接起来[1]143,并在此过程中作为一种“普照的光”[2]将一种多重异化状态最大程度地普遍化。
一、从资本到生命资本
当身体成为资本的积累场所和作为交换对象的商品,尤其是当生命沦为生存的手段而不再是存在的意义来源,生命就成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即我们要讨论的生命资本。马克思在批评国民经济学试图设定资本与劳动的统一时也提及“生命资本”一词[1]127,但生命的资本化趋向却由来已久(例如卖淫、贩奴等等),并逐步与生命的技术化互为补充。尤其是自从与资本开始联姻,科学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的发展更是不断地为生命资本开辟新的生长空间。所谓的劳动异化既是劳动与自身的对立,也是生命与其本身的对立。这种对立首先表现为对身体超越道德和自然界限般的摧残;而直接造成身体退化之命运的却是代表人的智力的技术。鉴于技术发展对资本增值的显著作用,资本要抽象化、合理化,进而占有、利用和异化科学,使之成为自身的附庸。马克思关注的对象无疑还主要是机械技术,它将工人的身体活力做一种机器化的运用,并在实质上剥夺工人的身体而使其为资本所有,为他人所有。而在今天的生物经济领域,资本主义正在一种资本、技术与权力空前结合的社会建制下,将身体变得更“生物”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将身体向机器化开放,并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为工具而围绕生命本身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造与重组。现代生物技术不再满足于对各种身体的外在整形和操作,而是试图通过对生命内在机理的控制和身体材料的再生产,创造远离自然性的技术化身体,满足人们对身体之善的无限欲求。正是这种以“生命”为直接客体和主体的新科学促使身体的空前商品化,即生命资本的衍生成为可能。
毋庸置疑,随着资本运行条件的改变,劳动的异化色彩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所淡化;但随着劳动的含义、形式的重新界定以及资本积累策略的不断变化,在生命科学领域,生命的资本化趋势却矛盾地日趋增强——生命本身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活劳动。一方面,鉴于今日消费社会对身体的崇拜、对健康的迷信、对快感的期待,身体、尤其是生命的植物性部分和动物性部分的美与善成为至上的关切,从而为资本物化欲望而占有身体并将其作为投资场所,以进一步作为资本的某种形式去赢得各种社会资本而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生命科学的进步使身体成为有待开发的新的无主地,并在某种意义上用“技术”重新定义了“生命”,由此改变了人们认识自我、组织社会的方式。借助对人体材料的所有权、提取技术、存储能力、再生产机会和人体的文化建构,以及产权、阶层关系、主体性、人格和认同意识等方面的实践活动,今天的资本主义欲将生产关系概念推展至一切有生命之物,即通过对基因、细胞、组织、器官、胚胎等各种身体物质材料进行提取、再生产、商品化,以纳入到资本的流动和运转过程[3]298。如果说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剖析主要以整全的身体为言说或考察对象(尽管是非完整意义上的人——如动物、奴隶般的工人),那么生命科学则进一步将部分的身体变为资本的投资对象。新的生产方式对身体部分的分离、买卖和杂合,使内在身体与外在身体的界限日渐模糊,整体身体和局部身体、不同种群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进而使身体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表现出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对象化和类生命的异化。而且,这种异化随着科学技术对身体不确定性的推进,即对身体和机器、人和动物、男性和女性、健康和疾病、活的身体和死的身体、真的身体和假的身体之间边界的打破还将日趋深刻。
总之,资本已经深入人体的内在机理,并将被视为蕴含身体一切秘密的、作为生命基石的基因同化为与自身相仿的另类神物。身体,即马克思视域中的劳动机器再次以崭新的形式,即基因机器的形式而存在。生命成为基因的载体和奴隶:身体不过是决定其机能与外观的基因的生存机器,或基因运输资本的一种媒介。因为生物技术已赋予遗传密码一种资本化的功能,生命的世界就是资本所控制的编码和计算的世界。作为信息载体的身体因此成为知识的重要对象,而知识就是资本,一种作为生命权力的资本。为资本积累而圈地、殖民与侵略既是资本的真义,也是资本扩张的主要方式。鉴于资本与基因的同一关系,以基因、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为对象的“基因圈地”在基因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的推动下,也就因此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由于基因资源与资本的分布往往成反比,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形式的灵肉较量,即“头脑国家”与“身体国家”的奇异划分,而这种对立某种程度上可视为马克思笔下的工人肉体与智力间对抗的自然延伸。
这种以直接的生命本身的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称为生命资本主义,在此生产过程中还会产生出一种与劳动价值相对应的生物价值,以及一种与生产关系相对应的所谓的生物社会关系。随着神从天空降落至实验室,掌握生命知识和操纵生命命运的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和生物企业必然被赋予相当的“生命权力”,从而与通过市场而卷入的国家、捐赠者、中介机构、消费者等众多主体,共同塑造着一种新的生命政治。尤其是当采取一种更广泛的视角,考虑到全球生物医药和食物,包括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人的身体,将不仅仅是通过分割、交换、重置而被层级化地卷入,而且还会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生产体系的对象——全球性的身体工厂[3]300。更有甚者,由于身体的自然基质和能力都成为生产工具,人类的劳动概念必然要重新界定,甚至动物是否参与劳动也需重新考虑。
二、对生命资本的伦理考量——以器官交易为例
对这种以“生命”为资本的生命资本主义的现在与未来,出现了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两种基本论调。理想化的生命资本主义确实为人们预设了一种丰富、促进和优化生命的乌托邦前景,进而为满足人们的身体理想,获致某种优良生活开启了更多可能性。而在现实生活、尤其西方社会中,身体优化、身体话语、生命计算等的充斥与盛行似乎也确证了某种与生命资本主义相呼应的身体文化。然而,生命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图景却可能是一个以风险、暴力和自我毁灭为特征的乌托邦。资本对不断扩张的医疗卫生体制的全面控制,使其可以根据利润需要而设定新的健康标准和疾病分类,并且规定着科学研究的方向、目的和建制,从而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不公的鸿沟。推而广之,资本与技术对生命的物化、客体化,还可能消解生命的自主性和开放性,无可挽回地扰乱生物圈的基因秩序,从而将人与自然置于更大的历史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之中。而对人本身来讲,生命的同质化和商品化,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重构还会引起空前的主体性恐慌或身份危机。在《手稿》中,马克思曾以人与动物、自然与文化的厘分来突显人的类本质,但异化劳动却使人的自由活动沦为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进而使人的机能与动物的机能相互倒置并剥夺掉人丰富而全面的本质。强调类的分界以及人感性存在的基础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淖或者类存在与个体存在的二元悖论,毋宁说其初衷是在人与动物的比较中追寻特定生产条件下的异化根源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而现代生物技术则试图通过对身体的分离与重置,将人转化为一种分子层面的存在,使作为人之类本质及其实现的劳动变为一种细胞的、酶促的或遗传的活动,以模糊和消释其类意识和类概念,同时将用于生物医学实验和人体器官移植等动物的生产引入新的生产关系中。这样动物的活动似乎就不再是简单的生产自身,而是为人而生产身体,但又区别于满足人之口腹之欲的生产,尽管同样是被置于一种绝对的、有意识的宰制之下。
总之,动物—人—神秩序确实正发生某种变化:在科学所塑造的万神循迹和万物祛魅的新世界,原与自然界脉脉相通的人试图通过对生命本身以及生命间关系的重构而确立一套新秩序。但充当世界主人的梦想却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基因结构所标示出的人物之间界限的模糊性,使如何界定、寻找人的类本质及其导致人兽之分的隐秘领域这一形而上学冲动更加迫切。只要人的理性还不因某种生物学原理和计算机程序的影响而被外在地规定,或许我们就可以用康德的方式回答:道德法则是确证自由和赋予自由的存在者以客观实在性,并将其从感性世界或机械世界超拔出来而进入超感性世界的唯一可能,人的道德存在是世界的最高或终极目的,因此我们应该诉诸伦理和道德力量,即通过一种伦理的“应该”来规约“是”的现实,以新的道义论来合理化新的“创世纪”进程。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种伦理的生命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伦理政治和伦理技术。
或许由前沿生命科学所描绘的生命资本主义图景对于一般人来说虽不遥远但并不切身,但总体上以身体为重要对象的经济现实,确实不断挑战着社会秩序和伦理底线,并使权力的扩散、滥用,以及伦理关系的重构成为可能。全球范围内的器官交易无疑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证。
“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1]66,由于无法负载生活的重荷,一种建立在技术许可、资源有限和市场需要基础上的,以维持肉体生存和生活必需的器官交易,就成为一些贫困者的无奈选择。因为身体是最后的商品、最后的资本,它可能既代表着维持生存的最后选择,也意味着最深层的商品化过程。同样是将身体作为商品卖出,但这里出卖不是身体的能力即劳动力,而是类似剩余劳动的“剩余”身体部分。因此,资本法则对器官移植这一触及人自身的完整性和人格同一性、人与人及其他物种关系的生命和技术现象的入侵,无疑使身体的无序和生命的异化状态更为普遍和深入。
与器官买卖相关的是一种被称为“情感性劳动”的付出。情感性劳动的商品化与马克思所言的为工资而出卖劳动力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种劳动的价值却似乎很难量化。然而使包括生命本身的一切“有价值物”可量化、可计算化却是资本的要求,只有定量化的价值才使得交换成为可能。而资本不仅要对情感世界进行全面入侵,而且还试图将这种情感成本外部化。所以器官买卖不只发生在个人以及包括医院的各种中介组织之间,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地区、民族、国家等不同经济实体(主要体现为落后国家为西方国家提供身体器官)之间,而后种情境往往更为复杂。因为在身体及其器官的商品化过程中往往还伴随着种族、文化观念的输出,阶层、种族、性别和体能等方面的分离使穷人或脑死亡者、甚至犯人等不同人群的身体器官呈现出进一步的层次性。由于资本既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文化实体,因此它甚至可以将情感性劳动所作用的自然身体所带有的文化印记都标以不同价格,以使器官交易在拥有不同身体观的地域文化间畅通无阻。
将一切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抽象和颠倒是资本的魔力所在;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超越和替代,个体生命在强大资本链条前的渺小和无奈,在器官交易中体现得尤为深刻。在目前最为频繁的肾脏交易中,买者通常以一种“当我能买一个肾,为何还要让一个家庭成员冒险”的态度而拒绝承认或无视别人的牺牲,尽管这种态度发生于人之自然本性,但客观上却使他人的身体作为一种例外而处于一种类似“牲人”(尤其是死囚)般的存在。科学则宣称第二个肾是“剩余的”[4]器官从而为商品化、为资本开路。有些医院更是将器官交易视为一场不同身体与医术、货币之间的游戏,利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其掌控的医学知识,助推某些非法的器官买卖或将无偿捐献器官变为有偿器官交易而从中牟利。当然操纵整个链条的主要是各种中介者,正是他们为生命资本的顺利实现而扫清了一切伦理关系、肉体关系上的各种障碍。而缺乏法律保护和相关知识的卖肾者本人却在某种程度上沦为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即与享有法律保护和政治身份的生命相对应的,仅存动物性的、匿名的生命。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语言说,他只是如同动植物般的活着而不是作为有逻各斯的存在者。一种健康为了异化劳动的工业资本逻辑也就因此转变为一种劳动为了他人健康的生命资本逻辑[5]。总之,由于异化状态下的道德领域与经济领域是分开的[1]125,一种无责任的伦理空白状态就变得顺乎其然。
三、伦理的生命资本:一种身体的伦理?
如果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诉求理解为一种伦理调控,或许我们确实需要一种与生命资本相伴而生的伦理来规约生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伦理的生命资本如何可能,具体而言,如何平衡好生命与资本、健康与财富这双重目的,摆脱伦理善从属于财富善和健康善的尴尬状态;如何设置稳定、普遍的伦理边界,在挖掘生物技术生产力的同时降低和消解其相应的破坏力,并赋予“生命资本”以某种合理性;个体生命又如何通过伦理实践对抗资本与技术的可能暴力,并在新的生命政治中看护好自我身心等等,关键在于从生命、尤其是身体的维度来反观和制约资本及其所挟持的科学。
生物技术使生命的逻各斯确实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改变;这种新的逻各斯要求我们关注身体的在场性,并从身体的具体境遇寻找伦理的可能性。身体,包括动物、大自然的身体,对生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生命资本主要是围绕身体来实现其运动,生命本身即是生命资本的母机。但资本对伦理实体和伦理关系的抽象化,以及生命伦理学领域的形式化和程序化趋势却倾向于消解各种身体的存在,或许这也是人们通常所抱怨的道德伦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步的根由之一。但是所谓的生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和技术对身体的操控,以及由此产生的愈加不确定的身体,却驱使我们关注身体和身体问题,并在特定情境下以一种身体化的思维来应对身体的现实。这既是关心和改造身体的应然态度,也是对身体的过分投入或生命资本的过分膨胀的必要警醒。一方面,资本和科学对身体的控制和规训实际上使我们远离,进而不能直接地倾听身体;另一方面,身体的解放固然使我们有可能摆脱疲惫、疾病、衰退和死亡的肉体而使其更好地侍奉灵魂,但是这种肉体的善却不必然带来灵魂的善。相反,未加修饰的、甚至残缺的身体依然可以承载不断向善的心灵。这种直面身体的伦理态度呼唤个人在关注身体境况的同时,还应在身体的诱惑面前守住灵魂的秩序,外化而内不化。
进一步说,对身体的伦理关注实际上也体现着一种与追寻稳定不变、普遍适用的伦理准则的理智态度以及二元思维模式相对的、面对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变化而诉诸伦理的多元性、可变性以及无终点性的新态度。马克思曾批评黑格尔将生命活动仅仅做一种逻辑的、思辨的、抽象的演绎,并指出全部历史的首要出发点应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1]215,一个不单纯是智性存在或环境产物,而是连接自然与社会的、活生生的具身性存在。异化的扬弃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扬弃,而要首先面向现实的、客观的、具体的存在。生命资本或许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但至少是一种新的思考和行动方式[6],因此在检视生命资本所关涉的纷杂伦理关系时,必须对资本和理性的抽象物进行还原并深入到由资本所连接起来的各种身体性关系。根据不同身体的伦理境遇来确立相关权利和责任,其中尤为关键的就是确立资本及其所控制下的技术或知识的人格化责任。
因此追究生命资本所关联的伦理责任,并不是刻意为资本另寻某种善的本体性质,而是更多地寻求一种对身体或生命商品化的伦理规约和牵制。尽管这种伦理努力可能带有消极性和防备性色彩,但却内在于人作为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存在而意欲冲破资本强制之网的不懈追求中。在当前这样一个身体善凸显,欲望的本体性和生命的工具性空前的时代,尤其是在生命科学使对生命的重新定义成为可能,对身体的局部锻造成为经常这一前提下,资本直接或间接地对身体的操作,使身体已经成为链接经济关系、表达社会符号的重要基质和场域。如果从概念上将身体与灵魂并行论之,那么可以说身体已成为重要的问题域、问题场,尽管被各种拜物教,尤其是资本拜物教和身体拜物教充斥的心灵才是真正的问题源。正如对大地身体的侵害遮蔽了其自然的灵性,技术对人的身体的过多干预也易使其忽视空乏的灵魂。而无论是伤痕累累的大地身体,还是作为奴役对象的消费身体,都无非是资本对身体的工具性利用——资本将一切现实身体置于自己的超验身体之下而加以记录、限定、编码和标价,使自然变为贫瘠的资本,使人本身变为贫困的资本。资本的这种抽象化作用与科学的话语权力相结合,不仅可以将商品化延伸至人的身体本身而威胁生命的至上性和人格的同一性,而且还往往在流动中而将相关的责任主体隐匿起来,从而导致责任担当中的无身体现象。资本的扩张和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伦理问题,但缺少具身化的道德代理人来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由于资本和技术既无善良意志又无实践理性,而行为也不可能是脱离肉体的单纯意愿选择的产物,因此必须深入到资本运动和技术生发的特定情境,追踪资本和技术的人格化力量,即相关组织和个人的责任。而其目的则在于使生命资本服务于优良的生活样态,而不仅仅是欲望满足和利益追逐的工具。
诚然,资本控制下的技术是这种身体及其伦理转向的直接推动者。从身体修复到身体增强,技术不断超越自然限制而致力于打造变动中的完美身体;反过来,身体又是技术的对象和源泉,技术仍然要植根于物质的肉身,不断满足并创造着身体的植物性和动物性需要。身体与技术之间的这种互动和相互作用使得对身体的解放与对身体的奴役成为一个货币的两面。因此对生命资本主义绝对地拒斥和拥护或许都是不够谨慎或明智的选择,唯一可能而现实的路径即是利用伦理、政治等力量,使自发变为自觉,消极化为积极,暴力转向解放。马克思虽注意到技术对资本的依附,但他并没有因此强调技术的绝对中立性,而是把技术作为生命能动性的展示和类存在的证明——生命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科学技术的对象性和创造性活动首先应是展现和滋养生命,促进生命创造与繁荣的生命活动方式。与其说是精神和理性,不如说是技术和生产等具身性的实践活动,真正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同时历史地建构人与自然。自然(包括人的内在自然)与文化间的变动的历史关系正是在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性化的这个双向过程中得到展现的。因此从未直接面对自在自然的人类在打造自身的不懈努力中,得以不断向前推移着自然限制,冲击着自然秩序。但由于科学的推动力由最初的惊异更多地转向各种利益,从而产生了更多的伦理空白,尤其是科学认知活动并非是无身体的单纯理智产物,而是以特定情境下的具身结构与活动为基础,并通过其对象性活动对人、其他生命形式以及自然环境等的脆弱身体不断施加影响,因此技术和工业必然要对其作品和现实担负更多的伦理责任,从而服务于生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面对科学技术,尤其是改变了身体的生物学宿命的现代生物技术日益增加的风险性、不可预测性及其后果的不可逆性,如何在市场逻辑面前守护真正的科学精神,并在研究自由与责任、功利与真理之间保持有效的平衡,将是科学共同体,尤其是实践科学的个人义不容辞的伦理责任。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责任主体,还有拥有医学知识,最频繁地对身体进行操作,并且连接各种身体间关系的医者及其医疗机构。在与资本原则保持适度距离的基础上,利用知识和技术对各种身体施加适当的权力,平等、公平地善待生命,或许既是医者应有的责任天职,也是社会对医者的基本伦理期求。
[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
[3]PALSSON G.Bio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009,51(2).
[4]COHEN L.The Other Kidney:Biopolitics Beyond Recognition[J].Body&Society,2001,7(2/3):9-29.
[5]RAJAN K S.Biocapital as an Emergent Form of Life:Speculations on the Figure of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C]//GIBBON S,NOVASC(eds.).Biosocialities,Genet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Making Biologies and I-dentities.Routledge:Abingdon UK,2007:176.
[6]ROSE N.The Value of Life:Somatic Ethics&the Spirit of Biocapital[J].Daedalus,2008,137(1):36-48.
The Ethical Reflection of Biocapital
YU Jiang-xia
(Center for Studies of Values&Cul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In the"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1844",Marx carried out a profound ethical critique to the capital,with the physical presence of human be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alienation"as the central concept,and the exploration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materiality and abstraction as an importantmethod.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ife sciences,as capital is increasingly aimed at the body,an implicit and extended form of capital,"bio-capital',grow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important,which may bring amore alienated life.Consequently,we should rethink the capital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body".That is to say,we need to have the abstraction of capital to bematerially reduced and call on a kind of ethics which emphasizes the physical presence,especially the embodiment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tomake effective ethical regulation of biocapital.
labor;alienation;biocapital;ethics
献标志码:A
1009-1971(2014)02-0135-06
[责任编辑:王 春]
2013-12-16
于江霞(1984—),女,山东五莲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希腊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