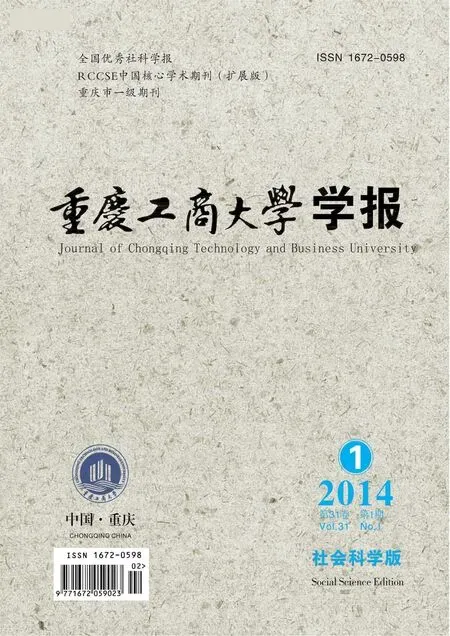藏族牧区小城镇的语言文化生活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镇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
姚春林
(1.河北联合大学,河北唐山063009;2.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081)
藏族牧区小城镇的语言文化生活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镇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
姚春林1,2
(1.河北联合大学,河北唐山063009;2.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081)
采用问卷调查、辅以访谈的方式,调查藏语安多方言区牧区土语片内的一个小城镇(尼玛镇)的语言活力、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结果显示,当地藏语文活力旺盛,所有被试都能用藏语流利交谈,藏语是当地的主要交际用语。大部分被试(77.4%)掌握汉语,是藏汉双语人。被试的语言文字态度的包容性较强,绝大多数被试认为藏语文和汉语文都很有用,希望藏汉语文在当地得到发展。所有被试都希望后代接受藏汉双语教育;61%的被试希望后代在接受藏汉双语教育的同时接受英语教育,成为多语人。目前调查地已逐渐发展成一个藏汉双语社区,这对在保护语言文字多样性的同时发展地区经济大有益处。
藏语安多方言;牧区土语;城镇;语言生活;语言使用;语言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迅速,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这增加了语言(或方言)间的接触,客观上加快了语言同化和弱势语言消亡的速度。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当今的经济发展经常是以牺牲语言文化多样性为代价的。据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统计(Lewis,2009),目前全球约有6 909种语言,其中的51%使用人数不足万人,22%的使用人数不足千人。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上的一篇文章(Gorenflo,Mittermeier,&Kristen Walker-Painemilla,2012)更是指出,语言消亡速度比物种消亡速度快千倍,估计50%~90%的人类语言将在未来100年间消失。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成为语言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学科面临的新课题。
我国有56个民族,130多种语言。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保障各民族的权益(包括语言使用权)是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关注的课题。藏语文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其使用范围遍及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五省区。因历史发展及地域环境不同,藏语在语言、词汇、语法等方面表现出一些差异,被分为卫藏、安多、康三种方言,各方言下又包括不同的土语。因社会经济发展、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其他民族杂居程度不同,藏语各方言内部的使用情况和语言活力也存在差异。本文将以藏语安多方言牧区土语区中的一个城镇社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镇——为个案(安多藏区其他地区的藏语文使用及态度研究将另文刊出),调查社区中藏语文和汉语文的活力以及语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变体的态度,为研究语言接触、语言发展以及藏语文保护提供个案,为制定民族政策、语文政策提供第一手借鉴资料。
一、研究概况
(一)玛曲县尼玛镇简介
尼玛镇是玛曲县府驻地,位于县境东北部,西倾山南麓,黄河西流段北岸,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处。东与甘肃省碌曲县尕海乡接壤,南与四川省若尔盖县辖麦乡、甘肃省玛曲县欧拉乡为邻,西北与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相连。尼玛镇所在的玛曲县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纯牧业县。全县藏族人口约占88%,牧业人口占83%。(2006年数据)①资料来源:“玛曲宣传网”http://maqu.gscn.com.cn/Html/mqxq/2008-6/20/140733431.htm l;“百度百科:玛曲县”http://baike.baidu.com/view/175205.htm.
(二)抽样与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当确定一个研究议题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调查对象的全体。通常情况下调查对象的全体数量巨大,有时甚至无法确定全体的具体数量。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社会语言学研究不能穷尽式地调查研究对象的全体。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过程中常根据某些原则,抽取全体中的部分单位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研究样本推断总体的指标数值。这种研究被称为抽样研究。
抽样的方式有很多种,最理想的方式是“阶段抽样”。但实际操作中,“阶段抽样”是很难做到的。例如,拉博夫(转引自祝畹瑾,1992)曾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采用“阶段抽样”的方法,抽取纽约市下东区10万居民(总体)中的340人(样本)做调查对象,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仅88人。除“阶段抽样”外,“偶遇抽样”“雪球抽样”“判断抽样”等非随机抽样方式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常采用的抽样方法。
实际操作中本研究借鉴祝畹瑾(1984)研究“师傅”用法时的抽样方式,采取“偶遇抽样”的方法选择调查对象。这种抽样得到的研究结果虽不能完全反映总体的情况,但至少可部分反映总体。
具体操作过程中,于2011年8月12日至13日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镇格萨尔民俗文化广场,以随机偶遇的方式,选择31名16岁以上的藏族作调查对象,其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N=31)
(三)问卷结构及调查方法
该项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集体和个别访谈的方式采集研究数据。调查问卷②调查问卷由作者本人,中央民族大学李庐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龙从军、孔敬、马爽共同设计,最后由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黄行研究员共同审订。由五部分45个单选或多选题组成,具体包括:(1)被试基本情况A1-A5,(2)语言习得及语言能力B1-B10,(3)语言学习途径C1-C4,(4)语言使用情况D1-D10,(5)语言态度E1-E16。每题根据调查需要设若干选项或指标,题目及选项、指标之间相互印证,可通过逻辑分析检验被试自报的可信度。调查采用封闭式问卷,即问题的设置及选项、指标是既定的,被试只需在给定范围内做出选择。为防止选项或指标过于简单而导致遗漏一些重要现象或问题,在问卷的题目旁留出空白,问卷末尾留出调查员日记栏,要求调查员把遇到的问题及被试的看法准确记录下来。如果一些问题或现象较重要,则采用个别访谈的办法补充调查。调查采用一对一方式,由调查员逐题询问、被试回答,再由调查员圈选或填写。调查问卷完成后,先由调查员检查各自负责的问卷,再分别进行交叉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联系被试重新询问,以确保问卷的有效性。个别访谈分两类:一是对问卷调查对象的访谈,内容多围绕问卷设置的问题进行;二是专题访谈,即就相关问题寻找合适的对象进行访谈。本研究的调查由作者本人、马忠娥、闫拉旦①马忠娥(藏名:格塔卓玛;女;藏族)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2011级研究生。闫拉旦(男,藏族)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2011级研究生。此次调查过程中,二人给予了极大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完成,调查时间为2011年8月12日至13日。
二、语言习得及语言文字能力
分析调查数据后发现,当地具有良好的藏语环境。小时候(上学前或5周岁前)被试的父母同他们都是只讲藏语②调查地主要通行藏语安多方言。如无特殊说明,本文的藏语专指藏语安多方言。,因此被试最先学会的语言都为藏语;只有一位出生在海东地区的被试因小时候长期和汉族伙伴玩,同时学会了汉语③调查地通行的汉语不同于当地汉语方言,有些被试讲的汉语较为标准,接近汉语普通话,另一些被试讲一种夹带着藏语口音的、不是非常标准的汉语普通话。一些学者(如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教授)称这种通行于民族地区的汉语普通话为“民汉语”。本文将这种语言变体简称为汉语。。现在所有被试都能流利地听说藏语,大部分被试会藏汉双语。其中29人能(或基本能)听懂汉语,24人能够(或基本能够)用汉语交谈。自报完全听不懂汉语的两名被试中,一位是76岁的男性,另一位是43岁的女性,二人均没上过学。另外,被试中1人自报能听懂藏语卫藏方言,1人基本能听懂藏语康方言,没有人能用这两种藏语方言交谈。
如果结合被试的基本信息分析会发现,被试的汉语掌握情况与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存在相关性。在7位藏语单语人中,6人为女性;6人年龄在40岁以上;5人没上过学,2人小学文化。
与语言能力相比,被试的文字能力稍差。21位被试自报能够读藏文(16人“能读书看报”,2人“能看懂家信或简单文章”,3人“只能看懂便条或留言条”);20人能写藏文(14人“能写文章或其他作品”,3人“能写家信或简单文章”,3人“只能写便条或家信”)。20位被试能读写汉文(11人“能读书看报”,7人“能看懂家信或简单文章”,2人只能看懂便条或留言条;8人“能写文章或其他作品”,7人“能看懂家信或简单文章”,5人“只能写便条或家信”)。
调查还发现,被试学习藏语文和汉语文的途径不尽相同。被试自报主要通过“家里人影响”(31人次)学会藏语,另外还包括“学校学习”(8人次)和“社会交往”(6人次)④问卷中部分题目为多选题,因此部分题目中总人次数多于总人数,下同。等;通过“学校学习”(18人次)学会汉语,其他途径还包括“社会交往”(13人次)、“家里人影响”(1人次)、“在外地”(1人次)等。自报受“家人影响”学会汉语的是一位43岁的女性(初中文化,工人)。她告诉调查员,是孩子教会她汉语的。与掌握藏汉语的方式不同,被试掌握藏汉文的方式较为相似,主要通过“学校学习”学会藏汉文。另有5人自报兼受家人影响学会藏文。
三、语言使用状况
(一)家庭语言使用
目前所有被试与父母亲(若父母健在)交谈时都只使用藏语;与同辈(妻子或丈夫,兄弟姐妹)交谈时,28人只使用藏语,3人兼用藏汉双语;跟子女(若有子女)交谈时,13人只使用藏语,4人兼用藏汉双语。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藏语是被试与家庭成员交流时的主要交际语。随着交流对象年龄的减小,被试使用藏汉双语的比例逐渐增加。
(二)社区语言使用
问卷设置了六道题,分别从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合两方面考察被试社区语言使用情况。
跟本民族邻居或熟人聊天时,30人自报仅用藏语,1人自报兼用藏汉双语(兼用藏汉双语的被试是一位60岁的男性,小学文化,出生于海东地区,1967年迁入本地)。跟外民族邻居或熟人聊天时,20人仅用汉语,3人仅用藏语,3人兼用藏汉双语①部分被试从未与外民族邻居或熟人聊过天,选择无此情况,因此此处各选项的总人数小于被试总数。下面的问题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部分问题答案的总数少于总人数。;跟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交谈时,15人兼用藏汉双语,分别有8人自报仅用藏语或汉语。
在本地集贸市场买东西时,18人兼用藏汉双语,9人仅用藏语,3人仅用汉语;去政府机关办事时,14人兼用藏汉双语,4人仅用藏语,1人仅用汉语;去医院看病时,21人兼用藏汉双语,7人仅用藏语,1人仅用汉语。
以上数据显示,藏语是藏族人内部交际的主要交际语,藏汉双语是被试与其他民族或陌生人交际的主要交际语。越是正式的场合,被试使用(包括兼用)汉语的比例越高(政府机关78.9%、医院75.9%、市场70%)。
四、语言文字态度
(一)对相关语言文字用处的评价
总体来看被试对藏语文和汉语文的评价都比较积极,对汉语文的评价稍高于对藏语文的评价。具体来说,21人认为藏语很有用,10人认为藏语仅对一部分人或在一定范围有用;22人认为藏文很有用,9人认为藏文仅对一部分人或在一定范围有用。26人认为汉语文很有用,5人认为汉语文仅对一部分人或在一定范围有用。
当被问到哪种语言或方言对他们更重要时,14人单选藏语,12人兼选藏汉双语,3人单选汉语,2人同时选择藏语、汉语和英语。兼选英语的两位被试均为在校大学生。访谈中一位被试和调查员说,他现在读大三,想毕业后考研究生,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英语。他认为藏族要接触世界,要发展自己,就应该掌握英语。因此他认为藏语、汉语、英语都很重要。
以上数据显示,藏汉双语是对被试更重要的语言,被试对这两种语言的评价和期望都较为积极。目前阶段藏语对他们更重要一些(选择藏语是更重要的语言的被试稍多一些),但被试认为从长远来看汉语文是更重要的语言文字(认为汉语文很有用的被试人数稍多于认为藏语文很重要的被试人数)。
(二)对语言文字发展前景的期望
与对相关语言文字的实用功能评价类似,被试对藏汉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前景都持较积极的态度,其中对汉语文的期待较藏语文更积极。具体来看,22人希望藏语文有很大发展,9人希望藏语文在一定范围内发展。25人希望汉语有很大发展,2人希望汉语在一定范围发展,4人希望汉语自然发展;25人希望汉文有很大发展,分别有3人希望汉文在一定范围内发展或自然发展。
访谈中,部分被试还谈了对藏语卫藏方言和康方言发展前景的看法,他们大多希望这些藏语方言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认为这些方言对一部分人或在一定范围内有用。
部分被试希望汉语文自然发展,访谈中他们向调查员表达了如下观点:全国范围内推广汉语是大势所趋。目前汉语文在当地普及的速度也很快,即使汉语文自然发展,年轻人也会很快成为藏汉双语人,所以目前阶段不需要保护汉语文,任其自然发展就足够了。
五、语言文化行为倾向
(一)日常文化生活
被试中,20人兼看藏汉双语电视节目,9人仅收看安多藏语电视节目,2人仅看汉语电视节目。自报只看汉语电视节目的两位被试均为男性,初中学历,分别是一位30岁的个体户和一位26岁的牧民。两人都表示,为了让孩子尽早尽快地学好汉语,他们家仅看汉语电视节目,不看藏语节目。另外,2位被试自报兼看藏语康方言的电视节目。
被试中,4人自报经常阅读藏文报刊,3人有时阅读,7人偶尔阅读,17人从来不阅读。4名被试自报经常上网,6人有时上网,7人偶尔上网,14人从来不上网。在自报上网的被试(包括经常上、有时上、偶尔上)中,8人只上中文网站,6人既上汉文网站又上藏文网站,3人只玩游戏;上藏文网站的被试偏好同元藏文输入法和班智达藏文输入法。
从以上调查可看出,被试的日常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包括看电视、读书看报、上网等形式。看电视是被试最喜欢的文化活动,藏汉双语是被试语言文化活动的主要载体。
(二)子女教育倾向
教育是关乎民族发展的重要问题。为了解被试对教育的看法,问卷中设置了这样一道题“假如您家附近有不同语言教学类型的小学,您希望后代接受哪种语言的教学(可多选)”。
与安多藏区其他地方的调查结果(姚春林,2012;2013)类似,尼玛镇的被试希望后代接受双语(或多语)教育,成为双语(或多语)人。其中19人希望后代接受藏汉英三语教育,12人希望后代接受藏汉双语教育,没有人希望后代接受单语教育。
访谈中部分被试表达了他们对藏汉双语或藏汉英多语教育模式的看法。几乎所有的被试都希望用藏语作授课语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加授汉语课,从一年级或三年级加授英语课。①不同地区的藏族群众对双语(或多语)教育的模式持不同观点。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调查时,几乎所有被试都表示,他们理想的双语教学模式是采用汉语作教学语言,从小学一年级起加授藏语课。
六、藏语文专项调查
(一)学习藏语文的目的
调查显示,被试学习藏语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民族情感,他们给出的原因主要包括“因为我是藏族人”(31人次)和“弘扬本民族文化”(23人次)等。此外还有一些实用角度的考虑,包括“说藏语能与更多的人沟通”(10人次)、“学好藏语有前途”(6人次)、“工作或外出需要”(2人次)等。
(二)认为藏语发展的困难
当被问到藏语在当地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时,被试给出的答案较为多样。12人认为藏语在当地发展不存在问题,其他被试主要担心政策的执行落实情况以及周围的语言环境会影响藏语今后的发展。他们认为可能影响当地藏语发展的原因包括“政府制定的语文政策执行力度不够”(17人次),“说汉语更有个人发展前途”(4人次),“说汉语可与更多人沟通”(3人次),“周围说藏语的人变少、说的机会变少”(2人次)等。
(三)认为藏文发展的困难
当被问到藏文在当地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时,被试给出的答案同样较为多样。10人认为藏文在当地发展不存在问题,其他被试主要担心政策的执行落实情况和当地藏族人对汉语教育的偏爱。他们认为可能影响当地藏文发展的原因包括“政府制订的语文政策执行力度不够”(20人次),“更多的学生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到汉语授课学校上学”(9人次),“藏汉双语教学质量不高”(7人次),“藏文信息化程度不高”(7人次),“藏文出版物较少”(3人次)等。
以上调查数据显示,被试学习藏语的主要目的是出于民族情感(“因为我是藏族人”或“弘扬本民族文化”);他们认为可能影响藏语文在当地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政府制定的语言文字政策执行不到位”。访谈中多位被试表达了如下类似的观点:我国法律规定各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各级政府也把保护民族语言文字作为重要任务,但实际操作中却存在一些问题,某些具体措施还不是很周全。比如公务员招聘考试中,汉语占相当比重。如果考生仅会民族语不会汉语,不可能被录用;反之,如果仅会汉语不会民族语,不影响最终录取。这客观上鼓励学生学习汉语,忽视本民族语。久而久之,当地的藏语文会遇到危机。再比如,现在好多考试都给少数民族(包括藏族)额外加分。但加分的依据在于考生户口本上的民族成分,而不考虑考生是否真是少数民族,是否掌握民族语言文字。一些汉族把户口本上的民族成分改为藏族,也享受少数民族的优惠待遇,这很不公平(据被试讲,省内天祝县就有一些这样的假藏族)。这些不完善的地方不利于发展藏语文。由此可知,切实落实和完善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语文政策,是发展和保护藏语文的有效手段。
七、结语
在尼玛镇这个以藏族为主的社区,藏语文充满活力,是当地的主要交流工具。77.4%的被试(24人)兼通汉语,会藏汉双语。藏汉两种语言在不同场合分别发挥各自的作用:藏语是被试主要家庭用语;藏汉双语是与陌生人或外民族交流,或在集贸市场、大型医院、政府机关等较正式的场合的交际用语,并且越是正式的场合,被试使用汉语的频次越高。
调查地藏汉语都具有活力的部分原因可能源于被试的语言态度。调查显示,被试的语言文字态度包容性较强。绝大多数被试认为藏语文和汉语文都很有用,并希望藏语文和汉语文都得到很大发展;所有被试都渴望后代成为多语人,希望后代至少接受藏汉双语教育,部分被试希望后代在接受双语教育的同时接受英语教育。
调查结果还显示,被试学习藏语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民族情感(“因为我是藏族人”或“弘扬本民族文化”)。虽然目前藏语文是调查地主要的语言文字,仍有部分被试希望落实和改进相关语言文字政策,以便始终保持藏语文的活力。
当今社会发展迅速,城镇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民族地区既要保护民族语言文化,又要发展民族经济,双语化(或多语化)是重要选择。目前尼玛镇已成为藏汉双语社区,这是在保护藏语文活力的前提下发展当地经济与社会的一条正确道路。希望调查地的藏汉双语始终充满活力,越来越多的人掌握藏汉双语。这既保了护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又能发展地区经济。
[1]Gorenflo,L.J.,Suzanne Romaine,Russell A.Mittermeier,Kristen Walker-Painemilla.Co-occurrence of linguistic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biodiversity hotspots and high biodiversity wilderness areas[EB/OL].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www.pnas.org/content/ early/2012/05/03/1117511109.full.pdf.2012-4-6.
[2]Lewis,M.Paul(ed.).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 World,Sixteenth edition[EB/OL].Dallas,Tex.:SIL International,2009.http://www.ethnologue.com/.
[3]祝畹瑾.“师傅”用法调查[J].语文研究,1984(1): 44-47.
[4]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5]姚春林.城镇化背景下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马克唐镇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J].语言学研究,2013(14).
[6]姚春林.一个藏汉双语社区的语言文化生活——天祝藏族自治县菊花村一组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J].中国社会语言学,2012(2).
(责任编校:杨睿)
Language Culture Life in a Tibetan Animal Husbandry Area Town——Case Study on Language Use and Attitude in Nima Town,Maqu Country,Gansu Province
YAO Chun-lin1,2
(1.Hebei United University,Hebei Tangshan 063009,China;2.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The language vitality,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 in a Tibetan community(Nima Town)in animal husbandry area tone of Amdo dialect region are surveyed by the research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ibetan Language vitality at this area is robustbecause all subjects can fluently communicate by Tibetan Languagewhich is the main communication language in local area,thatmost(77.4%)of the subjects are Chinese-Tibetan bilinguals,that the attitude of the tested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has strong inclusion,that almost all the subjects hold th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both Chinese and Tibetan,and that all subjects hope their children to access Tibetan-Chinese bilingual education while 61%subjects wish their children to access Tibetan-Chinese-English trilingual education.Currently,the surveyed plac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to become bilingual community with Tibetan-Chinese,which benefits the developmentof local economy while protecting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Amdo Tibetan Dialect;animal husbandry area tone;town;language life;language use;language attitude
H214
A
1672-0598(2014)01-0142-06
12.3969/j.issn.1672-0598.2014.01.023
2013-09-28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XZ0901)“藏语文使用活力的调查研究”
姚春林,男,博士,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站博士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博士后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濒危语言学、复兴语言学、二语习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