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生活事件、特质应对方式、父母养育方式及社会支持情况研究
温子玉 于敬杰 杨建立
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经历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1],且女性患者经历的要多于男性[2-3];采用了更多的消极应对方式[4],女性患者采用的更多(除酗酒)[5];父母倾向于低情感温暖、高拒绝否认及高过度保护[4];拥有较少的社会支持[6]。然而,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比如,男女抑郁症患者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采用的应对方式并没有明显差异[7-8];只发现社会阶层较低的患者倾向于拥有高过度保护的父母等[9]。可见,关于社会心理因素在抑郁症发生中的作用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必要对其进一步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组来自天津市安定医院2013年3月-2014年2月的门诊和住院抑郁症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②无严重躯体疾病、精神发育迟滞、人格障碍、无酒或其他物质依赖或滥用,无精神病性症状;③年龄18~55岁;④小学以上文化程度;⑤自幼大部分时间与父母共同生活;⑥获得患者对本研究的知情同意;⑦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评分>20分;⑧抑郁症病史不超过3年。
对照组为与本研究中抑郁症患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态及生活背景均较为接近的社区人群,入组标准:①无严重躯体疾病、精神发育迟滞、人格障碍、无酒或其他物质依赖或滥用,无精神病性症状;②年龄18~55岁;③小学以上文化程度;④自幼大部分时间与父母共同生活;⑤获得其对本研究的知情同意;⑥HAMD-24评分<8分。
研究组共104例,男性48例,女性56例,平均年龄(39.00±9.54)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46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58例,已婚92例,未婚12例;对照组共106例,男性48例,女性58例,平均年龄(36.04±8.50)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50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56例,已婚93例,未婚13例,两组性别、学历、婚姻、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由2名经过一致性培训的精神科医生采用①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②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③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EMBU),④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和⑤HAMD-24对两组进行评定,在评定前主测者与受测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评定环境安静无干扰,评定时间控制在50分钟左右,其中LES重测信度为0.611~0.742,TCSQ中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75和0.73,EMBU为0.58~0.82,SSRS为0.92,HAMD-24各单项信度系数为0.78~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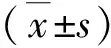
2 结 果
2.1 两组LES、TCSQ、SSRS得分比较 研究组的负性刺激量、总刺激量、积极应对方式、主观支持及客观支持得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见表1。

表1 两组LES,TCSQ,SSRS得分比较分)
2.2 两组EMBU各因子得分比较 两组EMBU父亲处罚、严厉因子,父亲拒绝、否认因子,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因子,母亲拒绝、否认因子,母亲严厉、惩罚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见表2。

表2 两组EMBU各因子得分比较分)
续

拒绝、否认 7.98±2.908.85±2.73-2.2390.026过度保护9.90±2.1810.20±2.58-0.9110.364母亲情感温暖、理解51.73±7.0049.97±9.311.5500.123过分干涉过分保护 31.13±7.0432.99±6.25-2.0260.044拒绝、否认 10.02±2.2912.64±4.13-5.6990.000严厉、惩罚 10.23±2.6912.34±4.39-4.2080.000偏爱被试9.00±5.558.49±3.280.8090.420
2.3 抑郁症患者男性组与女性组LES、TCSQ、SSRS和EMBU各因子得分比较 男性组48例,平均年龄(39.42±9.52)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22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26例,已婚44例,未婚4例;女性组56例,平均年龄(38.64±9.72)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26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30例,已婚50例,未婚6例。两组在年龄、学历及婚姻状况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男性组的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总得分均高于女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见表3。

表3 男女性LES、TCSQ、SSRS和EMBU各因子得分比较分)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发病前经历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1,10]。提示负性生活事件在抑郁症的发生中可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Caspi等[11]从基因层面发现:如果个体的5-HT转运体的基因启动子多态性中存在一个或两个短等位基因,那么该个体因生活压力导致抑郁的风险就会增加,提示不良刺激可能只对部分人群抑郁症的发生有影响。
本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采用的积极应对方式要多于对照组(P<0.05),而消极应对方式二者之间并无明显差异,这与之前的研究相悖:Holahen等[12]为期10年的一项大样本随访研究发现, 回避性的应对方式对抑郁情绪的发生具有预测作用。考虑到既往研究样本量较大并经过长期随访,倾向于认为两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样本量大小和研究时间不同有关。抑郁症患者的应对方式越积极, 病耻感就越低[13],提示在治疗中注意纠正患者的不良应对方式是必需的。
研究组患者的父母均表现为低处罚严厉、低拒绝否认、而母亲还表现为低过度保护,这与之前的研究不符。唐登华等[14- 15]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父母表现低情感温暖、高拒绝否认、高惩罚严厉及高过度保护。分析原因可能为从小在父母的较严厉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子女,有着更强的抗压能力和适应能力,所以更不容易出现问题;也可能受试者在作答过程中不愿意提及自己父母采用糟糕的教育方式而进行粉饰隐瞒。
社会支持方面,抑郁症患者主观支持得分较低,而客观支持得分较高,这跟以往的研究不完全相符:Tracey等[6]研究表明,抑郁症与较少的社会支持有关;而Symister等[16]则报道,在中、重度抑郁症中,有无充足的社会支持对患者的抑郁程度并没有影响。在本研究中,由于样本量较小,未能将结果按轻、中、重度抑郁进行分组后再比较,所以,社会支持在抑郁症的发病中发挥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发现,男性抑郁症患者的积极、消极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总得分均高于女性(P<0.05),这可能与男性比女性更擅于理性思考、更擅于利用身边现有的资源来解决问题但同时面临的压力更大有关。有研究表明,通过心理教育可改善女性患者的抑郁症状及应对方式,提示对女性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是必需的[17]。
局限性:①研究组并非从一般人群中筛查获得;②样本量较小,未限定入组的抑郁症患者为初次发作;③本研究是一个横断面研究,患者均被诊断为单向抑郁,但有可能其中部分患者,过一段时间会被修改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④患者出于隐私、人情世故等考虑,作答中很可能存在隐瞒。今后的研究如果能去除回忆及隐瞒等干扰因素,能随机选择入组患者,纵向研究患者情况,可能取得更为精准的结果。
[1] Joca SR,Padovan CM, Guimarães FS.Stress,depression and the hippocampus[J].Rev Br Psychiatry,2003,25(Z2):46-51 .
[2] Kendler K,Thornton L, Gardner C.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previous episodes in the etiology of major depression in women: An evaluation of the 'kindling' hypothesis[J]. Am J Psychiatry, 2000,157(8):1243-1251.
[3] Maciejewski PK, Prigerson HG, Mazure CM . Sex differences in event-related risk for major depression[J]. Psychol Med,2001,31(4):593-604.
[4] Muris P, Schmidt H, Lambrichs R,et al. Protective and vulnerability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normal adolescents[J]. Behav Res Ther, 2001,39(5): 555-565.
[5] Rudnicki SR,Graham JL,Habboushe DF,et al. Social support and avoidant coping: correlates of depressed mood during pregnancy in minority women[J].Women Health, 2001,34 (3):19-34.
[6] Tracey DW,Kenneth SK.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ajor depression cross-sectional longituainal and genetic perspectives[J]. J New Ment Dis,2000,188(5):251- 258.
[7] Sherrill JT,Anderson B,Frank E,et al. Is life stress more likely to provoke depressive episodes in women than in men[J].Depression And Anxiety,1997,6(3):95-105.
[8] Spinhoven P, Kooiman CG. Defense style in depressed and anxious psychiatric outpatients : an explorative study[J].J Nerv Ment Dis,1997,185(2):87.
[9] L. Rojo-Moreno á L,Livianos-Aldana G,Cervera-Martõnezá J A. Dominguez-Carabantes Rearing style and depressive disorder in adulthood: a controlled study in a Spanish clinical sample[J].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1999,(34):548-554.
[10] 任显峰,程荣玉,颜淑环.心理社会因素在抑郁症发生中的作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06,16(1):30-31.
[11] Caspi A,Sugden K,Moffitt TE,et al.Influence of life stress on depression: moderation by a polymorphism in the 5-HTT gene[J]. Science, 2003, 301(5631):386-389.
[12] Holahen CJ, Moos RH, Holahen CK,et al. Stress generation, advoidance cop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10-year model[J].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05,73(4):658- 666.
[13] 崔向军,周亚青,李丽娜,等.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20(6):814-815.
[14] 唐登华,潘成英,漆红.70例青少年抑郁障碍心理社会学影响因素探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7):468-470.
[15] 王高华,唐记华,王晓萍,等.抑郁障碍青少年父母养育方式、应对方式归因风格及其相关性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15(2):123-124.
[16] Symister P,Friend R.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and problematic support on optimism and depression in chronic illness: A prospective study evaluating self-esteem as a mediator[J].Health Psychol,2003,22(2):123-129.
[17] 方芳,汪作为,王亚光,等.社区人群抑郁障碍早期心理干预效果随访[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3):399-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