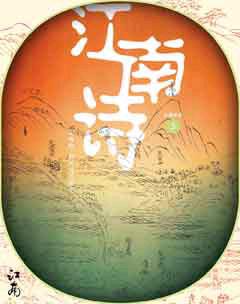祖国(外五首)
给我秤,我就轻
给我诺言,我就卑微
给我一棵草,我就是露水
而你给我的总是针尖与麦芒
在这旷世,我容易悲伤
容易掉眼泪,容易弯下腰聋哑
祖国太大,小小的站台上,三个民工被阻止上车
因为他们的身体,像他们手中的蛇皮口袋——
巨大的臭,挤压着光芒中的人群
巨大的臭,挤压着祖国敏感的嗅觉
而那三个民工消失的背影,恰如教堂上的尖顶
当公车开动,向后退的是整个世界的冷与硬
必须借助悲悯才能凌越悲悯吗
祖国,向日葵也会向大地袒露身体里的黑与红
祖国,本着良心,宽恕和赞美
每一行汉字里都有缄默、渴念和疼痛
老鼠之歌
楼道里的灯火依旧昏暗,风吹过四季
也没有将它吹灭,王家老太的眼睛却瞎了
她敲铁门栅的木拐落尽暮色里
而身后的石阶上飘满落叶,日渐光秃的槐树
像两手空空的僧侣,对着星空默诵着经文
这时候,老鼠又开始歌唱:“这里的世界。”
有人漫不经心地打扫落叶,并思考生命与存在
有人隐藏一天的酸苦,提着一壶酒从夜里归来
穿过那昏暗的灯火,像幽暗的树影穿过散碎的玻璃
这里存在一种不可知的神秘:窗外花盆里的种子
被小老鼠啃食过,但它依然在发芽,一想到这里
小老鼠放松了颤抖的喉咙,不再发出任何声音
黑夜里,王家老太的木拐又在敲打墙壁
像她戴着假牙的叹息。“有些人,总是好的!”
一只年迈的老鼠突然说,它带着明显的乡音
今夜,人民南路南延线二段73号,落满月光的墙上
那个圈起来的暗红的“拆”字,像老鼠们正在冷却的血
“这里的世界,我的世界……”黑夜从门缝里涌入
“……这里是最后的一晚”,
“我的世界,我的家园……”
歌声潮湿,像两行清明时节的脚印
走过革命纪念碑
钟声响动,整座城市
像那秒针被秋风放逐
街心的革命纪念碑
像山中耀眼的坟头
碑上的人如星辰
我相信,他们都是英雄
我独自走过,没有充满敬意
虽然它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也没有丝毫的怨恨
绕过它,是一个平民最好的捷径
致胡应鹏
乡村荒芜,城市雾霾重重
河流浑浊,藏不进孤独的风,我不想留下了
你支撑我掘出黑夜的隧洞
警车来了,啮齿动物说我是危险分子
需要一个小房间,和一些思考,他们的耳朵
就想听我说出谎言,可我不会
我有流水的心,宁可破碎,也要干净
与纯粹,于是,我病了,沉默是重疾
医生忙着堕掉阴暗的胚胎,满手血光
只剩下小护士,像我的每一个女友
面带桃花,仿佛单纯,已经很久没有性欲了
体内隐藏着病毒,它们啃噬我……
像在啃食醉鬼、流浪汉和小妓女
在立交桥上,在垃圾站,在小胡同里
前面是静止安谧的空旷,身后是流动不息的月光
没有菩提花,我开始相信命运了
你说,这是好事:终于找到了断除噩梦的良方
梦的本质是黑暗,我或者是找到了一口更深的井
把幽暗净化成虚无,滋养自己沙砾一样的身心
可我更想,像一片雪花,穿过这星球的边际
逆向飞翔,像你,将灵魂安顿在辽阔的星河里
孤 独
写下生活的真相
是一种惩罚
我难以在纸上获得
多么孤独,从急诊内科
到心理诊所,回家的路
深入镜中,当虚掩的窗扉
像熨斗,抚平时光的褶皱
痼疾沉疴,时光太深
从未停下的脚步,早已抬不起的双手
有时候,我看清了现实
看穿了生活,甚至看透了生死
这一天终将到来,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在黄龙溪独饮
醉酒伤身,那不醉呢
伤身的应该是这深夜的钟声了
昨日已然,今日已然,庙宇还是肃穆庄严
敲钟的人老了吗,顺着河岸,人影绰绰
我也来来回回,走走停停,像风里的柳永
流水茫茫,石头是隐居的长老,在深处看我
把酒水饮成悲苦,把词语垒成硬伤
再喝一杯,南风漫漫,我嗅出了幽暗之味
有夜风淌过流水的腥臊,与湿润
遥远的星辰落进我的酒瓶,再喝一杯,要痛饮
月行八百里,多么自在,身后的水声
像密集的花蕾,让枯坐的影子获得安慰
作者简介:罗铖,1980年生于四川苍溪,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刊物发表过作品,参加第29届“青春诗会”,出版有诗集《黑夜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