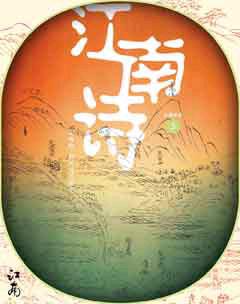一种微妙的互动
藏马
多多说,他的诗歌没有一句是朦胧的,虚假的。前几日,重新浏览友人杨邪的博文时我也感觉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说有些散文比一些描写单一真实事件的散文更有力更真切。因此,他也把此类散文开辟了一种栏目叫“虚构散文”。这也使我想到在阅读《吴越春秋》时的一种惊讶,譬如越女试剑——
越女将北见于王,道逢一翁,自称曰袁公。……袁公操其本而刺越女。越女应即入之,三入,因举杖击袁公。袁公即飞上树,变为白猿。遂别去,见越王。
和伍之胥死后的兴风作浪——
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
在这两段看似夸张的志怪式的叙述里,却凸出了两位历史人物的一些本质性特征:越女剑术的卓越和传奇,伍之胥的刚烈——那怕死了也要“依潮来往,荡激崩岸”,不依不饶。这看似是一种闲笔和虚构,但重现了历史的更深的真实。竟比后来的一些史书家的文笔强多了。
提到史书家的文笔,更值得一说的是司马迁,在大的历史事件和情景里,却着重了对人物的细节的描写,譬如《晋世家第九》写重耳临返国前的一个插曲:
重耳爱齐女,毋去。赵衰、咎犯乃于桑下谋行。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杀侍者,劝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齐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
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咎犯曰:“杀臣成子,偃之愿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
有声有色。人物、时间、地点以及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推动和过程,简直是一篇优秀的小小说,并且,最后的一段富有人性化的对话:重耳说,如果事情不成功,我要吃舅舅你的肉,而他的舅舅咎犯回答说,如果事情不成功,我的肉比较腥臊,不值得一吃。真是令人大笑不已。也许,虽然,作为史记,里面也包含了作者主观的一些构想,但恰恰是这种符合历史人物性格和情景的虚构,却更让人觉得凸现了历史的真实。还有一段记叙,也颇为有趣: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遣归家,欲其意折,后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云“公至”,夫人踞机如故。太祖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太祖却行,立于户外,复云:“得无尚可邪!”遂不应,太祖曰:“真诀矣。”遂归。
曹操本意是把闹得不像话的老婆搞回娘家折折锐气的,那想到他跑到丈母娘家去接人时,丁夫人就是负气不理他,也不管曹操低声下气,很亲切地用手抚摸她的背,说只要你回头看我一眼,我就带你一起坐车回去,求了半天,直到退回到了门口还恳求说,真的一起回去吧!丁夫人呆在织布机上就是不动,太有性格了。而通过这些平淡的细节性的描叙,似乎也让人触摸到了一代雄杰曹操真实的人性化的另一面。
那么,一个写作者,这样是否就算是真诚了呢?在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很多时候,一个写作者总是被集体幻像所左右,而丧失了自我和本我。另一种情况是:一个写作者拥有着内心的诚挚,但在文字的表达上,显示不出文采;因为写作归到底,还是要在语言和技艺上得到体现的,并在语言中获得自身的净化和升华。对于这点,诗人牛汉在其随笔《所谓第一义与第二义诗人》里反复强调过。他说:
“……只要他(或她)如布罗斯基自律的那样,每写一首诗,都是全生命的燃烧,不留下任何可燃烧的东西,他一定是真诚的,他的诗一定不会有自私或虚伪的阴影……即使有一些诗人,真的有某些应当谴责的地方,假若他进入诗的创作时,表现出了真诚与纯洁,而且写出纯美的作品,这是绝对应当赞扬的;而这些痛苦的具有复杂心绪、沉溺在现实生活中的诗人,当他们勇于投入一次美好的创作活动,对他本人我以为是一种真正的刻骨铭心的内省与自励。他的诗无疑地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
这些话,让人反省。而牛汉还说:“真的第一义的诗人……是那些表里如一堂堂正正的真诚而纯洁的诗人……在诗里都显示出了高尚的人格。”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