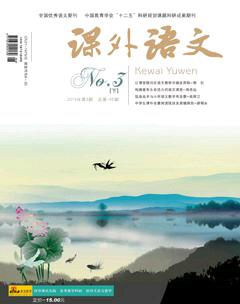冷热交错中的情感表达
林云妹
【摘要】《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情感呈现为冷热交错的状态,表现为文本语言独具特色:言语的逻辑矛盾贯穿全文;转折句式和反问句式大量使用;叙述、抒情、议论等表达方式的融合。
【关键词】《记念刘和珍君》;言语逻辑矛盾;句式;表达方式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谈到,“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这一提法正体现了鲁迅对于写作应合理处理情感和理性的看法。《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情感丰富,既有对反动当局凶残暴虐的控诉、走狗文人阴险无耻的揭露,又有对青年学生流血牺牲的颂扬,对青年学生生平际遇的追忆,还有对麻木不觉醒的国人的警示,对奋然前行的猛士的激励。而且本文情感强度高,全文字里行间充斥着鲁迅的大悲、大哀、大愤、大怒。但如此丰富、高强度的情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并没有表现为不可抑制的热力喷发,而在语言上呈现出冷热交错的独特风格,在冷静的理性中,情感更显强烈、复杂、深沉。
一、言语逻辑矛盾中暗含冷静的理性与热烈的情感的交错
本文八个部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言与不言这一矛盾。
1.我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2.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
3.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
4.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5.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
6.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7.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8.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表面上看这几句话在语义上充斥着矛盾,作者反复提到“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有要说的话”,但却屡屡表示“无话可说”。在言与不言中作者徘徊不定,自打嘴巴。但这样的语义逻辑矛盾,恰恰暗含了作者内心冷静的理性与热烈的情感的交错,从思维变化的维度来看,并不矛盾。
第一组中“我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一句是在程君劝鲁迅为刘和珍写文章,提及刘和珍爱读鲁迅的文章,并订阅《莽原》杂志后所述。这一“必要”应理解为鲁迅对像刘和珍这样的进步青年的认同与爱护。第二组中“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和“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这两句话都是在叙述“庸人”的世界中,时间会冲淡烈士流血的印迹后提出的,表达了作者欲警醒“庸人”世界保持记性,抗拒遗忘的想法。第三组中“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一句紧接着详叙了刘和珍等人的遇害经过以及她们在死难面前的互助,这一叙述侧面证明了她们并非“暴徒”,而真正滥施暴虐的是段祺瑞执政府。在这几句欲言的表达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对进步学生的爱,看到了鲁迅对麻木的国人的警示,看到了鲁迅对诬陷青年学生的反动政府的有力回击。这就是尚能保持冷静状态下的鲁迅,一个有爱、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的鲁迅。
但冷静的、理性的鲁迅却又时时为心中猛烈的情感的火焰所燃烧,呈现无语的状态。第一组中“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和“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是在论及反动派制造流血惨案、流言家在惨案后制造“阴险的论调”时所述。第二组中“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是在叙说惨案发生的经过,反动当局凶残屠杀进步青年,走狗文人无耻污蔑进步青年后所说。第三组中“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一句处于全文结尾,是作者在分析请愿的意义,提出“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后提出。在一、二组无语的表述中,充斥着对反动当局凶残暴虐的控诉,对走狗文人阴险无耻的愤怒,两次谈及都使他无话可说,这样的无语正是强烈情感使然,是情到深时的无言,鲁迅太愤怒了、太痛苦了。第三组中“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一句区别于前面的“无话可说”的表述。前两组中的“无话可说”,愤慨的同时并未真的无语,叙述还在持续。而作者在“呜呼,我说不出话”的表述后却真正无语了,全文止步于此。 “说不出话”较“无话可说”所表达的情感则更为浓烈,强烈、丰富的情感已无法以言语的形式来表达,而只能寄以“呜呼”的长啸来倾诉。此时,情感的浓烈打乱了言语的形成逻辑,情感占据了身体的各个器官,理性被最大程度的压抑,情感成为个体的主导,情感甚至能等同于个体,个体也充溢着情感,情感的强烈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状态。
二、转折句式的使用——维持文本隐形的热度
本文从开篇叙及写作缘由到第三部分叙述我对刘和珍君的印象及第六部分对徒手请愿意义的讨论,全文多处呈现为理性的冷静,但全文的情感却始终处于“冷而不冷”的热度中。转折句式的大量使用是维持隐形的热度的重要因素。
本文大量使用转折句式,其中以关联词“但”来连接的有10处,以关联词“但是”来连接的有2处,以关联词“然而”来连接的有5处,以关联词“而”来连接的有3处,以关联词“却”来连接的有3处,以关联词“可是”来连接的有1处,全文共有24处语义上的转折。 转折关系复句又叫主从关系复句,前后分句的意思相反或相对,或部分相反。转折关系复句语义上呈现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明显体现为情感不断地跳跃与突转。即便是叙述中也包含了大量的转折语气,“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大量转折句式的使用使得文章的情感虽在理性的控制之下,却从来未曾冷却,保持着一种热度,这样的处理也使得叙述之后的抒情、强烈情感的表达,更为顺畅。
三、在冷静的叙述、议论中抒情,情感热烈而深沉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第一部分先是叙述了纪念死难者这一写作缘由,后转入抒情“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第二部分在“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的抒情后又转入叙述“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第三部分叙述我对刘和珍君的印象。第四部分在叙说青年在执政府前遇难的概况后,转入抒情“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第五部分对几位女子就义的详细经过进行叙述。第六部分是对徒手请愿意义的议论。第七部分为抒发了对中国女子勇毅的赞扬。
全文杂合叙述、议论、抒情等手法,使抒情不呈现一贯而下的特征,而是在叙述中抒情,使情感有依托、有根据。“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平日的言行叙述正是对诬其为暴徒的有力反正,使作者对反动政府、文人的控诉更为有理有据,更具说服力。对刘和珍等人被枪杀的经过的叙述,以特写镜头式的描述来展现,“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并着重描述了几位女子在死亡面前互助友爱的场景,使作者对爱国青年的称颂“当三个女子从荣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更为感人至深,对反动政府“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大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的批判更显辛辣;在议论的冷静中抒情,作者认为徒手请愿的意义极为寥寥,这样冷静的议论使读者有被泼了一盆水的感觉,但冷静后读者对后文所抒发的对于中国女子的称颂则更为认同。几种表达方式的杂合使本文的情感表达表现为理性之下的情感,情感表达不只是维持表面的热度,而是具有了深层的热度,更犀利,更见力量。
参考文献
[1]刘福荣.《记念刘和珍君》抒情艺术的魅力[J].语文天
地,2007,01:7-8.
[2]高兵.《记念刘和珍君》中转折连词的语法与修辞[J].汉字文化,2005,04:20-23.
[3]李斌培.《记念刘和珍君》教学研讨[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02:125-128.
(编辑:龙贤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