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在南半球:包罗万象
司马勤 李正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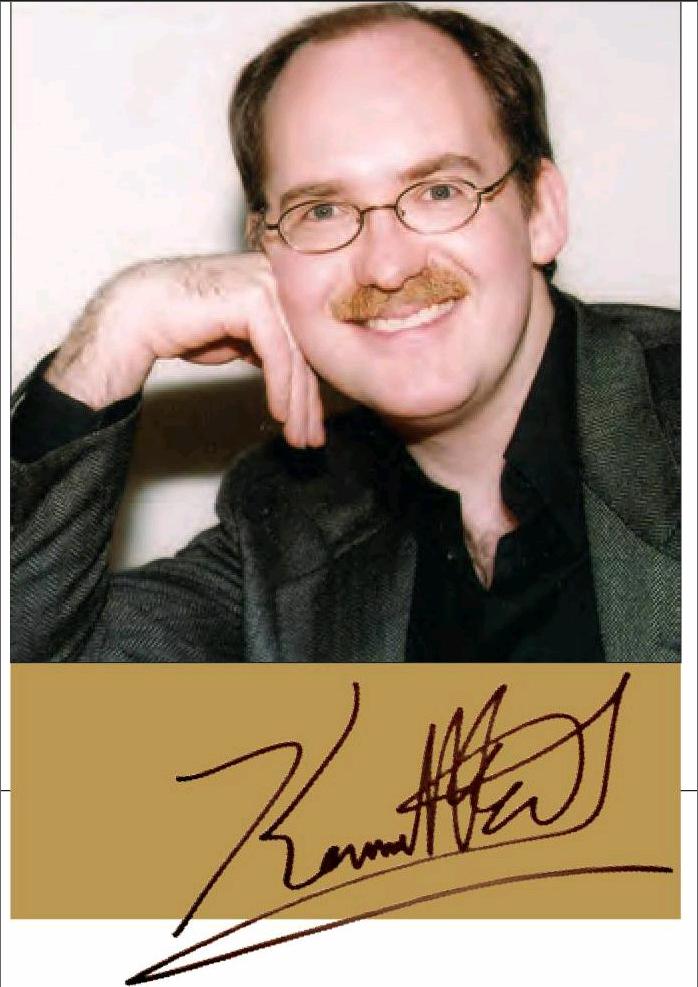

上个月我在专栏里探讨了“压缩”的艺术,因为看了一场瓦格纳的《指环》——这部人类文明迄今为止历时最长的歌剧故事—被浓缩成只有90分钟的木偶剧。本月的话题,则正好相反。
数周前,我满怀希望地去看了编舞家萨莎·瓦尔兹(SashaWaltz)执导的《狄朵&埃涅阿斯》)(Dido&Aeneas)——本年度悉尼艺术节大力宣传的重头戏——主要原因是去年艺术节搬演《塞魅丽走步》(Semele Walk)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两个制作都是从德国引进;它们把现代主义注入巴洛克歌剧——两者的视觉以及触觉都标奇立异。
但是,《塞魅丽走步》把亨德尔的乐谱裁剪了,恰当地搭配了精密的构思,效果天衣无缝。可惜,《狄朵&埃涅阿斯》给人的感觉,却是不修边幅。舞台上出现了不少非一般的画面:演出一开始,一群舞者在庞大的透明水槽里做出各种肢体动作。只可惜过了良久,我还是弄不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歌剧段落之间的连接究竟是什么?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
也许我不应该这么刻薄。瓦尔兹这个版本的《狄朵&埃涅阿斯》在悉尼的宣传资料中,被纳入舞蹈表演而非歌剧——我推测,英文名称中用了“&”这个符号不是表示“与”,而只是用来分隔瓦尔兹版本与珀塞尔原作的一个符号。还有,舞蹈在巴洛克歌剧中往往都是核心部分。可是,在这次演出中,音乐与舞蹈好像互不相干,有时候像是出现于两个平衡的宇宙空间中。
在一个舞蹈爱好者与音乐爱好者分隔的宇宙里,我必须郑重声明,我属于后者。况且,我们的杂志是《歌剧》而非《舞蹈》。令我稍许有些兴趣的不是实质的舞姿,而是整体演员的阵容。我很少看到舞蹈演员团队的体形能那么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团队中有老有少,高矮胖瘦样样都有,与平常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些像筷子般精瘦的舞者形成很大的对比。
我一边看演出,一边为演奏演唱的古音乐学院乐团(Akademie für Alte Musik)与柏林合唱组(Vocal Consort Berlin)感到惋惜,也担心喜爱珀塞尔音乐的听众会感到失望。指挥克里斯托弗·莫尔德斯(Christopher Moulds)带领乐团,无论风格与演绎都贯彻得十分顺畅,只可惜歌唱与戏剧效果却不那么理想,因为大部分歌唱家都有很重的德语口音,演出时又没有投放英文字幕。虽然这是一出英文歌剧,但我连一个词都没听懂。
到了演出结束时,我回想一下,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导演可能成心如此安排,她压根没想让观众了解唱词与情节。因为制作没有用上字幕,观众不用把目光投向字幕板,不用费心关注情节发展。于是,他们可以全神贯注地观看舞台上那些抽象动作的美妙效果。演出期间,歌剧人物同时由歌唱家与舞者扮演。
或者有人会用“解构”这个词来形容瓦尔兹的艺术思路。但是,“解构”的目的,是要挖开被埋没的、深层次的内涵。瓦尔兹的作品没有叙事发展的根据,也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另一种解读。最令人懊恼的是,演出时间比歌剧原版还要长。珀塞尔的原作历时大概一个小时,瓦尔兹的《狄朵&埃涅阿斯》却用了近100多分钟。在歌剧悠久的历史中,从来都没有把原作品延长的这种必要。
说到这里,我要推荐一个“大约一小时”(About an Hour)的概念——将每场演出控制在50~75分钟——这是悉尼艺术节极受欢迎的一种节目分类。这个系列的大多节目都在“车厢工作坊”(Carriage works)里举行。场地曾经是个火车站,现在是个袖珍表演艺术中心。观众可以高频率地、像短暂测试水温一般,轮换接触不同的表演方式,而演出都在从前的老轨道上或者车厢隔间里举行。因为表演时长只有“大约一小时”,观众不需要花上一整个晚上便能接触到不同的艺术媒体。我在车厢工作坊花了一整天,看了六场演出。
除了戏剧、舞蹈与电影,本年度悉尼艺术节的观众更可以在没那么痛苦的欣赏环节下品尝当代歌剧,由悉尼室内歌剧团进行表演。这一个新进的团队首次在艺术节中亮相,节目的标题是“他的音乐燃烧着”(His Music Burns),他们连续演出了两个剧目:盖奥尔吉·库尔塔格(Gyǒrgy Kurtfág)的作《踏步一无处》(pasàpas-nulle part)与乔治·本杰明(George Beniamin)的室内歌剧《走进小山》(Into the Little Hill)。两部歌剧加起来也只不过一个多小时,舞台上显示的戏剧元素亦相当可观。
库尔塔格这位当代匈牙利作曲家把爱尔兰现代诗人萨缪尔·贝克特(Samud Beckett)零碎的文句谱上了简约的音乐,而导演莎拉·吉尔斯(Sarah Giles)的舞台同样以简约著称。聚光灯的焦点是男中音米切尔·莱利(Mitchell Riley)。他在台上独自坐在一排观众席之中(正好与来看演出的观众相映成趣)。灯光明暗交接之间,莱利换到不同的座位,表达的感情也有所不同。贝克特的句子既不是诗词也不是散文,但字里行间的韵律与库尔塔格的音乐结构紧扣之至。音乐效果既不像纯歌剧但又不是典型歌曲套曲,效果令人觉得既兴奋又迷茫。
本杰明作品《走进小山》的编剧是马丁·克里斯普(MartinCrisp),讲述了花衣魔笛手这个童话故事中的社会与政治隐喻,全部角色由女高音艾伦·温哈尔(Ellen Winhall)与女中音艾米莉·埃德蒙德斯(Emily Edmunds)两人分担。花衣魔笛手本应戴上一顶花帽,但是这个制作强调世界幽暗的一面,所以魔笛手全身都穿上了黑色,也增加了观众想象的空间。
库尔塔格的歌剧是独角戏,因而本杰明剧中的两个演员,看起来就已经相当热闹了。库尔塔格的音乐精简,本杰明的乐段相对来讲更像热带森林般茂盛。本杰明与陈其钢都是梅西昂的弟子,他们同样喜好探索丰富的和声,但也专注打造自己的艺术视野。
悉尼地处南半球,阳光普照,不像北半球现在到处的白雪皑皑。悉尼人最喜欢的就是在沙滩上嬉戏。澳大利亚歌剧院新制作的《土耳其人在意大利》(The Turk in Italy)能如此成功,多少也与沙滩有关。这是罗西尼青年时代的作品,澳大利亚歌剧院请来了西蒙·菲利普斯(Simon Phillips)担纲导演一职。故事的背景就像罗西尼的《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An Italian Woman inAlgiers)的续集。当年,作曲家肯定受到那不勒斯海港的启发,因为委约他写新作的正是那不勒斯圣卡洛歌剧院。但是,菲利普斯为悉尼歌剧院制作的构思,更像是来自悉尼市内的邦代海滩(Bondi Beach)。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翻译字幕中插入了不少澳大利亚俚语[意大利语via di qua变成了澳大利亚英语的bugger off(滚)]。但是,有些元素在罗西尼的时代中出现却显得格格不入。比如说,化装舞会中竟出现打扮成猫王与玛丽莲·梦露的宾客。
讨好本土观众,只是其中一个目的。这个制作超越了平常在舞台上搬演的闹剧——或者应该这样说,一个被公认为罗西尼作品中像注脚般无关重要的博物馆藏物,配上枯燥乏味的处理手法——是因为指挥安德里亚·莫里诺(AndreaMolino)那天不怕地不怕的热忱。他让音乐充满生机,与舞台上菲利普斯所营造的、令人惊喜的疯狂节奏配搭恰当。把音乐底层藏着的动力发挥出来已经很难;让故事变得活生生,简直就是导演才华横溢的见证。
每一次在悉尼看歌剧都令我想起,悉尼歌剧院这个世界闻名的地标,令人赞叹的只是它的外观。其中1500座位的歌剧厅(去年改名为“琼·萨瑟兰剧院”)面积小,音响效果反复无常。(悉尼歌剧院音乐厅可容纳2680座位,声效相对来讲要好很多。)
参与演出的本土与海外演员都胜任有余。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澳大利亚男中音萨缪尔·邓达斯(Samuel Dundas)。他扮演诗人兼酒保普罗斯多西莫(Prosdocimo),正是站在台侧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脑,更把一切经历记录下来。邓达斯在台上的表现不但令人联想到费加罗的雏形——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推想,假如他们还记得有普罗斯多西莫这个人物的话——这位演员充分地表达了角色的喜剧性。邓达斯已崭露头角,未来的日子,他大可担纲罗西尼最令人津津乐道的那位理发师了。这么成功的制作,应该让普罗斯多西莫在台上频频亮相,多为大家调制几杯鸡尾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