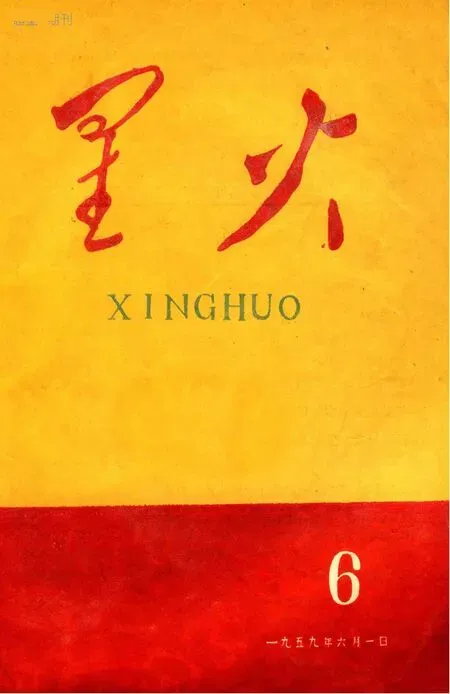蚂蚁
□张海芹
蚂蚁
□张海芹

九志刚去看过那个新送来的婴儿,现在天色已暗,有乌墨的云像破棉絮一般地压过来,可能是要下雨,谁知道呢?
可是,那个婴儿长什么样,九志发现自己想不清楚了。裹在小棉被里,一团粉肉,像是剥了皮的小耗子,可是眉眼呢?全没印象了。
九志之所以跑去看那个小婴儿,是因为保姨的一句话,当时很多孩子都围着保姨,保姨就有些不耐烦了,说,看什么看,你们来时也是这个小样子。
九志当时正和小苦瓜在院角扒蚂蚁窝。原本是九志发现有一弯弯曲曲排列成队的蚂蚁,为了生计正在碌碌劳作搬运食物,于是便喊了小苦瓜来看。谁知小苦瓜抄起一根木棍对着那条细细的黑线就是一阵乱戳,这还不过瘾,顺藤摸瓜直捣蚂蚁的老巢。被他一折腾,那蚂蚁窝就像打翻的墨盒,细黑的蚂蚁便如四溅的墨汁,惊慌失措四处逃窜。
那一刻,九志很后悔喊了小苦瓜,原本也知道小苦瓜不会安生来看蚂蚁搬家,小苦瓜坐不住站不住手也闲不住,他来只会是这个结果。好在,没容九志太过自责,那边保姨的声音就传来了,看什么看,你们来时也是这个小样子。
九志大概是最后一个看到那个婴儿的,因为就连小苦瓜都闻声第一时间跑去凑热闹了。九志看着保姨抱着婴儿上了二楼,那里有一个大育婴室,婴儿们都在那里,孩子们抬头看保姨上了楼也四散开去。保姨不是第一次抱婴儿回来了,抱回来的婴儿有的很快就被人领养走了,有的也会留下来,就像九志,还有小苦瓜,一直留到他们现在这么大。所以,有婴儿被抱回来,大家也就是好奇那么一时半会儿,很快就四散了。
但是,九志想去仔细看一看那个婴儿,自己刚来时真是这个样子吗?或者,为什么,那个婴儿会和自己一样也来到这里?
育婴室没有人,九志推开门,里面有婴儿嘤嘤哭声,声音不大,断断续续,九志知道,可能是拉了或者饿了,但是,不到时间,是不会有人来的,这些婴儿们别看混沌未开,却也懂,那哭声也是抑制而细微的。
靠窗的那个小床原本空着,有一个可爱的女婴,前天被人领养走了。那个女婴据说是被丢在院门口,一晚上没哭没闹,一大早看门的卫爷爷一推门,那个女婴传来两声咯咯笑,脆朗朗的,卫爷爷低了头才发现是个粉扑扑的孩子,这才抱了进来。保姨带去医院检查了一遍,没有任何毛病,保姨叹了一声,作孽。没过几天,那个女婴就被一对夫妇抱走了。然后,又没过几天,这个原来空着的床又来了这个小婴儿。
九志站在床前呆愣了片刻,突然伸了手去摸裹着婴儿的包被,摸了半天,才恍然,噢,也是个女娃。然后,九志又去摸婴儿的小脚丫。九志的举动并没有惊动女婴,她熟睡着,脸上很舒展,她太小,不知道她的前生今世,更不可能预测自己的将来。不要说她了,九志都七岁了,他的将来是什么,他都是糊涂的。
保姨总说,你好好上学,好好读书,齐家也不会亏待你,读书才能读出个好将来。
那时,九志就站在墙角,看着保姨整理别人捐赠的衣物,旁边是玲姐手脚勤快地在帮忙。
玲姐十七了,大九志整整十岁,也在读书。她是好运的,有人家领养了她,原本对她挺好,但是后来那家又添了一个孩子,到底领养的抵不过亲生的,人家对她也还好,只是这好是隔了一层的,如纱罩,朦朦胧胧不贴肉贴心。她渐渐懂了,也不痴缠,也不埋怨,只是时不时回院里待上个一天半天的,不等保姨催她,也不等那家来喊她,她也自觉回去。回院的次数多了,那家人也不便当她的面多说什么,私底下的话她也是听进半耳朵的,人家说,当初领养她时都六七岁了,大了记事了,现在养不家了。
九志想,自己也七岁了,大了记事了,也养不家了。所以齐家只助养却迟迟不肯领养他。这助养和领养是有本质区别的,助养只是供他上学,每周末带他回家住两天。说到底他还是他,齐家还是齐家。
保姨说,这有什么不好,只要他们肯资助你上学,这是顶重要的,你这么大了,也难融进去,与其别别扭扭地处着,不如就在院里待着,比起别人,你可是强呢。
九志也不是不明白,院里长大的孩子,总是比同龄孩子知事早。心里也感激保姨,保姨一碗水端平,每个孩子她都想给他们争个好出路好未来,可是残着的呆着的多了,你就是想替这些孩子争,也是没这个能力和可能。保姨也就把心思放在九志这些孩子身上,九志们的过去,保姨总是用两个字概括了——作孽。保姨不多说,九志也不多问,没有的注定生下来就失去了,何必追问。
保姨为九志争取的这家姓齐,齐家女主人原想领养一个女婴,偏那一段时间院里没有合适的,保姨就劝,你还年轻,又不是生不了,先助养一个孩子,说不定会为你们引来一个自己的孩子,这倒不是迷信,来我们这里助养的两口子后来又怀上孩子的可不少。
齐家女主人犹豫,大概就是觉得助养花了钱还不见得跟自己亲。保姨就说,这养孩子就如养小猫小狗,养时间久了,都是有感情的。助养能花几个钱呢,你们又是不缺钱的,每周你们带带孩子,享享一家三口之乐,别人看了也是赞你们的心肠好,再说你们助养他,他出息了也是惦着你们的好。保姨见男主人有些心动,就又推一把力,说,我们这里有个孩子,健健康康,安安静静,在学前班里学习都是好的,可招人疼,就看你们愿不愿意。
女主人顺着保姨手指的方向望去,那天九志就站在院里的花坛边,不知道为什么,九志在女主人看过来时,也抬了头,和女主人目光撞个正着。女主人面无表情,九志却目光一抖,低下了头。女主人还想说什么,却被男主人挡住了,男主人说,行,就是他吧。
保姨没有说谎,比起院里其他的孩子,九志是健康的,只有脱了鞋才会发觉他的左脚是没有大拇指的,那半个脚掌也深深地凹了进去。
男主人是周五下午五六点的光景开了车来接九志的。九志犹疑着不上车。保姨上前拉了一把九志,说,齐叔叔来接你,你赶紧去啊。
九志被动地走了两步,想回头,心里一挺,硬生生地坐进了男主人的车里。汽车开出院门时,九志知道保姨隔着车窗在挥手,也知道小苦瓜就站在院角吸着鼻涕在远远地看着他,但是他没有回头。
小苦瓜至今没人领养,也没人助养,他的胳膊一长一短,这在院里不算个事,可是伸到外人面前却也是触目惊心的。记得有人来捐衣物,小苦瓜兴奋,跑上前要帮人家提东西,胳膊伸出来时着实让来人吃了一惊。来人受了惊吓,却还得装着不在意的样子,半离不离地和小苦瓜把衣物拿进院里大堂厅。这样的距离小苦瓜是无知觉的,他不觉得自己残缺,他本来就什么都不缺。
小苦瓜说,九志好好的,我也好好的,为什么我就没有家?
保姨听了就扭过头去,剥了一颗葡萄塞到小苦瓜的嘴里,一嘴甜的小苦瓜立马忘了刚才自己为什么纠结,有了吃的小苦瓜就是快乐的小苦瓜。这真让九志羡慕。
坐在车上的九志浑身都是僵硬的,他坐在后面,一步不错眼地盯着前方,心里想着该怎样回答男主人的提问,这样家庭里的人总是对他会好奇一些才是的吧。九志真担心男主人会问一些他不想回答的问题,更担心男主人一旦问了,如果自己不说该是多么的造次和不应该,怕是到时男主人要生气的吧。但是,一路上,男主人只说了一句话,九志,坐好了,咱回家了。
九志就想,家?家是什么样呢?咱们回家,听着也是满心的亲切,可是,没来由的,九志就想冲下车跑回院里。但是,九志没有这样做,他懂得克制。
这一路男主人再没多话,只是按了音乐播放。感谢这音乐,没有言声也没人唱歌的音乐,静静在车里流淌,那流水般的声音像一把长长的小扫帚,缓缓清扫着车内的生分和尴尬。
随男主人回了家,家是温馨的,虽然看出女主人并不是很想助养一个孩子,但却也精心为他收拾了一个小房间,九志站在他的房间外满心的惶恐和满身的不自在。
女主人看在眼里,便站在饭厅里喊,九志,先吃饭吧。
这句话说处轻柔,像水浇着九志,九志人有了一些活泛,他看了一眼男主人,男主人径自走向饭桌,说,噢,还有红烧肉呢,九志,你最爱吃的。
九志心里热了一下,人刚准备坐下,却又听女主人说,去去,洗了手再说。话是对了男主人说的,却也惊了九志,九志赶紧抬起刚沾了座位的半个屁股,惶惶地站着。洗手间里传来哗哗流水声,九志突然有想小便的冲动,可是,忍着,必须忍着。但是,突然,裤档传来一股温热,九志心里一惊,大腿内侧一用力,那温热不待四散就被生生憋了回去。
九志,来吧,洗个手。男主人在洗手间里喊。九志逃也似的进了洗手间,慌乱地拧水龙头却不得要领。男主人一回头,说,把手放在水龙头下就可以了,感应的。九志脑子还是木的,手却已伸在了水龙头下,哗啦啦畅快的流水声一响,九志突然感觉后背也开了水龙头似的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刺辣辣的难受。
那顿饭吃的什么九志已经想不起来了,总之满眼花花绿绿的颜色,嚼在嘴里却不知道什么滋味,女主人总是说吃啊,九志,吃啊。女人主拿了一副公筷,时不时往九志碗里夹一些菜,再替九志盛汤时,男主人就说话了,你让他自己慢慢吃吧,这样反倒是让他不自在。
女主人犹豫了一下,却问,不自在吗九志,不自在吗?当自己家好了,这也是你的家。
女主人问时也并非全无方向的,她看着九志,九志赶紧摇头,然后埋下头去吃饭。女主人就笑了,把汤放在了九志面前。
这碗汤温温地冒着热气,九志知道自己已经饱了,可是撇下这汤却不合适,这是女主人盛的,里面还有香菇和鸡块,噢,是一个鸡胗呢,在院里哪儿会有这样好吃的东西,即使有,也不可能一整个的供你九志享用。九志端起汤碗埋头喝光吃尽那一碗的肉和汤。
这边嘴上还沾着油,那边却听到女主人在问,九志,在你们那里天天也能吃上肉吗?
是不是自己的贪吃相勾起女主人的好奇心?或者只是人家无意的关心一问?九志拿不准,自然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肚里撑着,脑子却是木的,呆呆地看着手里的空碗。
男主人扭了头看,说,九志,吃完饭就去房间写作业吧。九志低了头去拿书包,男主人对了空气蹦出一句,话多。九志知道这不是对他的,心里却紧张,怕女主人生气,可是碗碟相碰声中并没听到女主人再说话。她利落地收拾着残羹剩饭,很快厨房就传来洗碗的水流声,这声音让九志心里有那么一丝的平静。
睡觉前洗的那个澡真是让九志没法放松。九志写完作业,就听女主人说,九志,浴室里那个蓝色的包就是你的洗漱品,全是你的,不要拿错噢。
九志也怕拿错,自己一个陌生人,来到别人家,处处也是小心谨慎的,吃的用的,哪一样自己都要分清,不能让别人厌嫌。
九志也不是没心眼没心思,保姨说得好,助养并不是图有个家,而是有人家肯出钱资助九志上学。这个学和在院里提供上的学可不一样,院里也会让九志们上学,可哪里有什么好的条件,有人家肯资助就不同了。这齐家原不想助养,经保姨说得动了心,也可能是女主人很想通过助养九志为自己带来好“孕”吧。男主人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广告公司,手里自然有些钱,既然答应助养,便事事做得周全。托人找关系把九志送到一所实验小学,若九志有出息,就打算供他上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他若不肯读,大学毕业看他的造化了,男主人女主人费了心尽了力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九志。
保姨说得对,九志也都明白,自己毕竟知事的年纪了,人家轻易不肯领养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因为养不家。再说,真要有人不在意这些,领养了九志,怕是九志也是难适应的,七岁以前的记忆哪里说抹就能抹去的,适应一个新家,也许几年,也许一辈子,好比玲姐,要自己跟自己别扭几十年,想想都让人害怕。
九志也有不知轻重的时候,九志说,我能不能就在院里一直长到我可以自食其力?保姨就眼望了别处,想了半天,才说,你倒是甘心呆在这里一辈子,就这些钱,这么多孩子。保姨的话总是说一半吞下去一半,但是九志全都懂。
九志小心地进了浴室,换气扇开着,嗡嗡声像是有几十只蜜蜂在里面飞舞。那个蓝色的包就悬挂在醒目的镜架下,九志是穿着袜子进来的,他在齐家就一直穿着袜子,他想不让他们看到他的脚,他就是健康的。原以为会很尴尬,想着在男女主人刚用过的浴室里洗澡怎么都是不自在的,进去,才发现,里面干干净净,女主人来回在客厅和里间穿梭,最后还从里间拿出一把梳子,九志才知道原来里间也是有浴室的。九志这才放了心。
以为会是一个不眠夜,可是洗完澡倒在松软的床上,都还来不及跟院里的床作比较,瞌睡就如海绵般把九志的大脑塞满了。九志紧绷的神经在那一刻放松,人就渐渐沉入梦的海底。原来,一切也并非如他想的那般紧张,只要你放松,只要你都当这是必经的,闭着眼横着心走下去,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只是,在这张床上睡了大半年,九志就睡不踏实了。
那一天是男主人打电话说要出差,让九志自己坐车回家。九志正犹豫要不要回院里。有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至今没结婚,想领养小苦瓜以便老有依靠。那人姓魏,来看过小苦瓜几次,也是满意的,小苦瓜跟九志说过这事,满眼也是期盼的,两两都愿意,怕是最近就要办完手续领走小苦瓜了。九志想,这个周末如果不去齐家,倒是可以和小苦瓜好好聚一聚。
可是,没等九志犹豫多久,女主人就来电话了,九志的电话就是女主人给的一个旧手机,每月存一些话费,主要是便于男女主人跟九志联系。女主人说,你回来吧,我做好了冬瓜排骨汤。
九志回到齐家,那一汤盆冬瓜排骨汤赫然摆在桌上,女主人低头坐在沙发上,怕是在想什么心事,九志开门都不曾惊动她。九志愣了下,站在门口晃动了两下钥匙。
女主人这才惊醒过来,噢,九志回来了,快吃饭吧。
九志去洗手间洗干净手,捧了碗喝了两口汤,一抬头发现女主人半个脸凑了过来。九志一愣。
女主人挤出一抹笑来,想了想,问,九志,你叔叔每星期都是一个人接送你吗?
九志端碗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该如何回答?男主人并不是次次都是一个人来接他,有一个女人,九志遇到过三四次,三次还是四次,真是记不清了。那个女人就坐在副驾驶,回头冲九志明朗地微笑。那个女人从没跟九志说过一句话,而且每每在半路就下了车,男主人会在那个女人走出好几步后按一下喇叭,那个女人就回头冲车里一笑,然后再走,清爽利落,但是九志却莫名觉得有一种搅不散的黏稠在女人与车越来越远的距离间飘动。九志窝在后座上不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知道自己不该说。
女主人眼里有了希冀,只是这希冀带着一抹狠烈,女主人说,是一个人吗?是吗?
九志的手死死抠着碗沿,他努力不让这双手露出颤抖的破绽,心里飞快却又迟钝无比地想着能有一个最贴切的回答。男主人从来没有明示或者暗示过他,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况且,男主人和那个女人并没有什么,起码在九志面前并没有过什么,这个九志不能乱说。七岁的孩子,还是院里长大的孩子,总是知事早些,看不懂的都要努力看懂,学不会的都要努力学会。
但是,女主人也并不过分,她不过就是想弄清楚男主人是不是总是一个人接送他而已,他可以据实回答是还是不是。可是,不管回答是或者不是,结果呢?那该是怎样一场风暴?说是,这风暴就会骤起,说不是,如果男主人跟那个女人没什么倒也好,如果有什么,将来让女主人抓个正着,那九志又如何脱得了干系?说轻了,九志是撒谎者,说重了,九志就是同谋,那时再起的风暴怕是会更惨烈吧。
到底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九志觉得自己被淹没在一片波涛汹涌中,不得露头,严重缺氧的感觉真是让人窒息。就在呼吸困难不知所措中,九志听见女主人说,我知道了。
这真让九志疑惑。九志看着女主人,嘴里如嚼了一团乱麻似的吐不出一个头绪,只能笨拙地张着。
女主人看了一眼九志,说,吃饭吧。女主人端起饭碗,扒了两口,突然又一抬头对了九志,说,谢谢你,九志。
九志更惶恐了,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帮她,为什么要谢他?
女主人在九志惶恐的眼神里转了一圈,然后笑了笑,再开口时话里努力透出一些轻松来,九志,你还是个孩子。
九志看着女主人挑起一块烂熟的冬瓜,他以为女主人会放进嘴里,谁知女主人却把它放在面前的盘子里,筷子在那熟烂的冬瓜上戳来戳去。
九志,我是不会再有孩子的。女主人又一抬头,看着九志,眼角有一些波光在流动,这件事我对谁也没说过,告诉你也无妨。
女主认真地看着九志,说,你嘴紧。
这话让九志后背长刺般扎得难受,他听得出好赖话。
女主人还在戳那块冬瓜,手没闲嘴也不肯闲下来。我那时小,喜欢一个人,呵呵,现在想想,喜欢是什么呀,爱是什么呀,傻啊!算了,过程就不说了,说主要的吧,我怀孕了,当然了,那个人不肯承认,跑了。那个孩子,我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可是我不敢声张,想丢掉这个孩子,可是我的房东,平时为十块八块钱房钱都不肯对我让步的房东,居然帮了我一把,说可以联系一家人家领养这个孩子,会给我一些钱,条件是我必须从那个城市离开永不回来。我当时也真是小,房东说给一些钱,我原以为不过千把块,可是拿到手却是沉甸甸的三摞没开封的百元大钞,三万啊,我当时就蒙了,害怕人家反悔,拿着钱当晚就跑了。后来,我住到我一个亲戚家,身体并没有恢复好,下面一直流血,持续了一年多,等我明白过来想珍惜自己时,都晚了,我要不了孩子了。我在这个城市里找工作,把自己装扮成纯真的小姑娘,我知道我已经不是的,可是我想回到过去,我想过正常的生活,再后来,我遇上了齐永年,我们结婚了。他不知道,这么多年他一直想有自己的孩子,现在,他怕是等不及了吧。
吃饭吧,吃饭。女主人叹了口气,丢下那块已被戳得稀烂的冬瓜,伸手又舀了一碗汤。女主人的往事在她肚里早被煨熟了,一如那块冬瓜。可是,对九志来说,却是凭空抛来的一块生铁,咽下去哪就那么容易消化。九志呆坐在饭桌前,米饭粒粒都是铁砂,那汤口口都是溶化的铁水,硌心烫胃,如何安生?
晚上正在做作业,听到有人敲门,女主人却坐在电视机前并不起身,九志只得丢下作业去开门。门开了,却见一个人影匆匆闪过,九志正纳闷,一低头看见一个包裹,噢,跟院里育婴室里裹婴儿的那些包被一模一样,连花色也一样。九志心里一惊,弯腰细看,这一看不打紧,着实惊了九志一身冷汗,那个包被里裹着的却不是婴儿,那张脸好熟悉,是谁?再一细探,天,这不是九志吗,就是九志啊,可是,自己明明是站着的,怎么会被裹在包被里?是谁把自己丢在这里的?那个匆匆闪过的人影呢?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好好看清楚,为什么每次都看不清?九志飞快地追出去,谁知太急太快,一个踉跄,头冲地就裁了下去。
九志惊急地大喊了一声,人也就醒了。是梦,九志知道是梦,没有窗外,窗外被厚重的窗帘遮挡住了,这个小区很安静,静得九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声声如临战时敲打的鼓点。自己喊的是什么,不知道。但是那个一闪而过的背影,九志坚信自己真的见过,那不是梦,是真实的。都说人是要五岁以后才有记忆,自己不可能记得刚出生时的事,更不可能记得刚出生时的人,更何况一个背影。但是九志坚信自己见过那个背影,九志曾跟保姨说过,保姨想了想,很认真地对九志说,如果忘不掉,那就牢牢记住吧。
风暴终于来了。
男主人出差回来,再一次把九志接回家时,女主人摊了牌。只是女主人张了手肩想搂住太多东西,男主人当然不肯让步。九志躲在屋里,不是他想避开,而是这家男女主人并无意让他参与,多年的夫妻眼见要成陌路,更何况他本就是一个外人。可是女主人慌不择言偏要扯上九志,女主人扯大嗓门,你和那个骚女人的事,九志都跟我说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自己找好了退路,还想掐断我今后的生活吗?
男主人一听,眼睛便开始寻找九志。九志噌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那个转椅是可以调节的,当初男主人说方便九志写作业累了可以转动椅子休息休息。那个转椅在九志站起身的那一刻,突然一弹,骨碌碌滑出好远,直到撞在墙上才作罢。
哪里来再回哪里去,九志的生活并不曾改变。还睡他那张小床,只是边上那张床换了木鱼儿,木鱼儿残在头上,头大,却是智障,一天到晚傻笑。有一群志愿者来院里,对着镜头,好多人都上前来搂着木鱼儿,还教木鱼儿看图识字,在木鱼儿傻呵呵的笑声中,闪光灯闪个不停。可是,镜头扫过,木鱼儿就冷清了。那些捐赠的零食,夏凉被,院里的阿姨都收了去,丢给木鱼儿半袋炒脆角,木鱼儿嚼得咯嘣响。
小苦瓜走了,去了山东,老男人说要带小苦瓜换一个地方开始全新的生活。院里也不是完全放心,对老男人进行了细致调查,确定可靠才点了头让小苦瓜走。
玲姐说,还是要定期联系的,不然像断了线的风筝怎么行,现在卖人体器官可值不少钱。
小苦瓜居然给九志打过一个电话,也是急匆匆地,像是有人在追赶他,九志,九志,是你吗?你还在上学吗,我想你。
九志是在放学的路上接到电话的,九志原以为那个手机再不会响起,谁知不仅响了,打电话的人还令他很兴奋,小苦瓜,你现在在干嘛?你好吗?
小苦瓜告诉九志,他在村里给魏伯喂猪,三十多头猪,每天光喂猪饲料就得百十斤,全是小苦瓜天不亮就起来搅拌猪食,然后用手一桶一桶提去喂那些嗷嗷叫的猪。小苦瓜说我的手都磨破皮磨出血起茧子了,魏伯说等养猪挣了钱就送我去上学。九志,我想你,你来看我吧。
小苦瓜原本还想跟九志说一件事,可是话到嘴边又哽了下去,还是算了吧。那个姓魏的老头儿倒是不打他,喂猪算得了什么?姓魏的老头儿领他回来时向院里交了一笔可观的保证金,总得要让他用劳动偿还吧。只是,每每睡觉时,姓魏的老头儿都会把他脱光,用手摸他的小鸡鸡,嘴里还哼哼有声,那样子不知是难受还是享受。起初小苦瓜很害怕,后来也就习惯了,太累了,每天提一百多桶的猪食,累得浑身散了架,走路都打飘,倒在床上就跟死人一样,就是拿刀砍也醒不来,摸几下又算得了什么?
九志一想到小苦瓜用他那长短不一的胳膊去提一桶又一桶的猪食,歪歪倒倒走路的样子,心里就觉得扎疼。他不敢跟保姨说想去看小苦瓜,九志把保姨为他辛苦争取来的机会给弄没了,保姨虽没说过什么,可是九志知道保姨是惋惜的。
倒是玲姐来安慰九志,玲姐说,别放在心上,这不是你的错,也许是他们做的一出戏。
九志愣愣地看着玲姐,玲姐就笑了,说,我是瞎说的,你看你装的这个盒子多漂亮,九志,你天生手巧。
九志就看自己手里的那个音响盒子,他知道玲姐在转移话题,好在他也不想追问,问与不问不是都已经有结果了吗。九志每天给自己定任务,假期里,院里要求每天每个孩子至少装五十个音响盒子,每个盒子可以拿到一毛钱,九志就要求自己装一百个盒子,他不残不呆他可以完成,而且这样他就可以每天拿到十块钱,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攒足去山东的路费。
玲姐像是生来就会看人的脸色揣摸人的心思。玲姐说,用不着这样拼命,这才几个钱呢?
停了片刻,玲姐很认真地看着九志,你真的这么需要钱?
九志想了想,点了点头。玲姐却一低头,把那个音响的后盖使劲一拍,那个音响就严丝合缝了。玲姐再没说话,九志有些担心,刚才自己那一点头,她到底看见了没有。不过,就算是看见了,她能有什么办法呢?说到底,她也还是一个孩子。
九志的手也起茧了,这样的计件活九志以前也做,剥干玉米粒、给铅笔装盒,那时候还不会数数呢,只知道把那个盒子装满准没错。再大一点就是捋铜丝、给食品袋贴合格标签,总之院里领回什么活,九志他们就做什么活,报酬虽少,但计件,多劳多得,九志先前攒过一笔钱,他偷偷算过,大概有一百来块吧,他们这些孩子都太小,脑子难得有清楚的,手脚难得有利落的,攒下的钱都会交给院里的阿姨保管。那时,九志的钱是交给文姨的,只是交去了后,文姨再不提及,九志也全当没这回事,他吃着院里住着院里的,钱对他来说有自然好,没有也能过。后来保姨接手照顾九志,九志也大了,九志也交过钱,保姨说开个户存上吧,将来上学用。保姨还真给九志开了个账户,把那百十块钱一点一点替九志存进去,每到过年就拿出来给九志看,保姨会笑着说,九志,你是小富翁噢。九志心里就很踏实。
就在九志做够第六百个音响盒子的那一天,院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育婴房的一个女婴丢了。
这让当天值班的文姨很害怕,她站在院长室里大声哭大声申辩,我只是去了趟厕所,你知道我切了胆,肠胃很不好,我只是去了趟厕所,谁知道孩子就丢了。院长平时并不出现,只是年节过来看看,今天若不是丢了女婴这么大的事,九志们难得看到院长。九志看见矮胖的院长坐在办公桌前,只露出大半个脑袋来,样子有一些滑稽。院长说监控呢?文姨嗓门更大了,平时监控都是好的,谁知道昨天偏就坏了,院长,您得查个彻底,还我清白啊。院长肿涨着脸,拍着桌子说,报案报案。婴育护理长一听,赶紧上前,说,这个女婴前天才送来,还没有登记上报,这一闹怕是……您看……院长抬头盯着护理长,护理长低了头再不说话,院长就一扫四周,那眼神划过九志们的头顶,却又极快收了回来,院长压低声音说,关门关门。
下午,玲姐过来,凑在保姨身边小声说着什么,九志正坐在保姨的脚头,那话声再小也能听进一句半句。玲姐拍着音响盒子,遮着自己的声音,压了嗓子说,钱,怕是她们都分掉了吧。也不是第一次丢了,还弄得这样兴师动众,做给谁看?保姨的头深深埋下去,她把玲姐做好的一个音响盒子放在一旁的纸箱里,叹了一声,作孽。
九志听了,觉得整个人都随着保姨那长长的叹息一路滑下去,冰凉的,不见底的。
小苦瓜再没来过电话,九志跑到街对过的电话亭去打电话,他的手机欠费停机了。接电话的人很不耐烦,说,不知道,不知道,我是公用的。九志明白了,原来小苦瓜跟自己一样是趁空偷偷跑出来打的电话。
找不到小苦瓜,九志想去看他的心思就更加粘稠。九志蹲在电话亭边,低着头,有蚂蚁在他的脚下转着圈,不知道是迷路了还是怎么了,一遍一遍不肯离去。九志想,也不过是大半年前,他和小苦瓜还在院里一起看蚂蚁,现在,他们都各自散了。正看着蚂蚁,却觉得眼前暗了下去,一抬头,发现玲姐就站在跟前。
玲姐高高地站着,俯看着九志,很快也蹲了下来,蹲下时还向四周看了看。玲姐说,九志,我想去广州,或者深圳。
停了半晌,九志以为玲姐没话了,却又听玲姐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再开口时话却是七颠八倒的。我那个妈想让我嫁给她们一个死了老婆的局长,我才多大?她告诉我嫁过去就能吃香的喝辣的,有享不尽的福,怕是他们一家才有享不尽的福吧,我才不傻,都能当我爷爷的人了。九志,跟我走吧,我有钱,一万呢。玲姐结结实实拍了两下窝在怀里的手提包,有梆梆的响声传来,很厚实。
玲姐盯着九志,突然抬手在九志头上敲打了一下,说,你怎么总是这种呆傻样?还不明白吗?没有我,文婆子和护理长什么事也办不成。玲姐打了九志,却又伸手帮九志整理起头发,九志,跟我走吧,我供你读书,你能有出息的。
九志愕然地看着玲姐。有风吹起,把玲姐的头发吹到九志的脸上,九志挠了一下脸,却感觉并没有挠对地方。那个厚实的手提包还在玲姐怀里窝着,九志匆忙扫了一眼,整个人不自觉向后一退,因为蹲着,后退时并不稳当,好在电话亭的立柱挡住了他的后背,他没有摔倒。
干嘛?干嘛这是?你害怕了?觉得我坏是吗?我可是好人,我给那个婴儿找了一个好人家,她长大了得感谢我。九志,你别天真了,这里每个人都分过钱,包括——玲姐把脸凑到九志面前,盯着九志——包括保凤珍,大家都有份才不会有告发,明白吧你个猪头。
玲姐举起手又想敲九志的头,九志一抬手打开了。玲姐看着九志,九志盯着玲姐。九志想站起来,他想回手给玲姐一拳,她真的该挨揍,她不该提保姨,不可能有保姨,她骗人的,骗人的。
可是她为什么骗他?为什么?九志不知道,也理不出个头绪,脑子就像被洪水袭击后的地面,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不等九志起身,玲姐已经站起来了。她把手提包紧紧攥在手里,再不看九志,只是丢下一句话,九志,你好自为之吧。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色渐渐暗沉下来,那暗中还透着让人憋闷的昏黄,怕是要下雨了。九志抬了抬身体,却发觉脚下千斤般沉重,有无数小虫从脚底向腿上麻滋滋地爬上来,九志低下头,恍惚发现那是一群黑压压的蚂蚁,你挤我压,正奋力向上蹿,一波一波,此起彼伏,如浪潮一般,劈头盖脸,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把他吞没了。
责编:朱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