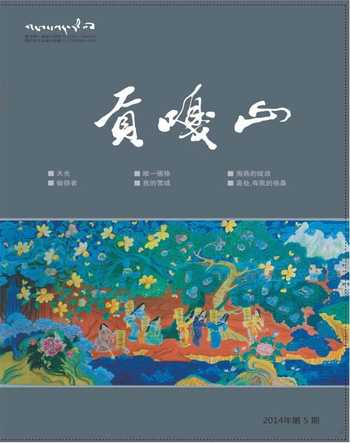阿普和他的“猎皮烟兜”
沈林清
在彝民族社会中,子孙辈们叫爷爷都喊阿普。
小时候往往因调皮捣蛋、激怒父母被训斥时,阿普便成了我们临时的“避难所”和“依靠树”。此时,阿普会敞开胸怀,把我们紧紧抱在怀里,并把生气未消停的父母教训一顿,“我的乖孙孙,明天阿普带你去摘最甜的野草莓吃……”不停安慰着,让自己受伤的幼小心灵得到及时的慰藉。
记忆中的阿普,中等个儿,时常戴着用青色纱布做的丝帕子,帕子的一端裹着短而无尖、呈卷状的锥结,里面装着一块干净的毛巾,天太热时,阿普会取下毛巾擦擦汗水。身穿黑色呢子中山服和浅蓝色大脚裤,裤脚边上镶有五寸长的青布一层,青布上面镶有边,裤裆外则镶贴着三颗对称的圆形贴花。腰上系着一个弧形猎皮烟兜,烟兜有兜盖,里面装着旱烟、烟袋、火镰、火石和火草等,那双长有约寸把厚茧的脚,从来没有穿过鞋子,因为阿普生活的那个年代农村特别贫穷,阿普从小没有穿过鞋子,也就养成了不穿鞋的习惯。阿普的这身穿着,在我心中牢固树立了八十年代康巴彝区老者英俊洒脱的形象。
阿普做农活很讲究,据父母告诉我们,在农村,春耕备耕来临之际,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各自都要把自家的土地好生整理一番,或者敲粹土疙瘩、捡小石子儿,或者烧前年遗留的秸秆,都想把土地整理好,打好基础,精耕细作,等待来年有大的丰收。在做这些备耕农活的时候,邻居们都会背着自编自制的篓筐,三五成群,分工有序,各司其职,一天下来,往往都累得汗流满面,腰酸腿痛。阿普却不和他们一样,从来不与其他哪个人组合,也不蛮干,而是左手卷起自己时常穿着的查尔瓦左角,右手往查尔瓦里捡石头,嘴里不停哼着“阿依妞牛”,每次捡的不多不少,刚好合适,别人还没有走一圈,阿普已经走了十几个来回,而且还不感觉累,偶尔停下手中的活儿,歇在地角悠闲地吸着兰花烟,看着其他人的劳作,虽然最后阿普会推迟些时间完成土地的整理,但始终没有影响春耕备耕的进度。细想起来,阿普采取的这种劳作方式,确有其方便快捷之处,就是以小积大,又不累人,而且在劳作中感受了乐趣。阿普的心理始终装着别人,对自己则要求过得去就好的原则,刚实行包产到户时,集体的土地要分到户上,作为一家之主的阿普,分土地参与者当然不能少了他。阿普随同村里的同胞们一起分地,总是先让别人挑选完后,自己把别人不要的土地接了下来,所以,阿普家分得的土地,要么是处于最远最偏僻,要么是土质不好,要么就是四分五裂,没有一块是上等或中等的土地,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在后来的劳作过程中,因为土地贫瘠、劳作量大,无论施肥、浇灌或换种上如何想办法,农作物长势始终不尽人意,与其他邻居家相比,粮食产量低。奶奶、伯父等一家子人都很有意见,阿普却不以为然。
除此之外,阿普还有自己的绝活——会做“猎皮烟兜”,因为有了这门技术,给阿普带来了不少实惠,故那时阿普家的生活始终比邻居们好得多。因为那时的大脚裤没有裤包,佩带烟兜就成了穿大脚裤且习惯抽兰花烟的彝族男人的必备工具,犹如今天的大都市里“上班族”、“经理老总”们携带的真皮包,形影不离。物以稀为贵,阿普所做的“猎皮肚兜”虽较昂贵,当时市场价在两元左右,有钱的给钱,一时没有钱的用粮食换取,或者赊账一段时间,等手头宽裕了再给,阿普始终没有计较,有私交、感情特别好的阿普还经常免费送他们。至于阿普做烟兜的独门手艺,或许是祖爷传给他,或许他从其它地方拜师求艺,或许是阿普自己看到类似于烟兜的形状独创而来……我们没有仔细追溯和考究过。那时的阿普,农闲时节主要承担家里的放牧任务,当然还没有进学校的我,就成了阿普的得力助手。阿普带着我们,手提装着猎皮和做烟兜工具的挎包,把马、牛、羊等赶进山坡后,嘱咐我们好生放牧,自己则找了一个地势较高、视野宽广、能够眼观四方的地方,铺开他准备的猎皮和各种工具,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放牧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有时阿普会偶尔停下手中的活路,歇下来抽顿兰花烟,随便观察马、牛、羊的走向,并不断高喊我的名字,嘱咐我马、牛、羊要到哪里哪里去了,要快点赶到哪里……如果连喊两三声,仍然没有回应,阿普就会冒火,甚至暴跳如雷,有几次与几个伙伴一起在河边戏水,因为水流声和玩性大的缘故,忘记了自己放牧的任务,阿普喊了半天没有任何回声和见到人影,后来找了半天才找到我们,当然,结果可想而知,阿普不知是早就准备了还是现找起来的,拿了约有三尺长、手指宽的竹条,把我和几个伙伴在河边就地进行了惩罚。这以后,放牧期间我们谁也不敢再吊儿郎当了,到河边去戏水成为儿时的一种奢侈品。
阿普做的烟兜的材料不是一般的,而是用獐子皮或麂子皮做的,做工精细,质地优良,经久耐磨,携带方便,颇受穿大脚裤的彝族男人的青睐,远村近邻经常有人登门来买或来订做,随着猎皮烟兜的销售,阿普会做猎皮烟兜的事也在彝区山寨逐渐传开,其知名度不断提升。大家都把阿普亲手做的猎皮烟兜视为“名牌”,以佩带阿普做的猎皮烟兜为荣。那时,居住在深山老林的彝族人们都有打猎的习惯,有的会安索子、有的家里有猎枪、有的家里喂养猎狗……在我的记忆中,阿普家曾喂养过一只猎狗,给猎狗取了名为“伟惹”,意为勇猛无敌,据说它为阿普获取了很多猎物,阿普对待它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每每开饭时,阿普首先给猎狗喂饭后自己才不慌不忙进屋吃饭。阿普家堂屋的右上方经常挂着一把擦得亮晃晃的“爪爪火”猎枪,每隔一段时间,阿普会选择天气晴朗的日子,把猎枪取下来,专心致志地给它上油,用一块白棉布把枪擦得亮晃晃的,但从来不允许我们去碰它。进入秋季后阿普会带上村里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牵着猎狗,背上那把猎枪,带足够四五天吃的糌粑、土豆及其他干粮,到深山老林打猎,儿时的我们就像等待过年似的盼望着阿普进山打猎,因为那时农村生活非常困难,很少吃上肉,如果不是逢年过节,连油腥都嗅不到。只要阿普他们一进山,意味着就要吃上肉了。阿普他们从没有失败过,每次都是满载而归,猎肉就分给邻居各家各户,獐子皮、麂子皮则全归阿普,其他人进山打猎,猎皮都会主动送给阿普,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猎皮对阿普有用。所以无论阿普进没进山打猎,都有人会给阿普送来猎皮。阿普在牛屋后挂了一根约有三寸宽的圆木杆,上面挂满了各类猎物皮,视这些猎皮如珍宝,隔三差五要检查一番,担心猎皮会被虫吃或被雨淋湿。农闲时节,阿普会提前把几张皮子放入木桶里,盛入足量的水,泡一至两天后,再捞出来刮掉所有毛,在阳光下开始搓成软绵绵的,然后再根据需求设计裁剪成若干个小块,有的两层、有的三层、甚至更多。根据需求者的要求来设计,用自制的浆糊把一块一块已经揉得软绵绵的猎皮粘在一起,之后在专用的缝针上连起已经剪成细细的猎皮线,沿着粘好的猎皮周边开始飞针走线般缝起来。于是白天阿普就做獵皮烟兜,放牧归来,来不及收拾就着手泡猎物皮子,准备第二天的活路。牛屋背后的那窝老花椒树下,已经堆了厚厚的皮毛,阿普习惯把刮下的皮毛堆积在花椒树下,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各种各样的鸟雀就齐集在花椒树下,鸣叫声此起彼伏,寻觅软弱的皮毛,达窝建棚,繁殖子孙,时有嘴里衔着皮毛的鸟儿一只接着一只从老花椒树下扑腾而起,儿时的我们经常躲在老远处,小心谨慎地观察着鸟儿飞去的方向,跟踪寻找小鸟的窝,还颇获丰收。
阿普去世在初夏的一个上午,那天我在跑通校路途中遇到邻居们用担架把阿普从区医院抬回来,我哭着要跟他们回家,但躺在担架上面黄肌瘦的阿普,用那双做出了N个猎皮烟兜的手抚摸着我幼小的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乖孙子,快点去上学,要不迟到了,晚上回来阿普带你捕鸟去……”。放学回家时,阿普已经闭上了双眼,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年我刚好八岁。阿普的去世,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
阿普去世后,父亲和伯父都没有承传他的手艺,把阿普生前做好还没有来得及送给买主的一大堆猎皮烟兜托人带给它的主人,后来,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村里打猎的人逐渐少了,猎枪都上缴了,猎皮再也找不着了。同时,人们思想观念改变了,穿大脚裤的人少了,佩带猎皮肚兜的人也就逐渐少了,村里再也没有会做“猎皮烟兜”的老者,阿普做“猎皮烟兜”故事也就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漠。时隔三十余年,偶尔看到稍上年纪的老者带着当年阿普为他们制作的猎皮烟兜,一种温暖的清风扑面而来,倍感亲切,阿普的那些年、那些事在大脑深处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