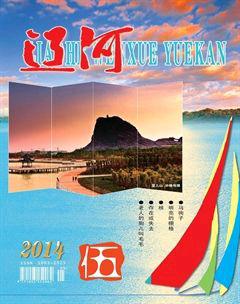老人的狗儿叫毛毛
恨铁
作者简介
恨 铁 本名孙开国,湖南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二级。1984年开始练笔,1993年在《青年文学》发表处女作,迄今在《北京文学》《啄木鸟》《清明》《上海小说》《星火》《芳草月刊》《广西文学》《小说林》《小说月刊》《黄河文学》《辽河》《创作》等刊发表中篇13部,短篇10多篇,并有作品入年选本或获奖。
老人的狗儿叫毛毛。这名字并不是老人下意识取的,老人又不是城里嗲声嗲气的小丫头,一辈子吃粗粮干粗活,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因为记也是白记,名字是给别人叫的,可别人根本不叫他的名字。从小开始,别人就叫他“老人”。开始只是绰号,后来居然一直延续下来,叫到老。都这样了,老人哪还有给一条狗儿取名字的兴趣?老人的儿子叫毛毛,这倒是老人自己取的。虽然算不上正儿八经,谁家的孩子小时候都这么叫,但老人第一声喊出来时就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取这名儿,让别人一辈子把毛毛当孩子,那样就显得毛毛永远年轻,也算是给自己扳了回本。
那条狗儿,是老人刚有毛毛那会儿,河对岸的小老头送的。小老头家里养了条母狗。猪四狗三猫儿打单。母狗三个月就要下一窝。小老头的母狗年年下四窝,窝窝三四条,没那么多人主动上门,小老头只好东家西家送。每年送四次,担心别人不要,小老头每回行动前都要帮别人找个养狗儿的理由。当初,他就抱着小狗儿,嬉皮笑脸对老人说:“老人,毛毛不能光吃不拉,养条狗儿你该要少动好多手脚吧?”
老人那时候还算不上老,刚刚50岁。老人一辈子没讨女人,毛毛也是别人送的。那个襁褓送过来才几天,老人心里正乐着。养儿防老,这辈子终于有了依靠。望着小老头捧在手中的小狗儿,老人说:“那我们讲好,等毛毛会跑茅坑了,我再把狗儿送回去。我没闲钱养畜生。”
“好吧好吧。只要你愿意,到时候连毛毛一起送我我都受了。”
只是,毛毛一天天长大了,一年年长大了,现在都已经在外闯世界了,但老人却把还狗儿的事忘到了爪哇国。真要还的话,最迟十年前可以行动的。十年前的一个秋日,六岁的毛毛上学了。按照小老头的说法,早不需要狗儿帮毛毛收拾屁股了。毛毛上学第一天中午,老人从地里回家,脑筋没拐过弯来,稀里糊涂把毛毛上学的事给忘了。老人提着一条还在垂死挣扎的草鱼,还在屋山头,就轻一声浅一声地喊:
“毛毛你饿了吧?快帮我抱柴,我给你弄好吃的!”
直到喊完话不见毛毛迎出来,老人才意识到自己糊涂了,还抿着嘴拍了几下自己的后脑勺。哪想到他话音未落,那条狗儿就一阵风杀过来,比平时毛毛在家时还兴奋,哼哼唧唧,摇头摆尾,恨不得蹦到老人头顶做窝。
“去去去,你又不是毛毛。”
老人对着狗儿头,真真假假扬了下巴掌。老人以为狗儿会逃之夭夭。但狗儿死皮赖脸,似乎想借毛毛不在家的机会,好好撒会儿娇。一个箭步冲上去,靠后腿把整个身子立起来,前腿比人的手还灵活,趴上老人肩头,不由分说伸出长长的舌头,舔了老人的老脸一口。老人再给狗儿一巴掌,真正的一巴掌:“你个狗日的,把我当母狗了?去去去,我要做饭!”
狗儿似乎听懂了老人的话,真的不和老人纠缠了。但出乎老人意外的是,狗儿蹦蹦跳跳跑过去,转眼又蹦蹦跳跳跑回来,嘴里还咬着柴火,直接窜到了灶门口。
“你这狗日的,当初是不是投错胎了?”
老人笑骂,但不一定是感到多么稀奇。老人明白,狗儿帮自己咬柴,完全是跟毛毛学的。毛毛从小就喜欢跟在自己身后没事找事,不让他干的事总想干一箩筐。刚走得稳路时,老人去柴棚抱柴火,毛毛也要拿个一根半截才满意。久而久之,连狗儿也学会了讨嫌。
从那以后,老人、毛毛、狗儿,就成了真正的一家三口。老人下地,毛毛就和狗儿看家。老人回家一声毛毛,毛毛和狗儿一起迎接。老人那天送毛毛上学,狗儿也跟着赶脚。到了学校,毛毛不想丢下狗儿,狗儿也不想丢下毛毛。直接钻进毛毛的座位地下,吓得别的孩子哇哇叫。老人跑过去,摸摸狗儿的脑袋:“你个畜生!难道也想认字?认了字也没用啊。走!我们回家!”
狗儿真的起身了。一边哼哼唧唧摇头摆尾一边起身,出门时还扭过头来,抬起一只前腿闪了闪,似乎在跟老师和同学们说再见,让一屋的孩子马上破涕为笑了。
回到家,老人要下地。狗儿又蹦蹦跳跳赶脚。老人回头,又一扬巴掌:
“回去!帮我看家!”
狗儿哼哼唧唧,夹着尾巴低着头,极不情愿的样子,但最终摇回了狗儿窝。
二
就是这样一条狗儿,后来说没就没了。老人连哭都找不到理由。那毕竟是个畜生,乡下人找不到哭一条畜生的理由。
老人的毛毛也没了。或许还有,但老人不知道毛毛去了哪里。毛毛读完初中后,没钱读高中,十五岁就拿着别人的身份证出门打工去了。老年得子,老人一直把毛毛看得娇了一些。但那种娇自己都说不出口,无非没让他冻着,没让他饿着,凡事都依着他。如果现在说出来,恐怕狗儿都要笑掉牙齿。毛毛成绩一直不错,想读高中,老人也想让他读。只可惜高中要很多钱,老人想不出钱来,连乖话都拿不出一句,杵在那里像个树蔸,毛毛才发飙:
“算了算了,到底不是你生的。养的没得生的亲!”
老人一愣:“哪个烂舌头的说你不是我生的?那你是谁生的?”
“哼!何必呢?你救了我一条命就该记在千年树上,现在该我自己去撞生死了!”
老人没话说了。毛毛都要离开了,还要将老人一军,多少让老人有些想不明白。想想十五年,老人真想哭一回。直到毛毛真正离开时,老人又想,让他去打工吧,那样总比在家里闲着好。出发前,毛毛似乎不赌气了。老人一言不发,给毛毛准备了一包衣裤。尽管那是从村里领回来的救济衣,但都是大半新。毛毛说,挂在身上像张网,不要!现在也穿不上,我是去广州,那里的冬天都热死人。老人又拿出一包用塑料布包好的荞麦粉,炒都炒熟了,加点开水砂糖,一搅拌就能吃。毛毛更不屑一顾:我又不是去讨米,早就吃得想呕了。老人没办法了,磨磨蹭蹭摸出一叠零钞,十元二十元的,加起来有三百挂零。害怕毛毛再拒绝,老人直接塞进了毛毛的口袋。毛毛这回倒是没再拒绝,瞟一眼,不轻不重嘟噜了一句:既然有钱为什么不换成整票啊?毛毛不知道,那是老人东家西家借的。他相信别人家有整票,但不愿意借。借点毛票,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扔个粑粑喂了野狗儿。endprint
毛毛上车那会儿,老人房门都没出。好在带毛毛出去的那位是邻里乡亲,而且听说在广州发了大财,这次回家就开着自己的小车。毛毛就是坐他的小车出门的。老人愣在房间里,隔墙听见带毛毛出门的那位问过:你爸不送送你?但老人没有听见任何回音,就像一片雪花落在水塘里。冷吗?大热天的,老人不愿意冷。或许,毛毛摇了下头;或许,毛毛悄悄流泪了?不管怎样,养了他十五年,是只猫儿狗儿都养熟了。老人躲在房子里,心里终究有些疼痛,但最多也就是滴了几滴冷泪。像那片雪花化出的水。
接下来,啪地一声,那是车门关上的动静。然后,屁屁屁。
“是你的别人抢不走,不是你的抢也抢不来。”老人果断抹掉了那把冷泪。
那只狗儿,这会儿倒是一步都没有离开老人。更没有像以往那样跟着毛毛赶脚。要么,是初中三年毛毛不住家,狗儿跟毛毛也生分了;要么,狗儿也老了,十五年的狗儿,听说相当于一百二十多岁的人,哪还有精力去管别人?
摸摸狗儿的脑袋,狗儿的哼哼唧唧都像老人叹气,老人心里舒坦多了。
老人把心思都放到狗儿身上。这狗日的,也许上辈子就是自己的孩子。好多次,老人想不明白了,遇上难处了,都是狗日在帮他。记得有一回,毛毛读初中那会儿,老人在家里发高烧,大天亮了还不开门。狗儿慌了,在门外爬爬打打,老人仍不想理睬。一会儿,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敲门的是对河的小老头。老人扶着墙壁打开门才发现,狗儿一身湿。一问才明白,是狗儿杀过门前的澧水河“咬”来了对河的小老头。澧水河平日里不深,乡亲们靠几个石墩来来去去,但过石墩要绕一段路,狗儿取了近道,就得淌浅浅的河水,溅了一身湿。
“妈的!这狗儿真成精了。我还以为是你让它跑过去的呢!”
“毛毛,我们……”想起小老头的那句感慨,老人不知此时的这声“毛毛”,究竟是在称呼谁。这多年了,狗儿逼着老人唤它“毛毛”,老人叫自己的毛毛也是“毛毛”,谁分得清呢?谁让狗儿和毛毛一块儿跑到他面前呢?
可是现在,那只叫“毛毛”的狗儿也不在了。
要怪,就怪皇天瞎了眼。
三
老人的房子,立在一座小岛上。虽然是山里,但悠悠澧水河,在老人生活的这里分了个叉,叉过老人居住的那个小岛后,又一咕噜合到了一起。因为这个小岛,这段河流就像一截永远疏通不了的猪大肠。过去,老人并不住在岛上。一般年景下,岛上是块宝地,有几十亩肥田肥地。不住岛上的人,也在岛上栽田种地。责任制那会儿,老人想到岛上耕作方便,就把家搬到了岛上。耕种季节,别人一担担猪粪牛粪压得牙齿像岩洞,老人这边没上肩那边早到了田里;收获季节,别人隔河渡水挑一担稻子回家,老人一丘田的稻子已经挑完。每到这样的季节,老人都让别人羡慕得想骂人。
这个夏天,连澧水河都想替对岸的那些家伙出口气。
那一声声怒吼,真就像河水在骂老人。我让你贪便宜啊!你贪!看我不整死你!
河水是在下半夜蜂拥而至的,没有任何征兆。不需要任何征兆。老天爷想找谁的麻烦,从来不通风报信。
年轻人被浪头推上河洲时,已经像一团浪渣。好在,他并没有和真正的浪渣一起被搁浅。拖着浑身泥水,喘着气,年轻人一边抬手清理满脸的渣草泥水,一边大踏步向老人的小屋跑过来。奔跑间,年轻人已经解开了捆在腰间的绳头,并吆喝对岸再松一松绳索。老人明白,年轻人是要找个牢靠的地方,把绳头捆稳。老人赶紧打亮了火机,照亮了小屋的门槛。
“快,老人家,把狗放下,我们马上过河!”年轻人在门槛上绕绳头时已经气喘吁吁,但语调比眼前呼啸而过的洪水还急。
“……”老人不知怎么办才好。
“老人家,您听见了吗?快把狗放下!我们马上过河!”年轻人的喊声类似于撕裂。
老人不适应那声撕裂。对年轻人心存感激是一回事,但老人抱着狗儿的双手,颤抖了一下,又一个颤抖,连同身子一起颤抖,狗儿被抱得更紧。就像有人要抢自己的孩子。
“老人家,我是来救你的啊!”年轻人或者把老人当成了傻子。
老人当然知道年轻人是来救自己的。平时,小孩们一口气可以游个来回的澧水河,年轻人刚才折腾了好几袋烟工夫才过来。蹲在家门口的老人,之所以一直用劲抽烟,就是想在黑天瞎地里,让忽闪忽闪的烟头,成为年轻人的航标。尽管对岸有手电光给年轻人指路,但漫天洪水里,年轻人动不动没了踪影。幸好,身影一次次逃离光柱之后,又一次次被光柱拽回来。其实,年轻人在水中每沉浮一次,老人的心也要跟着沉浮一次。好几次,老人只差开口让对岸的乡亲们把年轻人拉回岸。老人始终不敢开口的原因是,对岸的阵阵吼叫,比眼前的洪水更凶猛。
“老人!你快点!是不是不想活啦?不想活了你就别浪费了一河好水!”这会儿是村长,村长把手电光直接打在老人脸上,让吼声顺着光柱,蛇一样钻进老人心底。
要是平时,村长对他那么凶,一定有人会说句公道话。但这回,连村长身边的乡里乡亲,也一个劲给村长帮腔。
“老人你快点唦!真是急死人了。”
“命都快保不住了,还要狗儿干什么?”
“老人,你那么喜欢狗,能活着过河的话,老子再送你一窝!”连那个当初给他送狗儿的小老头,都丝毫不留情面。
“要我说,死了活该,刚才根本就不该让人家冒险过河去救他!”
……
老人始终没说一个字。老人在心里琢磨了一会儿,突然想笑。老人居然想笑。但老人的笑深深藏在心底。不是不敢笑出来,是老人不会绽放笑容。没办法像别人那样,让笑容大大方方跑到脸上。老人想笑时,只知道牙一呲,随后僵在那里,脸皮不抖一下,嘴角不拉一下,眼睛也不眯一下。谁会把这样的表情当笑容?最多以为他是要说话。也正因为天生就是这副表情,儿时的先生才问了句:你怎么一天到晚见不到个笑脸啊?简直就像个老人!“老人”,也便因此成名。一辈子,老人的笑,也便停留在别人说话与发笑之间。就像骑在门槛上睡觉的小孩,没人知道他醒来后会跨向门槛哪边。现在,老人就那样张着嘴,似笑非笑地望着年轻人忙活。转眼,年轻人已经将绳头捆在门槛上,一圈又一圈,然后整个人站上门槛,双手挽紧绳索,用整个身子的力量检验着拴绳的牢固程度。不用检验,肯定没问题。老人都坚信,绝对捆牢了。十万火急,年轻人又掏出另一根绳子,催促老人快把狗儿放下,并准备把自己和老人捆在一起。老人张了半天的嘴不再僵硬了。老人再次搂了搂怀里的狗,浑身抖个不停:“孩子,还是你先过河吧。我这儿不会淹的。我快活七十年了就没见淹过。”endprint
“您……老伯……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啊。那您,快快快,您把狗抱紧,抱紧,抱紧!”
年轻人和刚才一样果断。刚才果断,是让老人把狗儿扔掉,但现在,年轻人还一口一个“您”。老人差点没转过弯来,所有的心思,以及怀里的狗儿,一起凝固在黑夜的眼眶里。
“抓紧绳子啊,老伯,抓紧,抓紧。”
可是,抓得再紧也没用。
第一次失败,竟然是拴在门槛上的绳子开了个玩笑。不是绳头散了,是门槛从墙脚剥离出来。就像一根骨头,从煮熟的肉里拔了出来。
幸亏刚下水,幸亏年轻人劲头十足。不然,恐怕连人带狗一起跟着洪水冲进了某个漩涡。
又一阵手忙脚乱之后,绳子倒是听话了,年轻人很快找到了捆得更结实的地方。屋檐口的檩条上。但是,过河依然一次一次以失败告终。老人一入水,就像块石头。不是老人一点不会水,是老人抱着狗儿,腾不出手来和水纠缠。两个人,再加一只狗儿,就得靠年轻人一个人。等于身上捆着百多斤,与一头猛兽搏斗。
“汪汪汪!”那只一直和老人一起沉默着的狗儿,在洪水又一次冒过头顶,老人和年轻人一同呛了好几口水的时候,不再沉默了。狗儿突然挣脱老人的怀抱,一个腾身飞出去,飞回岸边,飞回了老人的小屋前。
老人要不是和年轻人捆在一起,肯定会立即跟着狗儿跳回去。
狗又是好一阵汪汪汪。
轮到年轻人浑身颤抖了。年轻人死死抱着老人,只差哭了:
“老伯,您您您看,狗狗狗自己都放弃了。我求您了。要不真的来不及了。”
远方,是老人从没听见过的某种闷响。声音并不大,但让人发麻。说远,不知在哪个天涯海角;说近,似乎就来在脑门边。像什么声音?老人后来一直想不明白,狗日的水怎么会折腾出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声音来?
“洪峰马上到了,老伯。”年轻人真的哭了,声音是带着血丝。
又一个浪头打来,狗哼了一阵嗷嗷嗷的小调,然后三声汪汪汪,一个纵身跳进了河里……
四
天亮了,老人才彻底承认,房子没了。狗也没了。什么也没有了。小岛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挣扎出来透口气。
老人蹲在河边,双眼死死地盯着河面,恨不得把眼前的一切盯成一场梦。
昨晚,老人之所以没能及时过河,就是因为被一个梦缠住,一时半会儿脱不了身。都说老来无梦。老人本来也好多年不做梦了,可偏偏昨晚做了梦。还想必因为梦成了稀奇物,好不容易遇上一个,物以稀为贵,老人才把梦当成真的一样。老人梦见了毛毛。毛毛一去三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个电话也没有,连个口信也没有,连个方向也没有。老人不是没打听过,问乡亲,问亲人,凡是在外打工的都问,但最终无异于一块石头扔进大海。这打听的人中间,自然包括那位带毛毛出门的发财人。可是人家摇摇头,一副有苦说不出的样子。最后,老人得到的消息是:毛毛小事做不来,大事做不了。在带他过去的发财人厂里干了不到半个月,就一声不响离开了。
老人在梦里,终于梦见了毛毛。梦见毛毛回家了。毛毛赚了好多钱,还带着儿媳妇,准备回家修房子。毛毛一见面就跪在老人面前赔不是,还拉着儿媳一起跪在老人面前,身边还带着孙子。孙子一声爷爷,叫得鹰子老哇落了一地。
醒来时才明白,落在身边的不是鹰子老哇,是狗儿的爬爬打打。
狗日一直睡在门外的狗窝里,怎么一下到了床前?拉了一下开关,电灯不亮了。摸出打火机啪嗒一声,才发现床头的土墙墙脚有个洞。他闪过强盗进门的念头,但转念否定了。偷他?等于瞎子点灯白费蜡。狗儿夹着尾巴嗷嗷嗷,那是从没有过的声调。老人明白了,彻底醒过来了,老人听见了对岸的吵闹声、呼喊声。
要说,落难的老人也不是没办法生存了。村长来了,乡长来了,请老人去敬老院住下来,那里有吃有喝有床,还有一群群无依无靠的老人可以吹牛扯谈。如今的政策好,老人每月有大几十元的养老金,愿意的话还可以学着和别人玩玩麻将跑符。村长乡长们还表示,如果老人愿意放弃收养的毛毛,还可以帮他申请五保。往后的日子就跟神仙没什么区别了。
面对那么多的好心好意,老人依然一言不发。依然呆在河边,望着一望无涯的澧水河发呆。一天没吃没喝,两天没吃没喝。人都饿小了一圈。第三天,当初送他狗儿的小老头,跟老人死磨硬缠,嘴皮都要磨破了。老人终于开口吃了。
但是,那顿看似吃得很顺当的饭菜,最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狂。老人被小老头带到家里,小老头的老婆炖了炉子。小老头爱喝酒,让老人陪他喝几杯,从不喝酒的老人还破例喝了一杯。小老头喝得脸像猴屁股的时候,开始安慰老人:
“我知道你舍不得狗儿。你放心,我家的母狗又要下儿了,过几天再送你一条。”
老人没应声,一边放下碗筷一边道谢:
“老哥老嫂子,感谢你们的大恩大德。可我只能下辈子还情了。”
一个活人想找死,除了阎王爷谁都无计可施。何况,老人并不是找死。老人是要去找狗儿。吃饱喝足了,他相信狗儿一定就在河边的某个地方。最糟糕的结局也想到过,但老人暗下决心:活要见狗死要见尸。见到之后怎么办,再说。但别人不这么看,又没钻进老人心里,谁知道老人怎么想?
人们所知道的,是第四天早上醒来,老人不见了。
一个活人不见了,而且是断定他寻了短见,总得想办法找找。找的方向都很明确。想起在小老头家吃饭喝酒时的那句话,大伙想到的就是奔腾汹涌的澧水河。村里派人顺河而下,开着划子一路瞎忙。不愿意忙也得忙。不说乡里村里的要求,就说祖先遗留下来的习俗,也得把死人打捞上来的,还不仅仅是入土为安之类的说法,关键是不打捞上来,说不定某个日子里,老人就会爬上岸来“找替身”。这样的教训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好在,找了两天之后,就在大伙即将泄气之时,老人被找到了。发现老人尸体的那一刻,谁也没想过悲伤。但最终,人人都忍不住心慌。因为老人身边有条狗儿,而且是狗儿把大伙引过去的。狗儿躺在河滩上,一阵阵嗷嗷嗷嗷,像儿哭老子。走进一看,狗儿还真是泪流满面。狗儿也只剩最后几丝气息了。大伙将老人的尸体搬上划子那会儿,狗儿用最后一口气又开始嗷嗷嗷,泪水流成了一抹河水。
“狗儿哭,难道还要死人啊。”有人想起流传千古的传说,心慌了。
“要不,我们把它带回去,和老人一起埋掉?!”
“这个主意好!”
一群喜鹊从天而降,唧唧喳喳。喜鹊是报喜的。大伙心里豁然开朗,有如眼前海一样的澧水河面。
(责任编辑/白凤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