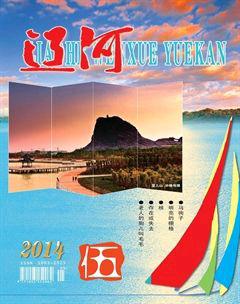春色二题
马永芳
地米菜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田边地头到处开着细碎的小白花,如点点繁星。那就是地米菜,一种极普通的野菜。它看上去似乎并不亮眼,也没有浓郁的芳香,却给人一种亲切而又自然的感觉。“地米菜”,长在地里,花小如米,又可食用,这名字真取得好。
“三月三,蛇出钻,地米菜,挂门栓”;“地米菜,蒸蒸菜,好吃婆娘拿碗来……”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学到的这几句启蒙诗,至今还流淌在我的心间。
故乡有个习俗,就是每到农历三月初三,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将鸡蛋和着地米菜煮了吃。小时候住在农村,母亲从田里扯来几把地米菜,洗净后放入锅中,放上适量水、少许盐,然后把鸡蛋放进去,把水烧得翻滚,然后熄火,稍凉,等蛋壳不太烫手了就可以剥着吃了——全家人都吃。锅里的汤泛着淡绿的颜色,透着一股泥土的清香。一边吃着鸡蛋,一边喝着地米菜汤,心里感到好惬意。母亲告诉我们:“吃了地米菜煮的鸡蛋,一年到头头不昏,不隔食,而且解热毒,眼睛亮。”后来我才知道这里面有些医学道理,但儿时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母亲的话是不会错的。
这个习俗我们家至今没有改变,我的小孙子不大喜欢地米菜的味道,我总是跟他说,这是你太祖母传下来的,你看爷爷不是很健康吗,那是与吃地米菜煮鸡蛋有关哩。不过现在有点不同了,小时候的地米菜是从田头扯来的,现在是到菜市场买来的。
地米菜的学名叫荠菜。宋代大诗人辛弃疾就写过一首咏赞荠菜的词《鹧鸪天·代人赋》,“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岗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好一派恬静、平和而又充满生机的村野景象,“柔桑”、“嫩芽”、“细草”、“寒林”,处处透出早春的气息。词的末二句把城中的桃李与郊野的荠菜同置于春寒料峭的环境中,两相对比,言春在村野而不在城中,颇具深意。
是的,岁月的风风雨雨,让人时时怀想那春在溪头的荠菜花。
油菜花
春风和暖,千里平畴,满望是金黄的菜花、葱绿的麦苗,正是黄与绿主宰着的世界。这是春的主旋律,是铺展在大地的两种生命的原色。大文豪苏东坡先生有这样两句诗,“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橙黄橘绿,秋色佳矣。不过眼前的春色却丝毫不逊那般秋色,因此这里不妨借而化之,一年好景君须记,菜花金黄麦绿时。
有一首老歌几十年来传唱不衰,一唱起它,我的胸中就升腾起一种质朴、亲切之情。“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麦苗儿青,菜花儿黄,多好的春色啊!我的耳边骤然又响起一首湖北民歌,“油菜花儿黄又黄呀喂,爹爹接我回娘家呀喂。只因社里忙跃进,我哪有闲功回娘家呀喂……”这首歌大约创作于1958年,那时正是火红的大跃进年代。且不论当时的时代背景如何,这首歌所独有的地方特色与欢快情调却是很打动人的。
谈到油菜花,又不能不说说我那小孙子了。小孙子上小学低年级时,每到早春季节,我总喜欢在双休日把他带到附近的农村去,让他多吮吸一些田野的新鲜空气,欣赏欣赏菜花金黄麦苗绿的美丽景色,当然,还有农家篱笆边那灼灼的桃花。记得有一次,我们爷孙俩正醉赏这美景时,小孙子忽然发现有一只黄色的小蝴蝶翩翩飞来,煞是有趣。他连忙张开小手去捧,没捧着,又追着去捧。追着追着,嗬,小蝴蝶一下子飞进了花丛中,再也找不着了。小孙子有些失望地对我说:“那只小蝴蝶怎么就不见了呢?”我一面宽慰他,一面顺口给他读了一首古诗,是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写的《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此诗正合眼前情景:菜花、蝴蝶都是黄色的,黄色的蝴蝶飞进了菜花地里,自然就难以发现了。小孙子似乎欣然领会,他灿烂地笑了,脸上花朵似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