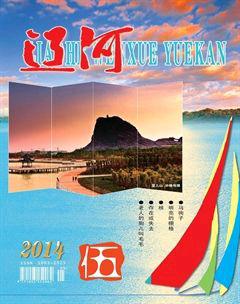马驹子
作者简介
白天光 男,当代作家。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发表小说八百多万字。近百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载。有二十多万字被译成英文、法文、日文、俄文介绍到国外。出版长篇小说《雌蝴蝶》等十一部。部分作品被改为影视。现为国家一级作家,兼某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歪梨屯儿总是寂静的,总是看不到热闹,狗的吠声显得很嘶哑,羊和牛也总是没有叫声,晨时公鸡也总是半醒着,打鸣的声音很短。歪梨屯儿的人们一年四季总是扎到地里,夏天铲地锄草,秋天收割,冬天就用驴车往地里送粪。歪梨屯儿的人们就这样活着,他们也愿意这样活着。
但屯子里也有不愿意这样活着的,不愿意过着这种寂寞生活的人,村西老马家在屯子里就与别人家不一样。主人叫马一琢,这不像一个庄稼人的名字。其实这马一琢还真不是庄稼人出身,屯子里的人大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而叫他马巡长。他十六岁就在江北的木香镇当巡警,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当巡长了。
马一琢也是大家族出身,父亲马辕曾做过巴彦县的县长。马辕有两个家,一个在木香镇。镇上有四、五个商铺,这些商铺都是大商铺,有药材商铺、洋货商铺(木香镇有许多俄国人,还有混血)、当铺、文房铺……马家在木香镇还有一个四合院儿,院儿里堆放的是木材,还有十几匹马。木香镇的大院儿没有长工,只有护院儿家丁,在这院儿里主事的是他的二姨太。在马家屯儿也有一个四合院儿,这个四合院儿比木香镇上的四合院儿大。马家的粮食、农具都在这里。四合院的围墙是红石岩砌的,有两丈高, 墙体很厚,四个墙角上面砌着炮台。马辕在马家屯儿有一百多垧地,家里有二十多个长工,一个厨娘,两个丫鬟,在这里主事的是大太太。马辕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江北的护国军里当团长,另一个儿子在省城省府街门做事。
马一琢是马辕的老儿子,是二姨太生的。二姨太叫黄彩莲,黄彩莲的父亲也是江北的大地主。马一琢从小娇生惯养,总是惹祸,马辕把他送到木香镇的巡警队,当时的队长是他的舅舅黄子善,是个武师。在舅舅手下做事,他就不再惹事生非了。后来他舅舅调到了别的县,做了警署的所长,马一琢就接替了他的职务做了队长。马一琢自从当了巡长以后,把这个弹丸之地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处理完公事就在父亲开的几个铺子里管事儿。
马一琢那时候有个外号,叫马大吃,他从来不吃青菜,猪肉、牛肉、羊肉、山上的狍子肉、狗肉、山狸的肉和狼肉都能下肚。但马一琢光吃不胖,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进青楼粘妓女。因为家里有钱,他每天都在想还有什么肉没吃到。那时候,山上的老虎也不少,打虎的人为的是卖虎皮和虎骨,对虎肉不在意,也没有人吃,因为虎肉有腥味儿。马一琢就派参铺的伙计到山上给他讨弄虎肉。他吃肉从来不让一般的大厨给做。木香镇有个御厨,当年在奉天城给张大帅主过厨,后来张大帅去了京城,这个御厨就到东北这个小镇开了饭庄。这个御厨和他同姓,也姓马,但不是近房。他叫什么名字,镇上的人都不知道,都叫他马大厨。马一琢吃马大厨做的肉,从来不欠钱,每次还要多赏给马大厨钱。那几年木香镇被日本人占了,马辕没有从县长的位置下来,做了伪满洲国的县长。马辕很精明,把他的铺子都卖了,一部分买了金条藏起来,一部分都买了地。马一琢也不再做巡警队队长了,因为县城成立了皇协军,巡警队不再自己说了算了,他就从县城回到了马家屯儿。
……
世道变得很快,十六年以后,东北解放了。马家在土改的时候被划成了地主成份,马一琢一下子就变成了受管制的地主。但马一琢回到马家屯儿以后,也没有受到冷落,屯子里的人也没有欺侮他,因为马家屯儿大多都是马家族人,按辈份马一琢算是家族中最年长的人之一。开始屯子被区政府管,区委主任也是马家人,也是马一琢的侄儿。后来,区委改叫人民公社了,公社的社长和党委书记是从别的公社调来的。马家人在公社也有一个副社长,还有一个民政助理。马家人虽然在公社也有些权力,但全公社的事还是由社长和党委书记说了算。党委书记叫陈志勇,才二十多岁,十八岁的时候去过朝鲜,当过志愿军。转业的时候就是连长,开始是在县政府,后来就调到三石桥公社。他对贫下中农很亲,而对地主富农却很冷漠。全公社的地主富农在生产队都被他安排了最受苦受罪的活儿,有的掏大粪、有的冬天打场、装车送公粮。每到过年的时候,屯子里要杀两口猪,还有过了十岁的马、驴,这些活儿都由地主富农去干。他们虽然杀猪、杀牲口,却分不到肉,这些地主富农能够分到的是马蹄子、马尾巴、猪肺子。马家屯儿的地主富农一到年根底下,日子就不好过,他们不愿意干这些活儿。但也有例外,马一琢愿意干。自从他被划成了地主以后,已经很少吃肉了,一年也吃不上一次肉,但杀猪、杀牛、杀马,他能把那些本来应该扔的牲口杂件儿,拿回家收拾干净,煮上一锅吃了。由于这种活儿不多,马一琢吃这些牲口杂件儿是不够的。某一天,生产队病死了两匹马,将这个马扔到了山上,想让狼把它们吃了。马一琢把这病马收拾收拾,挑马身上的整块儿的肉割下来,回去煮了一大锅吃了。也就是吃了病马的肉,马一琢就得病了,他得的是一种怪病,浑身起大包,整天流口水,半个身子也有点不好使了……
马家陷入了灾难。马家家族的人同情他,也可怜他,就想办法救他。村里有个土医生,叫马占富,能开些药方,但他最拿手的还是给病人指出一些民间的偏方,再有就是他能拔火罐子。马占富家的窗台上摆了一排火罐子。有的时候马占富的偏方还挺好使,拔火罐也能把体中的虚火和寒毒拔出来。马占富就开始给马一琢治病,先给他开了一副清火解毒的药,没见好使,不但病没治好,马一琢又得了新病,尿频。后来他明白,他用的药是寒药,寒气太盛,折了阳气。马占富又用了一个不轻易往出拿的偏方,叫两毒焙粉。就是在瓦片上,把蝎子和马蛇子焙成粉,和着童子尿分五次服下。这个偏方让马一琢天天恶心、呕吐,也不见好。最后一招儿就是用火罐拔毒。他在马一琢的身上燃了十二个火罐子, 马一琢身上被火燎了许多火泡,仍不见好。半年以后,不知是病情加重,还是马占富医治有误,一向头脑清醒的马一琢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傻子。
马一琢傻了。他的媳妇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吃过苦,她对马一琢不嫌弃,整天伺候他,怕他死了。如果他死了,他分得的六分自留地生产队就得没收。更让她揪心的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叫马占居,村里人也叫他马驹子。这孩子长得慢,四、五岁了还不会说话,十多岁的时候走路还不稳当。按说这会儿他已经十九岁了,应该帮助家里干点活儿了,可他干什么都干不好。到了夏天,他也像大人似的扛着锄头去锄草,但他草和苗儿分不清,他妈就说他傻,其实他一点儿也不傻。他也上过学,不过他上学上得晚,十岁才上一年级。他没有把小学念完,这很可惜,因为他在小学读了五年书,却已经识得了上千个字,字写得也好。只是他不愿意读课文,这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平时话语很吝,该说的话不说,该做的事情也做不好。可马驹子在村子里的人缘很好,虽然他农活儿做得不好,但眼中有事儿,看见谁家有忙不过来的活儿他就帮着干。他最愿意干的是帮助别人家劈柴禾、脱土坯。到农闲的时候,家家都要修炕,就是把上一年土炕上的旧坯换成新坯,为的是炕热。脱坯的活儿很累,尤其是和泥。和泥是黄粘土,把用铡刀铡碎的麦秸掺到里面。每见到这种活儿马驹子就去帮着和泥。冬天下雪的时候,他不光把自己家院子里的雪扫净,也把村路上的雪扫净,村里人就都夸他仁义。每当他娘骂他傻的时候,村人总是说,马驹子才不傻呢。马驹子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屯子里,他都不能干整装的活儿,可他也不懒。
马驹子还喜欢狗,村里的许多狗见到他都亲,见到他就往他身上扑,用舌头舔他。马驹子家里也有一条狗,长得很大,也很壮、很俊。这狗的两个上眼皮有两个黑点儿,马驹子就叫它四眼儿。四眼儿整天都离不开马驹子,马驹子到哪儿去,它都尾随着。冬天的时候,四眼儿就拉着狗爬犁,马驹子坐在爬犁上到山上捡柴禾。
马驹子秉承了他父亲的天性,他也喜欢吃肉。家里是没有肉给他吃的,但他也能想出吃肉的办法。到夏天的时候,村西有个江岔子,水很浅,江岔子里长满了蒲草,一些蛤蟆就藏在草根儿里。白天看不见它们,一到黑天以后,这些蛤蟆又从草根儿里蹦出来,对着岸边使劲唱,唱一宿也不觉得累。也就在这个时候,马驹子就去江岔子捉蛤蟆。他把蛤蟆用柳条儿穿起来,白天的时候,挂在院儿里的沙果树上晾晒。晒干的蛤蟆用油炸才好吃,但马家一瓶子油能吃多半年,娘是舍不得让他用油炸蛤蟆的。他就到山坡上去拾一些干柴,烧出炭来把这些晒干的蛤蟆烤熟了再吃,这也是马驹子夏天和秋天能过上的好日子。
在屯子人的眼里,马驹子是屯子里最乐呵的人,这也是真的。别看马驹子在读小学的时候不愿意读课文,但是在没人的地方,他能把过去学过的课文背下来,背的时候很愉快——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
这是马驹子最喜欢背诵的一段课文,其实就是毛主席语录。他还会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除了背诵课文,马驹子还能唱上一两段儿蹦蹦戏(二人转)。蹦蹦戏公社和大队是不让唱的,但屯子里的人都能唱上一两段儿,尤其在地里铲地的时候,累了人们就唱。马驹子会唱蹦蹦戏是偷听来的,他唱得最拿手的是一个小帽儿——
三伏天里雪打灯
大年三十月儿明
咱家公鸡下个蛋
龙王爷山上捉长虫(蛇)
……
马驹子和他爹不一样,爹傻了,庄稼地里干不了事儿,可他心里总想事儿。有的时候想好事儿,有的时候也想一些不好的事儿。那年冬天他就遇见了一件不好的事儿,这件事儿只要想起来,他心里就痛。那天,他在三泉山的山洼里,见一个狍子趴在雪地里。它腿上有伤,一条腿出血了,看样子它是走不动了。他就把这狍子抱起来,放在了一块岩石的后面。他又拔开雪,拔了许多干草,抖净了雪,垫在了狍子的身下。这狍子很可怜,是一个小狍子。他又用石头围起来,防止狼来吃它。他跑回家,找到了放在药笸箩里的马蹄包(马勃),然后又跑回山上,给狍子的伤口涂上马蹄包粉,又用布把它缠紧。他原本是想要把狍子抱回家的,可爹总想吃肉,如果把狍子抱回去,娘肯定要把狍子害了,给爹炖着吃。这狍子很听话,每天很老实地藏在石板的后面,为了防止狼来害它,马驹子用石头给它盖了一个石头屋子,四周砌得很紧,也砌得很高。石屋子的上面铺满了棘子树,狼是最怕棘子树的,树上的刺儿扎到狼的肉里就断,狼会疼得直打滚儿。
狍子也饿不着。他每天都从家里偷一葫芦瓢猪食,送到山上喂狍子。有时又把白菜帮子和萝卜送到山上去。渐渐地,狍子的伤好了,能站起来了。这时,他又感到为难了,这狍子总不能在石屋子里呆着,它是一个活物,说不定有一天它就会从这石头房子里走出去。如果它要走出去就危险了。因为山上有几只狼,狼头儿叫三爷,很恶。屯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叫三爷的狼。这狼很狡猾,领着只狼崽总是藏到别人不知道的地方,一到黑天的时候它就会下山祸害人。这狍子一旦要是出去,三爷是不会饶了它的。此时,他想到一个人,就是后屯儿也就是石磨屯儿,有个大好人,叫武正良。有一年,一个要饭的老汉到他家讨吃的,武正良就把这老汉留到了家里。原来这老汉没儿没女,有个侄儿也不理他。这件事儿前后屯的人都知道。马驹子到武正良家去过,是因为武正良家里有三个丫头,没有儿子,一到农闲扒炕的时候,就没有人帮他干活儿。马驹子到他家帮他家和泥,脱坯,干了好几天活儿。武正良还管他一顿饭,是白面馒头炖豆腐。这也是马驹子这年吃得最好的一顿饭。
马驹子为啥到武家干活儿?是因为武正良的二闺女武凤娟和他是小学同学。在学校的时候,武凤娟没有和马驹子说过话,就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碰到了,相互之间也没打过招呼。武凤娟在班里是班长,她很老实,但她学习不好。她能当上班长是因为她勤快,每天她总是比别的同学先到学校,然后打扫教室的卫生。她每堂课下课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专门擦黑板。班主任不太喜欢她,但校长喜欢她,因为校长和她家有亲戚。小学毕业五、六年了,有一回,在江岔子武凤娟正割蒲草。蒲草能缮房子,每年房盖儿换蒲草都是武凤娟到江岔子割蒲草。那天,马驹子在江岔子捉蛤蟆。白天抓蛤蟆需要人跳进江岔子里,在草根儿里摸。那天马驹子的手气不好,捉了一下午,才只捉到两只蛤蟆。武凤娟见到他,对他说,马占居,帮我割几捆蒲草。马驹子也没有说话,就接过武凤娟手里的镰刀,使劲割起草来。天傍黑的时候,马驹子已经割了十多捆草,这些蒲草已经够缮三间房的了。武凤娟很感动,就对他说,谢谢你了马占居。马驹子脸红着,低着头说,没啥。
那次武家脱坯,是武凤娟到山下去等马驹子。因为一到夏天的时候,他总是到山上去拾从树上落下的干枝子,武凤娟多次看见过他。那天,她还真把马驹子等到了,对他说,马占居,还得求你,我们家过几天扒炕,现在需要脱坯,如果你能抽出功夫,就到我们家帮我爹干两天。
这也是马驹子求之不得的事儿,他仍然低着头说,嗯哪。
马驹子到武家干活儿,什么事儿都不想。武正良并不认识马驹子,武凤娟向父亲介绍马驹子以后,武正良惊了,半天才说,我认识你爹,你爹马一琢在这一带应该是个大人物,要不是解放了,他也许都当上省城的警署署长了。武正良唠他爹的话题,也只能唠到这里,不能再继续唠下去了。南北二屯儿知道马一琢这个人,只知道他是吃了死马肉得了怪病瘫了,却很少人知道他过去曾经是巡长,武正良知道。马驹子干别的活干得很慢,但他脱起坯来很麻利,也不觉得累,好像浑身都有劲儿,这也许是马驹子和泥脱坯上了瘾。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见得什么都喜欢,也不见得什么福都愿意享,但马驹子在和泥脱坯的时候,就觉得幸福。马家屯儿几乎所有的人家他都去帮着脱过坯,他不图什么,有的时候帮助人家干活儿,人家招待他吃晌午饭他都不吃。
在武家足足干了两天活儿。武家三间房,却有四铺炕,除了厨房,其余的两间屋子里都是南北大炕,需要的坯多。要是武正良一个人脱坯,至少得干上半个月,就是请别人来帮忙,也得五、六天。马驹子在干活儿的时候,武凤娟只看了他一会儿,挑了几个他干活儿的毛病,马驹子也不生气,照样还是说一句话,嗯哪。武凤娟挑完被她发现的几个小毛病,然后就走了。她先是到后院儿喂猪,然后又去地里看她种的几垄蔬菜,好像已经记不得马驹子在她家帮助干活儿。马驹子帮着武家干了两天活儿,他不想让武家领他的情。他原本是要跟武凤娟说把那只狍子寄养在他们家,但他想了想还是没有勇气说。心想,还是别说了,因为这时候说也不是时候,武家还以为要他们人情呢,他觉得过一段儿再说更好。
吃晌午饭的时候,算是和武凤娟在一块儿的时间长的时候。这天在吃晌午饭的时候,他有了意外的发现,他发现武凤娟的手很好看,又白又嫩,手背上还有圆润的坑儿。其实,武凤娟长得并不好看,眼睛不大,脸却很大,尤其她的嘴里露出的几颗牙又宽又大,牙和牙之间的缝隙也露得大她还有点胖。武凤娟身上的这些物件儿,马驹子都没有看进眼,却觉得她的手太好看了。无形中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欲望,如果摸一摸武凤娟的手,那会幸福无比。马驹子这个发现也是他幸福的开始,这种幸福虽然是虚幻的,可想像着摸到她的手就足以让他从心里往外舒坦……
在屯子里马驹子永远让人看到的是寂寞,其实马驹子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别人谁也猜不出来,也没有人愿意猜。马驹子也不能天天都幸福,他也有不幸福的日子。这年天旱,旱得很厉害,将近半年也见不到一滴雨星儿。江岔子的水越来越瘦了,有的地方接近干涸,平时鲜活的那些蛤蟆,和他一样也感觉出了不幸,蛤蟆成片地死掉了。马驹子踏进江岔子感觉不出一点清凉,泥是热的,甚至有些烫脚。在夏天应该是蛤蟆最多的时节,马驹子每天也捉不到几只蛤蟆,后来,他竟然放弃了,不再到江岔子去捉蛤蟆了。
爹整年吃不到肉,但他不吃蛤蟆肉,他嫌蛤蟆肉太瘦,而马驹子在吃蛤蟆的时候,却觉得越吃越香。捉不到蛤蟆了,他的感觉就像他爹一样,每天有些烦燥不安。这天,他忽然想到山上还能捉到能吃的动物,可他却从来没有勇气去吃,因为山上能吃的东西都被人们捕获没了。也就在这一天,他发现了在树上跳来跳去的松鼠,他觉得如果能把松鼠捉到,这小活物也能吃。松鼠长得像耗子,他总认为它是树上的耗子。既然是耗子,将它们杀死是不作孽的。这天,他捉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松鼠,回去摆弄干净,就让他娘给煮。他娘不给他煮,也劝儿子别吃这东西,吃了恶心,就是在煮的时候,锅里冒出的汽都有腥味儿。因为前几年他爹想肉都想疯了,就让屯子里的一个能爬树的半大小伙子,捉到了一只松鼠,煮熟了以后爹闻到了这肉味儿,就开始恶心,到后来,爹还是一口没动。娘不给他煮松鼠肉,他觉得把这松鼠扔了怪可惜的,他就想办法要把这松鼠肉煮熟了。这时他就忽然想起后院儿还有一块锅碴子,这锅碴子虽然已经两半儿了,但还能装进去两葫芦瓢水,也足以能把松鼠肉煮熟了。他怕他娘知道,就趁他娘不注意,扛着锅碴子去了山上,在一块儿很隐蔽的山洼里,把锅碴子支起来。又从不远处的小溪里盛了两葫芦瓢水放进锅碴子里,下面放了干柴燃着了。水开了的时候,他将松鼠肉放进锅碴子里,也刚好水能浸过松鼠肉……马驹子此时显得异常精明,将火候把握得很准。煮了两袋烟功夫以后,又抓了一把盐放进去,然后就把松鼠肉捞了出来。等松鼠肉不烫嘴了,他就大口地吃起来,这松鼠肉虽然有些腥涩,但也能嚼出肉味儿来,细品也很上口……
马驹子半夜的时候开始发烧,后来又身子发抖,他娘说这孩子是打摆子了。就连夜敲开了马占富家的门,请他救救马驹子。
马占富从来是不拒绝别人求他的。他拎着一只木匣子,就来到了马家。他给马驹子切了脉,又翻开他眼皮看看,说道,这孩子是得了邪病,可能是吞服了秽物。我给他开一副催呕的偏方,服了药以后能把秽物吐出去,这病就能减轻。
马占富开的偏方,多少也算是起了点作用,马驹子服了药也果然呕吐了。马占富很喜悦,每当他给别人出了偏方,对方见好的时候,他的喜悦就掩饰不住,他从兜里掏出烟袋,拖着长音说,上烟!
抽完一袋烟,马占富又出了第二个方子。他第一个开的偏方是实方,第二个偏方是虚方,就给马驹子指出一条明路:这孩子吃的秽物是在什么地方吃的?要到那个地方叩三个头,然后再燃三柱香,这病就能好一半儿了。
马驹子还能站起来,但身子很虚弱,走路的时候需要拄一根棍子,走了几步就又摔倒了。马占富就背起马驹子,到了山上,亲自看着马驹子叩头,燃香。
马驹子的病又加重了,马占富这时开始担心,怕把马驹子的病给耽误了,就让他去医院看看。马驹子的娘显得很为难,说,现在家里也没有几个钱了,怕是到了医院也没钱治。马占富想了想说道,我家里还能拿出几个钱来,先让马驹子用,啥时候你们家有钱了再还我不迟。
这时候,马驹子娘再次看出了马占富是个大好人。上县医院路途远、路程长,马车也行不了这么长的道儿。马驹子娘就说,到县医院路途远,花费也大,还是到公社卫生院去看吧。
天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公社卫生院。这天,卫生院的西医没来,只有两个中医在坐诊。给马驹子看病的大夫二十多岁,一脸的稚气,他就给马驹子开了祛热药和消炎药,说,服了药看看,也许能退热,炎症也能消。
在回来的路上,马驹子娘说道,这大夫就给开了两包药,也没打针,能治好吗?
马占富说,我打眼一看,这个大夫也就二十一、二岁,光退热消炎这么简单,我怀疑他没有能力治这个病。不过,可以服他的药,服完以后看见不见效。
马驹子娘问道,占富,你说这孩子会不会有个三长两短。
马占富想了想说道,二婶儿,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话,这孩子从根儿上说,得的不是病,病是从五脏六腑中自然生出来的,而你家马驹子是中毒……用文一点儿的话说,叫生死未卜,谁也不能担保这中毒症就一定能好……
娘和马占富的对话,马驹子听得很清楚。他知道生死未卜的意思。马驹子虽然很痛苦,但他没有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在回来的路上,马驹子想了很多……
他最惦记那只走失的狍子。这也怪他,如果那天他跟武正良说让他帮助收养狍子的事儿,说不准还会同意。这也是一件遗憾的事儿。
还有一件事儿他觉得应该冒一次险,那就是他想向武凤娟提出一个非分的要求,他想摸一下武凤娟的手。狍子的事儿已经算是没指望了。三泉山深不可测,越往里走,林木越茂密,狍子的最后结果肯定是被狼吃了,它也不可能在山里碰不见三爷,任凭狍子怎么样在山上乱窜,或者隐藏在某个地方,也不会有好运等着它。马驹子还是觉得这件事儿也该死心了。武凤娟虽然没看好他,可也并不烦他,他现在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要是能够摸一下武凤娟的手,也算是这辈子没白活一场。
武凤娟知道了马驹子得了重病,她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她就到木香镇的一家商店,买了二斤槽子糕和一斤绵白糖,这两样东西在农村也算是最好的东西了。这天,武凤娟把她买的东西拎到了马驹子家,见马驹子病得确实很重,就把这两样值钱的东西放在了炕上,真诚地说道,你现在病得不轻,得好好补补身子,点心和糖就能补身子。这让马驹子很感动,他说不出感谢的话来,只说了一句,这东西太贵重了。就再也没有话了。他已经看出了武凤娟没有咯应(方言,嫌弃)他,现在他要是像武凤娟提出那个要求也许她不会拒绝,但他还是没有把握。武凤娟在马家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要走了。这会儿,马驹子的爹妈都没有在屋里,他们都出去干活去了。马驹子就费力地坐起来,武凤娟看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可怜,就问,马占居,看样子你还有话要说,有啥事儿求我你就只管说,我会尽力帮忙的。
马驹子的声音变得低了,又低下头,声音像蚊子那样细,说道,有点儿事儿,可我不敢说。
武凤娟说,说吧,啥为难的事儿我都能帮你。
马驹子说,这事儿太难了,我怕你……
武凤娟就训斥他,真不像个大老爷们,有啥话该说就说,要是不难我就办,太难了我办不到也告诉你一声。
马驹子头更低了,说,那我就说了。如果你办不到就不用说了,你可以扭头就走。
武凤娟说,这主意不错,说吧。
马驹子终于有了勇气,说,我想……我想摸摸你的手。
武凤娟想了想,说道,你咋有这个想法。
马驹子说,没啥想法,就是想摸。
武凤娟把手抻过去,摸吧,咋摸都行。
马驹子就摸了一下武凤娟的手,再也没有勇气把手伸过去了。摸完就说,武凤娟,我的愿望实现了,谢谢你,也对不起你。你……你走吧。
武凤娟笑了,笑出了声,然后就走了。
……
马驹子感到少有的轻松,他觉得这辈子也没有啥不满足的事情了,死了也值了。
晚上,驹子娘对他说,明天你还得上医院。马占富说得对,就是有一线希望,我也要给你治。咱们家虽然没有钱,我也想好了,过几天,把咱们家的房子卖了。生产队长家里有一间闲房子让咱们去住。咱们也不白住,秋天的时候给他一袋子谷子就行了。
马驹子说,娘,我不去医院了。就看命了,咱村里有人说过,该河里死,井里死不了。人的寿禄靠的是命大或者命小。
马驹子娘说,我知道你心里头有咱们这个家,舍不得花钱。钱是人挣的,将来你身子壮实了,再挣钱也不迟。
马驹子笑了,娘,我真的不去看了,我这辈子知足了。
马驹子娘一直在琢磨着儿子的话,他不知道儿子还没有成亲,怎么会知足,这孩子有的时候说出的话让人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