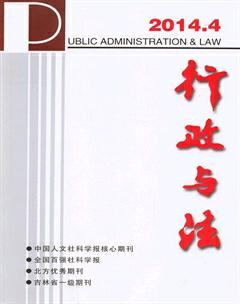非法采矿牵连环境犯罪研究
摘 要:非法采矿与侵害矿业环境是孪生关系,山体滑坡、地陷、毁林以及污染水源等损害价值特别巨大。但损害环境从未定罪而仅以非法采矿罪判刑,罪刑不相适应导致违法成本少于非法采矿的收益,催生非法采矿现象蔓延。因此,应认定非法采矿牵连系列矿业环境犯罪形态:毁坏财物罪、污染环境罪、滥伐林木罪以及非法占用耕地罪等。牵连犯罪广泛,不应有统一的处断原则,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牵连关系度松散的非法采矿牵连矿业环境犯罪,应适用数罪并罚原则;对恢复环境、消除危险、填平损失等,还应适用非刑罚措施。
关 键 词:矿业;非法采矿;牵连犯;环境犯罪
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4)04-0118-06
收稿日期:2013-11-28
作者简介:康纪田(1957—),男,湖南新化人,湖南娄底行政学院法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矿产资源法。
在现代刑法制度下本不应该继续存在的一种现象:明显构成犯罪并且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而在司法实践中从未定罪和处罚。如在非法采矿方面,即使导致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也从未予以定罪和处罚。因而,面对非法采矿蔓延趋势,只能停留在行政手段的严厉打击而难以利用刑事惩罚的震慑力。
一、非法采矿的犯罪成本低于收益
非法采矿,是指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而擅自进入矿业开发市场进行开发。非法采矿的社会危害性极大,不仅在于扰乱矿业市场秩序、致使国有矿产物权丢失,更在于损害矿业环境而影响区域内民众的基本生存权。非法采矿必然会损害矿业环境。非法采矿的“非法”就在于,有的逃避政府对环境和安全的管制,缺乏开发的地质信息资料,全无合理开发的计划,没有开采技术和开采设备,只能利用野蛮的开采方法开采;有的为了不让行政执法部门发现而秘密进行,或者在晚上、或者以游击战方式、或者利用合法形式掩护等方法开采;有的为了占有国有矿产物权,没有理由也不必要顾及社会相关联人的利益损害。这些非法行为的每一个方面都直接威胁生态环境,因为行为人所欲占有的矿产不是裸露在空阔地面上的动产,而是包裹在生态环境之中的“矿藏”。那么,只要是非法开采“矿藏”,就必然会破坏和污染环境。因此,保护矿业环境应是禁止非法采矿的主要目的之一。
我国自2002年整治矿业市场秩序以来,各级政府逐年加大打击非法采矿的力度,一些地方组织多个部门形成合力出重拳打击。但是,非法采矿现象越整治越严重。广东省新丰县的稀土品质很好,但盗采稀土矿则是公开的秘密。2012年8月,新丰县“开展了号称有史以来最大力度整治非法稀土矿的‘飓风行动,而恰恰就在这次行动中,新丰的稀土盗采也达到了空前猖獗的程度:仅在遥田、沙田两镇找到非法稀土矿点不下30个。……这些矿点树木多被砍尽,黄土杂陈,块块伤疤般裸露于新丰西部的大片葱绿山林之中;雨水冲刷,疮痍满目,大多已呈现出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景象。一位知情人士估计被毁林地应该不下5千亩。沙田镇天中村腊坑组、缠良村石桥组、下埔村陈洞组部分村民向记者叹苦:因为山体遭毁,水源遭毒,他们的村庄已不适宜居住,大家正考虑搬迁事宜。”[1]非法采矿空前猖獗,由此破坏和污染环境而迫使区域内民众搬迁,不只是广东新丰县,在全国也带有普遍性。
非法采矿蔓延的情势,关键在于法治手段不力,尤其是未能形成刑事震慑力,因此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福建省南靖县龙山镇涌口村沈某洪、沈某喜两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09年至2011年长期擅自开采国家保护性特定矿种稀土矿。经司法部门依法鉴定,沈某两人获得非法采矿的矿产品收入超过100万元;造成稀土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为117.45万元,破坏山上植被面积达9.3亩;矿区山体形成斜滑面而处于随时塌方的危险状态;同时,选矿遗留的注液孔导致地表水快速渗入地下而不断形成新的斜滑面。2012年9月,南靖县法院对被告人沈某洪、沈某喜共同非法采矿一案判决: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被告人沈某洪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5万元;判处被告人沈某喜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5万元;判决两被告填平因非法采矿遗留的注液孔和因沉淀矿产而建的12个沉淀池,消除山体滑坡的危险,恢复破坏的植被。[2]这是一个公益诉讼的案例,南靖县检察院以原告身份向南靖县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人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对公益诉讼作出了大胆的判决(南靖县的公益诉讼案,在于矿业环境责任承担和实现方式的创新,后文简称“南靖案”)。“南靖案”有创新,而除了创新以外的刑事处罚是很有代表性的:两被告均以非法采矿罪认定并判缓刑,均未承担其他刑事责任。
从“南靖案”可以看出,非法采矿犯罪仅就矿产物权所得这一方面来看就明显存在刑法惩治不到位的弊端。非法采矿的收益所得有上百万元的价值,而对主犯判处的徒刑只有3年,而且是缓期执行;对于破坏巨额矿产资源、破坏植被及其他方面等生态环境,既没定罪也无刑事处罚。然而,象征性惩治非法采矿罪的“南靖案”是一个判例,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采矿罪均倾向轻刑化和缓期化判处。非法采矿罪的犯罪目的和行为性质与盗窃罪相一致,但非法采矿罪的判处与盗窃罪的惩罚相比较,非法采矿罪量刑畸轻而显得罪与刑不相适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法采矿的犯罪从未计入环境刑事责任成本,可以说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非法采矿侵害环境权益应当以犯罪论处的刑法制度。对于非法采矿损害环境的行为,一般以承担民事责任为限,即使“南靖案”也只是停留在公益诉讼而已。这就等于从制度上放纵了矿业环境犯罪,而让非法采矿者逍遥法外。
非法采矿犯罪出于占有财物的经济动因驱使,这就要进行相关的经济分析。行为人遵守法律而保护环境,在于对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之间的衡量,如果违法成本小于违法收益,则有了选择违法的条件和动力。行为人经过犯罪成本的利弊衡量,如果犯罪更加值得,就会选择犯罪行为;如果认为犯盗窃罪的成本远高于非法采矿罪,就会改盗窃为非法采矿的犯罪行为。遏制非法采矿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环境,合理惩治矿业环境犯罪才能从违法成本方面预防非法采矿犯罪。
二、认定非法采矿牵连矿业环境犯罪
必须区别“非法采矿罪”与“非法采矿的犯罪”。非法采矿的犯罪比较复杂,几乎集罪数理论于一个产业领域,并且很有代表性。①一般来说,因非法开采而能导致多种犯罪形态,如牵连犯、想象竞合犯、共同犯数罪等;其中的非法采矿牵连犯可牵连盗窃罪、抢夺罪、环境犯罪等。[3]而且,这些数罪在非法采矿罪犯罪中同时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应分析和评价非法采矿罪与其相关犯罪的法理关系,以防止将非法采矿行为统统纳入非法采矿罪。在此,重点关注非法采矿罪与矿业环境犯罪的关系。
⒈非法采矿牵连犯罪的构成。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结果,不但将国有矿产物权据为己有,还侵害了生态环境。当侵犯物权和环境权可分别构成犯罪时,则两者之间具有比较典型的牵连犯特征而属于牵连犯罪。②在牵连犯中,侵害生态环境没有独立的目的而是服务于非法采矿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国有矿产物权。侵犯两个权利的目的是相同的,目的的同一性是牵连犯的基本特征。
构成牵连犯的前提条件是有两个以上的危害行为。行为人要实现非法采矿的目的,就必须至少实施两个行为。矿产物之所以称为矿藏,就在于“藏”于土地之中,要使矿藏转化为不“藏”的矿产品,必然影响环境。如果影响环境的方法不当或行为过度,则必然会损害环境。而且矿藏本身具有双重价值功能,即除了经济价值以外还具有生态价值。矿产生态价值的重要功能是支撑地面及其他生态的平衡。采矿者将经济价值占为己有时又撤走了相应的生态功能,如果不采取补偿措施,则导致地面及其他方面的失衡。然而,非法采矿者不可能采用反填、充实等补偿措施。这样,非法采矿者将“藏”矿的包裹体掀开及撤走生态功能的行为,与取走有经济价值的矿产品的行为,是分别独立存在的两个行为。两个分别独立的行为之间基于同一目的而存在牵连关系。也正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使我们忽视了两个行为的独立性,只看到占有矿产物权的一个行为。在两个牵连关系中,掀开地面、毁灭植被等行为是无法避免的必要手段行为,意味着必须有这个手段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因此,影响生态环境的手段行为与取走矿产经济价值的目的行为之间,两者互相依存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于牵连关系而形成整体性,其中侵害环境的手段行为是为取走矿产的目的行为服务的,是为实现主要目的创造条件的从行为;取走矿产据为己有的行为是实现最终目的的行为,属于主行为。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构成整体的牵连关系,跟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构成的牵连关系的“牵连度”不同。后者的牵连度紧密,往往是别无选择,前者的牵连度松散而有灵活性。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为实现目的可以有不同的手段或方法,但构成牵连犯罪时往往是行为人选择危害性最大的手段或方法。因此在牵连犯中,构成犯罪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牵连时的恶性更大。①
⒉非法采矿牵连犯的形态。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然触犯数个罪名,这是牵连犯的法律特征和标志。根据非法采矿牵连行为的不同方式,非法采矿牵连矿业环境犯罪可涉及多个罪名:破坏环境罪、污染环境罪、破坏性采矿罪、非法占用耕地罪以及滥伐林木罪等构成系列环境犯罪。[4]这些罪名有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案件,无论是否同时存在,都符合罪数的一般理论,并且具有典型性。
矿业环境是指开发矿产资源时所必须利用的相关生态资源要素,包括水、空气、森林和土地等。矿业开发所利用的这些环境资源,又是该区域内民众生存与生活所必须享用的对象。区域内民众有权享用洁净、安宁的环境,称为“公民环境权”。当非法开发时,这些生态要素都有可能受到非法行为的侵害而构成矿业环境的系列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环境权,对象是生态资源要素,主观方面属于明知故犯。非法采矿行为所侵犯的对象以及行为手段或方式不同,所触犯的罪名也有区别。前述两个案例中的行为人,使用隐蔽性极强的管道浸析法污染地下水而水源遭毒、毁林不下5千亩、破坏矿产资源价值117万元、占用大量耕地等行为,分别构成污染环境罪、滥伐林木罪、破坏性采矿罪与非法占用耕地罪。
在矿业环境犯罪中,“破坏环境”犯罪的后果最严重而且具有不可逆转性。如前述两个案例中,“南靖案”的非法采矿导致地表形成斜滑面、破坏植被9.3亩;另一案例的非法采矿导致沟壑纵横、山体遭毁、已不适宜居住而考虑搬迁,均符合矿业环境犯罪的构成。由于矿业环境犯罪是新型犯罪,而在现行《刑法》中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只能适用传统的“故意毁坏财物罪”。1996年修改的《矿产资源法》关于非法采矿罪的评价和处罚,明确规定适用刑法的“故意毁坏财物罪”,②这为破坏矿业环境犯罪的评价提供了支持。
破坏矿业环境适用“故意毁坏财物罪”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③一方面,生态环境要素资源属于“财物”范围。毁坏公私财物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核心是处分权,而对处分权的侵犯则是最严重的侵犯,这是侵犯财产罪的本质特征。但是,随着物权理论的发展,导致刑法关于“财产罪的保护法益不能仅仅局限于财物的所有权,还应包括所有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利,如他物权、债权、租赁权等”。[5]这说明,毁坏公私财物罪中的财物范围较广,包括各种公与私的动产和不动产,包括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等有体物。尤其是不动产财物,并没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只是表现为毁坏财物,不动产理所当然可以成为毁坏的对象。矿业环境诸要素均属于不动产物权,包括特定区域的水体和空气。对于民众及其经济组织的公民环境权而言,这些不动产物权属于他物权之列,而且《物权法》已将环境权保护列入相邻关系,认可公民环境权的物权性质。因此,矿业环境属于“财物”,有理由成为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侵犯对象。另一方面,非法开采时的破坏手段属于“毁坏”行为。非法采矿对环境的“破坏”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毁坏”属于一个方向。有学者总结认为,“毁坏财物行为应当揭示行为破坏性,只有破坏性的行为才能构成毁坏,那些不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则不能认定为毁坏。”[6]《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本罪中的毁坏,主要讨论关于对财物的毁损说、效用损害说这两种不同的刑法理论学说。毁损说认为,是指通过对物的全部或者部分进行物质性毁损、破坏,以致全部或者部分不能遵从财物的原来用法进行使用,即全部丧失经济价值或使用价值。效用损害说认为,是指通过对物的全部或者部分进行物质性破坏、毁损,导致全部或者部分不能按有体物的原来用法进行使用,从而损毁物的价值、效用。这两种学说没有根本区别,均认为不限于从物理上变更或者消灭财物的形体,只要有损于财物效用或使用价值的行为都是毁坏。破坏矿业环境的破坏,符合关于毁坏的效用说或毁损说。矿业环境资源全部丧失或部分丧失使用的价值,都是因为非法开采者对环境施加外在的作用力而导致环境的价值、效用减损。如果没有施加外力的事实,矿业环境既不得毁损也不得降低效用。毁坏矿业环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包括使用火力、爆炸物或其他危险手段损坏他人的公民环境权。
三、非法采矿牵连矿业环境犯罪的处断
关于牵连犯的处断原则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而理论上的争议较多。主要存在三种学说:一是从重罪处断说。牵连犯构成实质数罪,但与典型数罪相比,由于存在牵连关系而标明主观恶性及其社会危害程度与数罪有区别,认为应对牵连犯择数罪中的一重罪予以处罚,这也是理论界对牵连犯处断原则的通说;二是从重重处断说。对牵连犯罪,仅从重罪处罚却另一轻罪被无端放弃了,应从数个具有牵连关系的罪名中选择一重罪定罪并从重予以处罚,这也符合刑法的谦抑原则;三是数罪并罚说。牵连犯属于实质数罪,根据有罪必定、有罪必罚的原则,理应按触犯的所有罪名实行数罪并罚才能最终实现刑法的终极目的。“对于具有牵连关系的数行为,除法律有明文规定从一重处外,一般应予数罪并罚”。[7]这些处断原则,各自只宜适用牵连犯的某一类犯罪。而牵连犯涉及众多种类的罪名,面对广泛的牵连犯罪的处罚,很难用一个通说的处断原则。对于非法采矿牵连环境犯罪的处断,必须根据罪数类型的目的性、犯罪形态等贯彻全面评价原则。非法采矿行为牵连产生多个犯罪构成,既要在定罪上给予全面的评价,也应在刑罚上给予全面的评价。
对非法采矿牵连犯罪的全面评价,可从刑事制度的规范理论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入手。从刑事规范理论上来分析,应当按数罪处罚。非法采矿牵连犯罪属于两个违法行为并有两个独立的犯罪构成形态,与一般数罪并无差异;非法采矿行为人实施了多种犯罪,则侵犯了法律保护的多个不同的客体,因而构成多个不同性质的危害性。不同的罪质说明,非法采矿犯罪行为侵害法益的指向不同,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程度,进而决定刑事责任不同。至于其中存在非法采矿牵连关系,同样具有数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能成为减少犯数罪社会危害性的理由。既然牵连犯罪从理论上说是数罪,那么从处断理论上也应按一般的数罪予以处罚。从司法实践来看,也应当按数罪处罚。如果按照“从一重罪处断”原则,意味着非法采矿牵连犯数罪处断为一罪。那么,处断时要么选择非法采矿罪处罚,要么选择矿业环境犯罪处罚,这就相当于只犯了一罪而放纵了另一罪,等于认可放纵一罪的合法性。即使对非法采矿牵连犯罪依“一重重处”,仍显得处罚不到位。无论是非法采矿罪还是矿业环境犯罪,无论侵犯对象的价值以及情节达到何种程度,最高刑只能在7年以下。如“南靖案”中,认定破坏矿产资源价值为117.45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且牵连犯数罪,最高刑罚不能超过7年,这与其他犯罪的处断相比较,如此畸轻处罚却显得罪刑不相适应。畸轻的处罚,则很难从犯罪执行成本上遏制非法采矿现象。刑罚的功能和目的是通过惩罚和教育实现预防犯罪,为此必须做到罚当其罪。因此,按照全面评价和处断原则,非法采矿牵连环境犯罪至少应适用“数罪并罚”。数罪就是数罪,处罚就按数罪量刑,这样才能实现罪与刑相适应。
笔者认为,对非法采矿牵连环境犯罪适用数罪并罚,是由非法采矿牵连环境犯罪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牵连犯适用数罪并罚说必须限制在一定条件下,否则就混淆了牵连犯与数罪的本质区别。对二者不加区分而一概施行数罪并罚,抹煞了牵连犯这一客观性。牵连犯是由目的的同一性、数个行为的牵连性等基本特征决定的,因而对各行为分别评价后的处断要受到基本特征的制约。但是,目的单一性特征不能区分社会危害性完全不同的牵连犯,无法对危害程度不同的牵连犯进行区别化的处罚。因为有些牵连犯从一重罪重处显得处罚过重,而另一些牵连犯则显得畸轻。“而数个犯罪行为之间的不同关系无疑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尽管这种关系统称为牵连关系,但各种行为之间的牵连度并不是等量齐观的”。[8]牵连犯的基本特征是,为了最终的一个目的而有数个犯罪行为。“也就是说,数个犯罪行为表现为目的行为、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以目的行为为轴心,方法行为是为实现目的行为服务的,结果行为是由目的行为派生引起的。”[9]为实现目的服务的牵连行为与为实现目的派生的牵连行为之间,两者的牵连程度完全不同。方法行为或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度并不紧密,为实现同一目的,行为者有诸多方法或手段选择。可选择恶性最大的方法也可选择没有恶性的方法,只是当选择没有恶性或恶性较小的方法时要增加实现该目的的成本而已,非法采矿时若要选择保护环境的方法则要增加更多成本投入,甚至无法达到目的;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度显得紧密,是一种内在的原因与结果关系,为了实现其目的,多数情况下没有选择其他行为方式的余地,因为其结果行为的必要性而促使行为人不得已而为之,比如盗窃枪支而收藏起来就是这样。这从刑法理论上来说,别无选择的结果性行为是在本罪行为之后实施的,为了目的的完整实现而体现行为的依附性,这种事后的依附性基本丧失了量刑的刑法意义。因而,事后不可罚行为与事前的手段行为,在处罚方面应当区分两者的恶性。而对于事前故意选择实施恶性较大的行为者,理应承担较重的刑事处罚,否则将成为放纵甚至鼓励犯罪的原因。
刑罚要与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的罚与罪质相适应,对于手段性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事实也是如此,如果对非法采矿牵连环境犯罪也“从一重处断”或者“从一重罪从重处断”,必然会放纵犯罪,相当于支持犯罪行为人选择恶性方法实现其犯罪目的。这有悖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最终无法遏制非法采矿牵连环境犯罪的现象。因此,牵连犯的处断没有通说,从一重罪处断说不适宜非法采矿牵连环境犯罪,而数罪并罚也不适应整个牵连犯。
四、非法采矿牵连矿业环境犯罪适用非刑罚措施
在“南靖案”中,法院支持了公诉机关的公益诉讼,判决两被告承担相应责任。这是在矿业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使环境的公众利益不继续受损害,以公益诉讼的方式针对民事主体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这项制度对于保护公共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已经提起的刑事诉讼来说,应将公益诉讼合并于刑事诉讼,由法院在判处被告刑罚的同时判处被告承担非刑罚的法律责任。这样,不但可以节约诉讼成本,还有利于现代刑法制度的完善。
环境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又称为环境刑事措施。根据环境刑事责任的特点,可将环境刑事责任措施分为两类: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刑罚措施包括自由刑和罚金刑,是判处非刑法措施的前提;非刑罚措施是矿业环境犯罪的补充性处罚方法,是指在刑罚之外对矿业环境犯罪人旨在恢复或救济被犯罪行为损害环境的处置措施,包括教育性处罚、民事性处罚和行政性处罚等。惩治非法采矿牵连环境犯罪只是手段,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应当是对矿业环境的补偿与恢复。利用刑事责任的非刑罚方式,能够有效地发挥消除环境犯罪后果的持续危害和恢复环境权益的作用。
矿业环境犯罪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犯罪,危害环境的犯罪人往往是因经济利益的驱动而无视损害生态环境的后果。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侵害后果的不可逆转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特点, 导致矿业环境犯罪与普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一样,其刑事责任实现方式有必要实行多元化。对于非法采矿牵连矿业环境犯罪,需要采取更为严厉和更为广泛的制裁手段,才能实现保护矿业环境的目的。因此,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方式,理应采取有别于其他犯罪的传统刑罚措施。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惩治环境犯罪,是现代刑法的要求,也是世界刑法发展的方向。但是,我国在惩治环境犯罪方面还是传统的刑罚手段,缺乏与刑罚相匹配的“非刑罚处罚措施”来保障矿业环境的恢复与补偿。因此,“在适用刑法已经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之外,应当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在判决中对被告人宣告适用义务性命令,例如责令补救、恢复原状、限期治理等等”。[10]
我国《刑法》已规定了多元化的刑事责任方式。除了规定主刑和附加刑以外,还规定了判处非刑罚的刑事责任实现方式,如《刑法》第37条。但《刑法》还应进一步规定:对于系列环境犯罪,除了判处刑罚以外还可以判处承担非刑罚责任,可责令犯罪行为人在规定期限内治理好已被损害的环境,包括责令补救环境或恢复环境,消除危险状态,责令赔偿损失等。当然,为避免评判的随意性而需要明确相关原则:非刑罚措施,只能作为刑罚措施的补充措施而不能代替刑罚措施。有了相关原则以后可以认识到,非法采矿牵连环境犯罪而判处非刑罚措施时,不需要顾及罪数的评价和处断,可独立考虑非刑罚措施的适用与否。
以严厉的刑法惩治环境犯罪可以遏制非法采矿,以适度的刑法惩治非法采矿罪则能保护环境,两者是相互促进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升值,无论是非法采矿还是合法采矿都有可能构成环境犯罪。环境犯罪是一类新型的犯罪,可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责任推定原则和非刑罚措施等。为此,《刑法》应增设“破坏矿业环境罪”、“破坏植被罪”,以适应现代刑法打击犯罪的要求。
【参考文献】
[1]亚立广.新丰非法采矿触目惊心[J].源流,2012,(05):13.
[2]吴铎思,刘荫花.非法采矿者既要赔矿又要“赔生态”[N].中国矿业报,2012-10-23(5).
[3]康纪田.论非法采矿罪的归位与拓展[J].时代法学,2012,(05):81-90.
[4]冯春萍,张红昌.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探究[J].法学杂志,2012,(12):45-49.
[5]康纪田.增设破坏矿业环境罪的路径分析[J].行政与法,2013,(09):115-121.
[6]陈兴良.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之定性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01):97-108.
[7]沈言.牵连犯的成立要件及其处断[J].人民司法,2009,(18):62-65.
[8]汪雷.论牵连犯的处罚原则[J].人民司法,2011,(17):91-94.
[9]冯野光,闫莉.论牵连犯的内涵、特征及处罚原则[J].法学杂志,2012,(03):19-24.
[10]赵秉志,陈璐.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J].现代法学,2011,(06):90-98.
(责任编辑:王秀艳)
Abstract:Illegal mining and destroy mining environment works the same.The damage of landslides,subsidence,deforesta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is great.However,th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has never been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in the crime of illegal mining only.Cost of illegal less than the profit of illegal mining makes illegal mining spreads.It should be recognized illegal mining implicated series mining environmental crime,such as he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crimes,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deforestation and illegally occupation of arable land.Widely implicated by this crime,there should be no unified principle.Graft principles should be applied for those harmful,widely implicated crimes.To reinstatement of the environment,and eliminate the hazard;non-punitive measures shall also be applied.
Key words:mining;illegal mining;implicated;environmental cr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