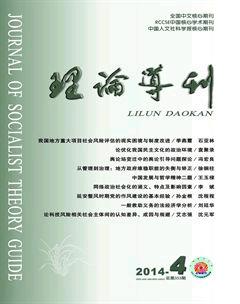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视阈下的公共利益问题析论
朱 雯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超时代性、前瞻性的文化哲学思潮,自其产生之日,就以一股势不可挡的思想涌流和观念力量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蔓延、渗透和扩张,公共行政领域自然也成为后现代主义批判、解构现代主义的重要阵地。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逻辑起点、价值核心与元叙事的公共性及公共利益同样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攻讦。
那么,作为整体主义价值和宏大叙事的公共利益在多元化、差异性的后现代社会是否存在?后现代视阈下的公共利益以何种形式存在,又以何种方式实现聚合?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论述,进而把握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
一、后现代公共性的存在释疑
后现代性孕育于现代性并以批判和解构现代性为其内在价值。作为现代性外在表征的公共利益,无疑会遭受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抨击,正如马歇尔和乔杜里所说,“在公共行政领域,后现代主义指出这样的疑问:在一个进步、理性与意义受到了严重挑战的时代,还能够存在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集体性表达吗?”[1]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作为公共利益本质属性的公共性是否存在于后现代社会。
1.后现代性阐述问题的立场和取向。现代性发源于启蒙运动中对理性主义的高度宣扬,其合法性建立在科学和技术能够解放人类的神圣地位上,主张主体中心化和元叙事,追求同一化和理性化、系统化。同时,现代性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冲动——控制,直至导向总体性的一致。依托于现代性建构起来的现代公共行政是现代主义不断自我确证的表征:注重主体、一元、权威;崇尚科学和理性;对核心加以模式化,忽视边缘的现象、理论;社会逐步走向专业分化;权力和统治成为主宰,人丧失了其作为人的主动性和价值理性而沦为机器的附庸;以效率和效益为导向的庞大科层制官僚机构机械地管理整个社会。
此时的现代性已不再作为解放人类、象征自由的力量存在,而是异化为禁锢、奴役人类的枷锁和工具。人类试图反抗这种奴役,权威性、主导性的宏大叙事逐渐无法压制微观话语、边缘群体的发声,多元化、差异化、碎片化、彼此平等而独立的话语开始勃兴。这种零星话语、微观叙事和差异文本逐渐扩散、汇聚,终于形成一股思想涌流——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主义中具有整体主义取向的公共性。在这种反叛和解构下,公共性作为公共行政领域主体间相互对话、政治行动的基础,是否会被解构甚至走向虚无?毕竟碎片化、无中心、反权威、凸显多元和差异性的后现代主义在将我们带入一个扁平化世界的同时,也可能将我们推入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深渊。公共性的存在与否,不论是对公共行政的学科建设还是对政府行政实践来说,都至关重要。
2.后现代公共性的阐释:“差异中的统一性”。“在既承认又抛弃现代性的基础构成的意义上说,解构乃是在对后现代情境的确认中对文本阅读和重读。”[2]251就公共行政领域来看,后现代主义从价值和事实的两个层面对公共性进行解构:一方面,否定现代公共性的叙事“符号”。在现代公共行政中,公共性所指涉的是一种先验性的、普适性的、与公众和共同体相关的整体主义价值概念,强调主体中心化、理性化取向,而后现代主义批判这种一元论的价值取向,关注边缘话语和微观叙事,主张开放性、多元性、破碎性、差异化;另一方面,是对现代公共行政事实指涉的否定。认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往往是政府为维护自身统治和合法性所标榜的借口和工具,弱势群体、少数公民的诉求被以整体、多数的名义压制,现代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主义、僵硬死板的官僚机构和丧失活力的公共行政人员,已经不再是积极的力量,反而成为压抑、奴役公民的根源,基于此,后现代主义否定正典、消解权威、批判官僚制、主张超越工具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批判和解构的对象是公共性的现代主义解释,而并非对公共性本身的否定。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一直尝试赋予现代性以后现代视阈的解释,试图唤回在现代公共行政中一度失落的公共性。后现代主义对公共性的重构首先体现在对主体“公”的重塑,后现代关注微观、多元,认为从根本上说社会的主体不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而是作为构成社会的无数个“原子化个人”;其次,是对价值“共”的重构,即共识、共同、公意,是所有相关者彼此同意的共同意志,而非主导意志。
后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在解构现代性基础上获得自身解释的后现代公共性,是一种与现代公共性截然不同的客观事实,是在差异、多元、破碎中的统一性(unities-in-difference)。“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并非一种虚无的事实……它包含于碎片、差异、多元之间。”[3]这种后现代公共性是在尊重每个个体自主意愿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真正且真实的公共性。
二、后现代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形式
与现代公共行政公共性在后现代社会的境遇一致,作为公共性外在表征的公共利益宏大叙事也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反叛和解构,并为后现代主义独特的言说方式和话语建构所重塑。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层面,一方面,公共利益被视作整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元叙事而存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占据了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制高点,个人利益事实上被奉行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公共利益被视作主张国家主义、全能主义的代名词,与效率至上的现代公共行政理念格格不入而陷入尴尬。而在现代公共行政实践中,信息垄断的黑箱政治、层级严密的政府机构及其命令—执行运行的僵化模式、官僚们“独白式”的专制话语又使得公共利益成为统治阶层获取选票、利益集团攫取利益的空头支票和挡箭牌。
后现代主义解构和否定现代公共利益,在理论上抨击现代主义的公共利益取代个人利益、无视弱势群体利益的整体主义取向宏大叙事;在实践上揭露现代公共行政以实现公共利益之名攫取特殊利益之实的伪善面孔,否定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所建构的民主代表负责制的环式民主模式及官僚制。
后现代主义否定公共利益的现代主义“解释”,并赋予公共利益符合后现代情境要求的新意义。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马歇尔和乔杜里就宣称,后现代公共利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合成式的公共利益观念”。这种后现代公共利益更加“强调包容而不是整合(后者是传统主义者的追求),强调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区别(后者是现代主义者的价值)”。[1]后现代“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远离我们的抽象的普适性叙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的诉求。因而,以公共利益为旨归,就要求公共行政既不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同化异质性利益诉求,也不出于竞争性管理的需要而区分近似的利益诉求,而是要鼓励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相互包容,使它们在这种包容中都能使其利益诉求归并到公共利益之中”。[4]简而言之,后现代公共利益是一种包容于无数利益碎片之中的包容性公共利益。
后现代社会包容性公共利益的存在形式,不仅关注价值上的“公”,也强调事实上的“共”,这使得公共利益与个人主义真正达成和解,彼此共融。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公共利益是一种共同善的公共,融于差异中统一性的公共,真正具有共享性和非排他性,是一种具有浓厚价值意涵的“common good”,而非“public interest”;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公共利益并不是单个利益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成员相互对话、沟通、协商所得出的具有共识性的、包容性的公共利益。这就意味着,包容性的公共利益既不排斥任何公民个体利益的表达,也不会强制形成关于公共利益的总体一致。因此,公共利益不再成为一种元叙事而存在,从而规避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
三、后现代公共利益的行动主体及发生场域
后现代主义碎片化、反权威、多元化的取向意味着新的行动主体即原子化个人的崛起,而包容性的公共利益正是通过无数原子化个人的一系列切合公共利益的意向性活动聚合而成的。在后现代社会,行动主体要表达切合公共利益的意向性,必然会形成公共能量场,即后现代公共利益的发生场域。
1.后现代社会的行动主体:原子化的个人。现代社会的公共利益主体,意指的是一个抽象化、具有普适意义的公民整体,弱势群体、边缘公民则往往被忽视。在高度碎片化、扁平化的后现代社会,主体权威被消解,主流叙事被解构,民主代表制也被批判和否定,微观话语逐渐凸显,总体性的概念不能胜任对后现代社会行动主体的指涉,因此,后现代公共利益的主体指向构成社会的每个公民个体,即原子化的个人,其基本特征是:享有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具有意识、反省、积淀的习惯行为以及所有感官和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身体本身”,并能够借助意向性的知觉使“身体—主体的积淀经验面对着新的情境”,[5]79“是一种体现、汇聚和谋划各样历史沉积性,可以进行自主选择”。[5]84
2.后现代社会利益聚合场域:网络结构的公共能量场。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建构了“公共能量场”这一概念,用以涵盖公共组织和公民群体所从事的具有公共意义的行动和重复性实践的聚合场域。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福克斯和米勒详细阐释了这一话语凝聚的场域,指出公共能量场是由“人在不断变化的当下谋划时的意图、情感、目的和动机构成的”,[5]包含着情境、语境及历史性三个要素。首先,公共能量场是一个公开的场域。任何公民进入和参与公共能量场都是免费的;话题、议题的提出、信息的交流都是公开透明的;最终共识的达成必须接受其他公民的检验。其次,公共能量场是一个网络结构的场域。“只要社会治理在结构上分为主次,即作为一种中心——边缘性的线性结构而存在,在民主的问题上,就会‘导致一种伪政治’。”[6]因此,公共能量场中,不存在绝对的权威,公民作为原子化的个人彼此平等。第三,公共能量场是一个真实的场域。参与者可以就某一特定事件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诉求,且这种观点诉求能够引起他人的关注并进而形成讨论,交流协商后所达成的共识也必然包含了这一参与者的意见。因此,这是一种“因他者的存在而获得自我在场的真实体验”。[3]
在公共能量场中,呈现出一个源头多元化而线性结构的氛围,参与者的观念、思想、谋划的目标可以在一个特定的与他人互动的模式下流传。某一情境或特定事件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表达意向,形成“零星对话”。每个具有意向性的观念、思想及谋划的目标都“犹如一个太阳黑子,它可以从任何的和所有的点上燃烧起来,燃烧产生的能量以波的形式向外传导,进而作为一个整体影响到整个领域,也影响到其他潜在的火焰点”。[5]98零星对话产生能量波,形成聚集动力的矢量,通过在人类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相互交流,形成彼此交流协商的共同语境,影响人们建构理解过程的社会互动,并对他们的重复性实践和情境不断提出问题,进而不断对其修正使之产生历史性的改变。这种网络结构的公共能量场,为公民提供了自由发声、协商交流的场域,成为后现代社会公民表达自身需求并达成公共利益诉求的平台。作为一个充满公共意义同时是政治与行政的中介的理想共同体的公共能量场,具备民主协商的理想环境,也是后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话语场所。
第一阶段为自然本能阶段,企业尚未形成安全规范制度及纪律约束,安全多源于人的自律与本能,安全管理更多的是安全管理人员的职责。
四、后现代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形式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语言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是我们在世界上充分行动的先决条件。“语言不只是思维、认知和思想交流的工具。它也是构成我们世界观、方法、直觉、假设和欲望的制造厂:语言构建了我们。”[2]1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叙述,它根植于语言并以不同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的方式出现,因此要“将科学还原为话语”。[7]我们必须借助语言才能认识世界的历史积淀,表达意向。在后现代公共行政领域,话语是个人利益意向性的表现形式,“一种内在的民主的意愿形成结构”。公共能量场中,参与者彼此交流、沟通、说服、面对面的交锋,作为一种建构的现实为基础的重复性实践,实际上是话语性的。
公共能量场的话语准入是自由且免费的,公民协商的过程也尊重每个公民个体自我的利益取向、话语需求,并不排斥公共利益的非理性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话语都是正当有效的。诡辩、谎话可能会使对话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官僚制民主模式的独白性言说而无法凝聚真正的利益诉求。为此,后现代主义学者引入尤根·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建构后现代话语理论以对话语的正当性进行严格的规约。
哈贝马斯主张实现一个真实交往的理想,他认为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相关性是真实交谈所应必备的条件。但这种“异口同声的和谐”和无争议的、非主导的普遍同意并非后现代所认同的话语形式。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只有话语形式具备真实性,使用合理的语言并造成某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才能更好地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8]因此,后现代主义引入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对抗是一种公共竞争,在其中存在着无法简约的他性、对立或紧张关系,但这种对立不是碎片化的,离心的反对被对普通参与的向心承诺抑制着。后现代主义学者进一步指出,对抗性意味着观点、话语的多元化,即话语参与者之间既是平等的,又是对抗的,在既定的规则下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关系,在辩论中决定“下一步做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会在能量场的空间发生,并伴有类似电流的不同电压水平,而且被多样的对抗性观点间的紧张关系所控制。”[5]117
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福克斯和米勒在以上两种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公共能量场中保持话语的正当性所须遵循的根据——话语正当性标准并不是为了把话语的实施禁锢于最纯粹的形式中,而是为了阐明一种使对话能带来丰硕成果的理想,以实现话语作为一种民主过程的真正价值,它包括以下的内容:①真诚。真实的对话要求参与者间的彼此信任,言说者的话语是真诚、热情、诚实和真实的,否则,就会导向话语的恶化,无法保证共识的真实有效。因此,没有一个真诚的公共话语,就不要指望满足公众利益且为此付诸行动。②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这一规定保证了话语是针对特定事件、特定语境下以实现某种共识为目的的行为。符合此要求的参与者会考虑问题的语境、受影响的人群及公众利益,也有责任表述他们关于社会目的的思想,并要说明这种目的应该怎样去实现。通过阐明公共目的,可以使关于公共利益的思想具有一致性。③自主参与。自主参与的谈话者会以一种积极、热情、主动的精神状态使人们关注那些影响特定政策讨论的事件,同时,会在尊重他人合理观点的基础上,自愿去倾听并参与言说,并且不排斥参与者话语的非理性表达。④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话语正当性要求话语具有实质意义,对话参与者可以提供一个独特的观点、普遍的知识或者相关的生活经历,可以表达其所代表的公民团体或阶级的兴趣,也可以为一个新的参与者概括至今的争论发展进程、勾勒下一步新的发展,这些都是在推进对话的深入,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贡献。
五、后现代公共利益的聚合方式
在后现代社会,话语是表达公民个人利益的载体,则公共利益凝聚的实质就是话语凝聚。公民在网络结构的公共能量场中平等地表达意见、自由言说自身需求,当然,这里的话语并不是无数语言碎片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话语,彼此交流、沟通、说服所形成的包容性对话。为实现话语凝聚,将碎片化的话语诉求聚合成公共利益表达,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建构了“部分人的对话”,即“具有不同意向性并符合正当性的话语在某一重复性的实践的语境中为获取意义而相互交流、论争的过程”。[9]
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否定和批判了少数人的对话——精英支配的少数人独白式的单向度话语体系,以及多数人的对话——无政府主义混乱无序的对话形式,认为只有“部分人的对话”的公共话语模式才有可能实现民主话语。这种对话形式凭借其公民参与的广泛性、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利益表达的自由性、话语的正当性及沟通的动态有效性,成为一种最接近公民真实话语和需求的公共利益聚合方式。
当然,“部分人的对话”也有其不足,福克斯和米勒认为“一些人的对话……的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但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5]143因此,“部分人的对话”是后现代包容性公共利益聚合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结语
后现代公共利益能否实现高效、有序的聚合,不仅依赖于公民是否有高超的话语技巧、自由协商的公共场域,更有赖于公民是否具有公共精神和公共知识,是否受到过公民教育。罗伯特·D·帕特南认为:“公共精神是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设,以营造适宜人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治理念、伦理追求和人生哲学。”[10]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公共的观念“必须建立在乐善好施与爱心”的基础上,“乐善好施所要体现的是一种服务的意识”。[11]42这种公共精神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它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取向的追求,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
一方面,具备公民意识和公共关怀的公民,能够主动关注公共事务,并自主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对话和交流中,真诚地运用公共理性和公共知识进行准确言说、理性协商、说服他人或妥协,最终形成公意、达成共识,这种共识才能最大限度体现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后现代社会的政府机构和公共行政人员,需要完成从利益聚合的主导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换。政府在后现代社会中,并不直接参与公共利益聚合的话语游戏,而是处于服务的地位来保障这种话语游戏的顺利进行。这不仅需要政府公职人员的高超行政技能,更需要深植于公职人员心中的公共精神。因为“技术上的专业也许能为公共话语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但这首先要以针对某一情境的公共对话为基础。……最终的问题是关于责任、意愿、价值与说服能力的问题”。[11]42公共精神是“一种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承担责任和义务并为此而献身于公共行政专业领域的信念”,[5]151会促使人们超越个人利益而寻求公共利益的实现。在公共能量场中,拥有公共精神的公共行政人员会积极地致力于搭建舞台,建立行之有效的公众交流机制,促进公众进行平等、真诚、自由的对话,确保公共利益本身及其产生过程符合公平、正义和公正的民主规范,并最终确保公共利益居于主导地位。
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阈中,原子化个人作为行动主体使公民个体能够自由、平等地言说、表达;网络结构的公共能量场为公民的对话协商提供公开、平等、真实的场域;话语的正当性能够排除不真实或者无意义的话语,从而尽可能地吸纳真实的公民利益诉求;采取部分人对话的话语形式则为后现代公共利益的聚合提供了可能和途径;而良好的公民教育和普遍的公共精神,则成为后现代公共利益高效有序聚合的重要因素。
[1]Matshall·Gary,S.Choudhury·Enamul.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Re-Presenting a Lost Concept[J].Americ 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97,(1).
[2][美]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黄显中,袁红娟.后现代话语中的行政公共性[J].宁夏社会科学,2012,(1).
[4]张康之,张乾友.“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公共行政概念[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1).
[5][美]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行政——话语指向[M].楚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张康之.探索公共行政的民主化——读《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7][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168.
[8]梁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现实抑或乌托邦?——基于对南京市“话语民主”实践的实证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7,(6).
[9]尚虎平.是“公共能量束”而非“公共能量场”在解决着我国“焦点事件”——《后现代公共行政》评述兼议我国“拐点行政”走向[J].社会科学,2008,(8).
[10][英]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83.
[11][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