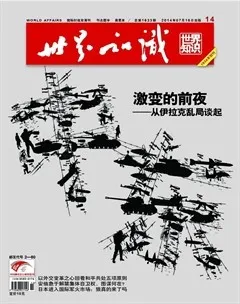沉重的留学生
我的外交生涯中结识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是个重庆女孩,叫张炜。虽然20年过去了,往事却依旧非常清晰。记得与张炜在一起聊天,她谈的最多的是关于她和她的先生如何结识的过程。他的先生罗兰是我的好朋友,当时是苏黎世大学东亚所的助教,是位很儒雅的瑞士男孩。罗兰曾在我的母校南京大学留过学,我们很有些共同语言。他是欧洲汉学界的后起之秀,记得他的研究领域是《儒林外史》。我与罗兰的交流大多使用半文半白的汉语,他向我坦承,他的古汉语水平要比现代汉语高很多。他所在的东亚所教授高斯曼也是这样,说起现代汉语磕磕巴巴,但却是研究《左传》的高手。
张炜只是在德语区留学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留学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很多学子来到德语区留学。所谓的德语区包括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卢森堡算半个。这众多的莘莘学子中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高端人才,比如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曾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的吴启迪,曾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的田力普等。德语区,尤其是德国和瑞士,凭借其深厚的人文科学底蕴以及世界领先的科技水平,近年来正成为吸引中国学子前去留学的热点。
两个月前,我应邀前往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为今年新入校的中国留学生做领保报告。随着来德国等地留学生人数的大幅增加,各种领保问题开始凸显。
我在德国工作的第一个任期时,就接触到发生在中国留学生身上的领事保护案件。一个中国男孩在德国东部某城市留学,其间与一个中国女留学生相恋。两个年轻人相处久了,免不了磕磕碰碰,产生一些矛盾。失望的女孩遂提出分手。绝望的男孩冲动之下将女孩软禁在自己的宿舍,试图让女孩回心转意。未果之后,男孩对女孩进行性侵。某日,女孩趁男孩不在向外求助。女孩得救了,男孩被德国警方拘留。恐慌之下,男孩在囚室里自尽。
上述案件是个较为极端的案例。但也多多少少反映出年轻的留学生,尤其是90后的留学生在心理和情感上的脆弱。去年末处理的一个案子让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某日,我们接到一个中国女孩从德国西部一精神病院打来的电话。女孩用非常虚弱的声音向我们求助,说她现在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四肢被绑在病床上,每天都被迫服用大量药物,很少进食,快支撑不住了。我们通过与女孩的对话以及之后向院方的了解得知,女孩某天突发精神病,行为难以自控,直至自伤。院方被迫采取强制措施对她进行治疗。
还有其他一些案例,如一中国男孩承受不住沉重的生活和学习压力自沉多瑙河,等等。
在处理这些案件的同时,我也对案件背后的因素进行了梳理。这些年轻的学子大多是85后甚至是90后的孩子,很少历世,其家庭结构也基本上是6+1模式。出来之后,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大多比较茫然。案件的当事人大都心理脆弱,抗压、抗挫能力较差,且不善于跟同学和外界沟通。所以,出问题的几率相对较高。出于报喜不报忧的心理,国内的家人和朋友往往得不到准确的信息,难以对这些孩子的现状进行把握和有效疏导。更有甚者,一名90后的中国女留学生,去年来德不久即精神崩溃,被迫送回国治疗。孰知仅隔了两个月,其父母又把她送了回来继续学业。结果可想而知,两周后,这个女孩子精神病复发,不得不再次被送回国。
虽然发生上述状况的留学生仅是少数,绝大多数留学生都能健康地生活和顺利地完成学业。但留学生的安危还是成为使馆领保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一方面鼓励当地的华人侨团和侨领从物质上给予留学生更多的支持和关爱,如每年资助中国留学生会印制留德生活指南,帮助新生尽快了解和融入当地生活,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成立各类留学生的社团和组织,为留学生的交流创造各种不同的平台。
我很高兴,过去交往的一些留德、留瑞学子现在已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我也期待更多的留学生能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早日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