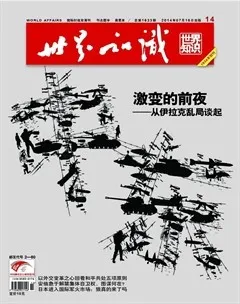“万恶之源”是伊拉克战争

原来的“金字塔”被颠倒,无法平衡
李绍先:
虽然“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今年初就占领了伊拉克重镇费卢杰,但直到6月10日该组织突然占领摩苏尔、政府军溃败而逃,伊拉克乱局才一下子凸显出来。伊拉克之所以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首先是与伊拉克战争有关。
伊拉克这个国家实际上是由三部分人构成的:60%以上的人口属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派别什叶派,是阿拉伯人,主要聚集在南部地区;20%左右是库尔德人,信仰的是伊斯兰教的第一大派别逊尼派,主要集中在北部几个省份;还有不到20%属于逊尼派,这部分人也是阿拉伯人,主要居住在中部,比如费卢杰所在的安巴尔省、摩苏尔所在的尼尼微省和提克里特所在的萨拉赫丁省,一直到巴格达。
实际上,千百年来,伊拉克一直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斗争和冲突的前沿,两大民族长期在此拉锯,伊拉克的政治生态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波斯人的伊朗是什叶派国家,而什叶派的大部分圣地(比如卡尔巴拉、纳杰夫等)都在伊拉克境内,伊朗的什叶派都到那儿朝圣。阿拉伯的伊拉克虽然什叶派人口占多数,但历史上则一向是逊尼派居于统治地位。因为阿拉伯世界主流是逊尼派,他们绝不允许伊拉克这个阿拉伯国家由什叶派把持。所以伊拉克的政治结构长期以来是金字塔型的,顶层是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处于金字塔的塔底。这个结构看似不合理,但由于历史和民族的原因各方力量却能达到基本平衡,因而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维持稳定。在萨达姆政权时期,伊拉克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也经常造反,但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随后美国在此推广所谓自由和民主。通过一人一票选举,什叶派翻身掌权了,无论是过渡时期的阿拉维总理,还是现在的马利基总理,都属于什叶派。
在库尔德方面,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伊拉克的北部设立禁飞区,库尔德地区事实上处于自治和被保护状态。20多年来,可以说库尔德地区始终是稳定的,甚至没有受到伊拉克战争的波及。由伊拉克北部杜胡克、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三省组成的库尔德自治区在伊拉克战后基本上处于准独立的状态,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司法、财政体系和军队。现在的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是库尔德人,现在的伊拉克外长霍希亚尔·兹巴里也是库尔德人。
与此同时,美国在战后对伊拉克旧政权进行了彻底清算,解散复兴党政权和伊拉克军队、情报机构、安全部队以及警察力量,并禁止前复兴党高级官员在新政府、大学、医院等公共机构中任职,逊尼派的上层精英基本上都被赶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因此,伊拉克原有的政治金字塔结构整个颠倒了过来,失去了政权、政治上被边缘化了的逊尼派精英始终不接受战后政治秩序,这是11年来伊拉克局势持续动荡的内因所在。可能一直到今天,小布什都不愿承认伊拉克战争打错了,但他很早就承认了战后美国在伊拉克政策的错误。实际上,正是伊拉克战争本身和战后美国一连串的政策失误捣碎了伊拉克政治原本脆弱的微妙平衡。
伊拉克战争以后,伊拉克中部逊尼派聚居地区从来就没有稳定过,费卢杰、拉马迪、提克里特、摩苏尔等地、甚至首都巴格达一直都处于动荡之中,爆炸不断。这些地方的抵抗武装层出不穷,美国驻军的时候,他们抗击美军;美国撤军后,则反对伊拉克中央政府。
很多人都想看马利基的“好戏”
李绍先:
伊拉克乱局还与其当前国内政治局势息息相关。伊拉克战后,美国一直试图把什叶派和逊尼派政治力量撮合起来。2010年议会选举时,无论是马利基还是其对手阿拉维,都被要求打破宗教派别界限组党。在美国的压力下,他们象征性地拉拢了一些逊尼派。
在今年4月底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以马利基为首的“法治国家联盟”又恢复了清一色的什叶派。实际上从去年8月开始,逊尼派政治力量与马利基政府就基本上处于对立甚至决裂的状态,议会都开不起来了。在本次选举中,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还是第一大党,拿下了300多个总席位的92席,遥遥领先。伊朗影响下的、由哈基姆家族领导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是第二大党,获得34个席位。之后还有萨德尔家族领导的什叶派政党,获得31个席位。这些力量虽然同属于什叶派,但都不希望马利基再次连任总理。所以不仅逊尼派抵制马利基,什叶派也希望看他的“好戏”。事实上,伊拉克乱局“凸显了马利基的无能”,使其原本看似毫无悬念的连任出现变数。
似乎全世界都觉得奇怪:为何伊拉克几万人的政府正规军在几百名反政府武装面前望风而逃?其实,伊拉克政府军虽然由什叶派构成,但是这些士兵各有各的山头,有的是听从马利基的,有的可能是听从哈基姆或萨德尔家族的,再加上摩苏尔这些地方本来就不是什叶派的传统地盘,驻守在这里的什叶派士兵根本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家园,自然是仗一打甚至没打就跑了。而ISIL是在叙利亚战场上真枪实弹打过仗的,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还懂得利用其他手段瓦解对手。
按计划,伊拉克议会7月1日要选出新议长及下一届总统和总理,不过当天召开首次会议时没能达成共识,议会“半途而废”。目前,要求总理换马的呼声高涨,越来越多的人逼马利基下台,包括美国也松口了,暗示可以换人。但是美国能换谁呢?再换个马利基党的人上台,那有什么意义?
殷罡:
我认为战后伊拉克最理想的体制应该是松散的联邦制。因为这个国家本来就是英国人将奥斯曼帝国东方三省拼凑起来的,这三个省原本就是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什叶派阿拉伯人的传统领地,这个新国家从一开始就预示着三方持久冲突。1958年革命推翻了英国人安插的逊尼派费萨尔王室,2003年的战争又推翻萨达姆的逊尼派强权控制,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必然各自为政,高度自治的松散联邦是最合理的方式。但是美国人偏要在伊拉克搞欧美式的选举。
一开始联合国选举专家设计的方案是选区代表制,即将伊拉克18个省转为18个选区,分区举行投票,由获胜政党占据该省在议会中的席位。这种选举方法有利于跨民族和宗教派别的世俗两党制发育,近似于美国的选举制度。但这样一来,什叶派的人口优势就被稀释了,因为什叶派尽管人口众多,但主要集中在南部三省,只与库尔德人占优势的省份数量相当,分散在其他省份的什叶派选民基本成了打酱油的陪衬。这样的安排激起了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塔尼的愤怒,几百万什叶派民众上街游行,坚决要求实行单一选区比例代表制,即全国不分选区,一人一票,谁人多政权就是谁的。美国人被迫屈服,什叶派人士当总理的模式就这样定下来了。
所以说,伊拉克虽然是美国人打下来的,但战后伊拉克的体制却是西斯塔尼为代表的什叶派制定的。想起来,实在是荒唐。
不要简单地把ISIL定义为恐怖组织
李绍先:
从伊拉克目前的战局来看,6月10日到14日是第一个阶段,ISIL一路攻城略地,直逼巴格达,一下子造成轰动效应。从6月14日开始到现在是第二阶段,政府军开始组织反攻,守住巴格达是没什么问题的。从目前形势看,ISIL没有力量拿下巴格达。它现在主要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把伊拉克和叙利亚打通,在叙利亚它已经完全控制了东部的拉卡省和靠近伊拉克的代尔祖尔省大部,6月15日之后基本上就是在攻打、占领和巩固边界城镇和哨所,使人员可以更自由地穿梭于伊叙两国,并控制叙、伊和约旦、沙特边界;第二个是在攻克下来的城镇巩固政权,而不是打了就跑,比如它今年初占领费卢杰后,在此地建立政府进行管理和统治。
现在伊拉克面临的问题是,跟政府作对的不只是ISIL,这个组织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人员满打满算可能也就1万人左右。关键还有很多逊尼派反政府武装,包括萨达姆时期的军官和复兴党成员(据说领头的还是萨达姆的女儿)。这些反政府武装在逊尼派聚居区拥有很深的社会土壤,特别是在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特。这些人拿起枪来就是武装人员,把枪一扔就是老百姓。有个现象值得关注:ISIL攻占提克里特后,是把这个地方交给这些人去管理的。
殷罡:
如果简单地把ISIL定义为恐怖组织,那就大错特错了。前些天约旦的贝都因人也出来游行了,声援ISIL。现在的局面不单单是一个极端组织反对伊拉克政府,而是整个逊尼派势力要“革命”,要权力,要崛起。
我一直在思考ISIL的变质问题。就是说,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的策略可能会调整,会渐渐地吸收部落长老、逊尼派长老,有可能从现在宣布建立的哈里发政权演变成某种形式的政教合一的激进强权,类似于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但不是恐怖主义的。单纯地把ISIL看成一个恐怖组织,那就小瞧它了。现在它刚刚制定建国纲领、税收政策,关键是要看这个组织变不变,它要是不变,而且还能维持下去,那就邪乎了。
教派冲突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
李绍先:
当前伊拉克乱局背后是一个很深刻的中东教派冲突问题,而这个问题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也可以追溯到伊拉克战争。
我一直强调中东地缘政治中平衡的重要性。在中东的地缘政治上,阿拉伯国家、波斯人的伊朗、突厥人的土耳其和犹太人的以色列这四大力量在内外力的相互作用下构成脆弱的动态平衡,不管这个平衡合理还是不合理,只要有这个平衡,地区局势就能大致稳定。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的中东政策是“西促和谈,东遏两伊”,即在西边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谈,在东边同时遏制伊朗和伊拉克,被海湾战争削弱了的伊拉克还与伊朗相互制衡。因此,上世纪最后十年,中东地区是相当稳定的,中东和平进程还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但是这个结构被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破坏了。加上此前的阿富汗战争,两场战争把伊朗的两个死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打掉了。这样一来,中东原来的平衡被彻底破坏,伊朗作为什叶派的波斯人的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这一结果并不是伊朗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而是美国的两场战争间接造成的。
在伊拉克战后,实际上中东隐隐约约出现了两个集团。一个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联盟,不管是在战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还是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伊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2004年约旦的前国王侯赛因提出“中东出现了什叶派新月带”,指的就是伊朗领导的什叶派联盟。据说这是伊斯兰教近1400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另一个就是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逊尼派集团,他们的目的就是遏制或削弱伊朗的力量。
后来中东出现的很多事情,包括叙利亚危机,背后都有这两个集团在较量和角力。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沙特一定要推翻巴沙尔?直观地理解,推翻巴沙尔政权对沙特并没有好处,因为阿拉伯国家一个个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很可能最终会波及沙特自身。但是对于沙特而言,作为巴沙尔盟友的伊朗才是更大的敌人,削弱伊朗是首要目标。
殷罡:
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现象。刚才绍先也讲了,伊朗在阿富汗的影响很大。美国不仅要和伊朗谈伊拉克问题,还不得不和伊朗谈阿富汗问题。阿富汗有20%的人口是什叶派,伊朗已经牢牢控制住了阿富汗中部的什叶派地区。用伊朗的话说,“我们要想搅动阿富汗的话无需派兵”。还有尼日利亚,过去是逊尼派的天下,现在几百万上千万的人转为什叶派。所以说,教派冲突不仅体现在伊拉克局势中,整个中东或者说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冲突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中东自一战以来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一个激变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