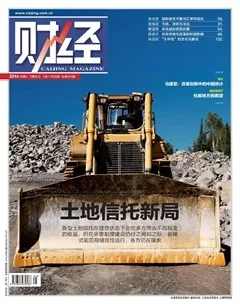“大中亚”的文化马赛克
“大中亚”的地域广阔,历史久远,民族众多,语言纷繁、宗教各殊,所以很难掌握它的文化全貌。然而,不了解它的文化脉络,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状。本文从作者自身经历出发,尝试用“大中亚”地区的东北部(贝加尔湖)、东南部(河西走廊)、西北部(阿斯塔纳)、西部(咸海)、西南部(拉合尔)和中部(塔吉克斯坦)这五小块地方,以“马赛克”(mosaic)的形式镶嵌出“大中亚”的文化轮廓。
苏武牧羊北海边
小时候常唱一首歌:“苏武牧羊北海边,雪地又冰天,羁留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
2012年夏天,我从蒙古的乌兰巴托坐了15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这是一座既有俄罗斯正教教堂又有藏传佛教寺庙的迷人城市,居民约40万,65% 是俄罗斯人。布里亚特人总数约50万,大半住在乌兰乌德之东的小镇和乡下。
当然去了苏武牧羊的北海——贝加尔湖,全世界最深、容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在历史博物馆任职的业余导游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小男孩与我一起游贝加尔湖。导游的妻子是药剂师,两个人都可以说是俄罗斯化了的布里亚特人;他们彼此以俄语交谈,但也能说布里亚特语,两人都来自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但是仍保存某些萨满教的习俗。十年前这对夫妇在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劝导下,领洗成为南方浸信会的基督教徒。
贝加尔湖畔的历史
贝加尔湖之东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和蒙古在未兴盛之前游牧过的地方,对这些民族起到过孕育作用,也对世界史发生过重要作用。既然这些民族以及其他几个后来的民族或国家,对“大中亚”的发展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就必须对某些历史大事做一个简述。
公元前3世纪匈奴崛起,前2世纪后被汉帝国遏制。公元1世纪汉朝势力进入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开始兴旺。4世纪,鲜卑崛起,统治华北,推行佛教,并主动汉化。6世纪,突厥脱离柔然而兴起于蒙古高原,继而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南下阴山,被唐降服,西突厥越过帕米尔山脉,继续西进。
8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力量进入波斯人世界,直抵锡尔河与帕米尔高原;8世纪中,唐退出西域;吐蕃乘势进入河西走廊及塔里木盆地。10世纪,突厥人开始伊斯兰化,并先后建立几个政权,在统治地区实行突厥化和伊斯兰化。13世纪初,蒙古崛起;40年间三次西征;14世纪,统治伊斯兰地区的蒙古人伊斯兰化;统治突厥地区者则自我突厥化;但蒙古上层维持政治力量长达500余年。16世纪初,欧洲人经海路到达亚洲,丝绸之路衰落。17世纪至18世纪,俄罗斯征服伏尔加河地区的鞑靼人及西伯利亚草原的哈萨克人;清朝控制蒙古高原、内蒙古与天山南北路。19世纪-20世纪,俄罗斯统治“大中亚”的大部分。20世纪末,苏联解体,大中亚进入新形势。
13世纪,有一批信奉伊斯兰教,说乌古斯突厥语的部落从撒马尔罕地区向东迁移。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定居在离黄河源头不远的青海东部,据说因为这里的水味甘美,和他们在中亚家乡的水相似。自10世纪,这一带就是汉族和藏族混居之地,元朝时又有许多穆斯林士兵被安置到此地。今天,住在甘肃临夏附近,说东乡语(近似于蒙古语)的穆斯林称为东乡族,说保安蒙古方言也信仰伊斯兰的称为保安族。而这一批说乌古斯突厥语方言的则称为撒拉族,目前约有12万人。撒拉族有语言但没有文字,目前多数人的汉语比撒拉语流利。
从甘南与河西走廊看“大中亚”
1987年夏天,我从美国到兰州开会。会后主办方组织与会者参观了刘家峡水库的(起建于南北朝时期的)炳灵寺石窟、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和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寺。这一片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相连接的土地恰又是汉文化和藏文化的边缘区,应该不是偶合。
接着我们又去了敦煌。敦煌在河西走廊之西,位处沙漠与高山之间。这里在汉代以前是汉文化的外延区,也是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的分界线。唐代吐蕃兴盛后,敦煌成为汉文明、西域文明和吐蕃文明的交汇处。
2009年,我乘汽车分五日穿越整个河西走廊,并在敦煌停留三日。这次旅行使我真正领悟到“大中亚”的意义。它不只是地理概念,也不限于国际政治,而更加是整体文化发展的概念。蒙古、内蒙古、宁夏、河西走廊、甘南、青海东部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确实是“大中亚”的有机组成部分。
代数之父与科学家
2007年我和妻子到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希瓦(Khiva)古城——以前花剌子模(Khorezm)的首都。城里除了有16世纪所建的保存完整的建筑之外,还有一个不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纪念,本地最有名的人的塑像。
“Algorithm”(计算程序)是计算机所不可缺少的。这个字是被称为“代数之父”的波斯数学家花剌子密(Al-Khorezmi,783-840)的转音,我们见到的塑像就是以出生地名为人所称道的他。他成名后迁往巴格达,用阿拉伯文发表数学和天文学专著,把印度的十进制数学介绍到阿拉伯世界。他的著作于12世纪被译为拉丁文,欧洲人因而学到当时最先进的数学和天文学。
花剌子模位处锡尔河下游的突厥游牧者与阿姆河下游的波斯农耕者之间,11世纪中叶开始强大,国君是奴隶兵出身的突厥裔军人, 12世纪初成为统治全部波斯人世界的帝国。1218年因为侮辱蒙古使节令成吉思汗震怒,决定暂停攻打西夏而发兵西征;1221年,花剌子模被蒙古军所灭。花剌子模国君死后,他的长子转战各地,企图重建故国,但1231年被蒙古军歼灭。早期的花剌子模今天是乌兹别克斯坦属下的卡拉卡尔帕克(Karakalpak)自治共和国;大部分居民说一种有别于乌兹别克语,而与哈萨克斯坦语、吉尔吉斯语更接近的卡拉卡尔帕克突厥语。
2007年秋天在乌兹别克各地旅游,我就雇用了一位在中学教英语的卡拉卡尔帕克人担任司机兼导游,和他朝夕共处八天。他的语言能力让我印象深刻。他和我们夫妻说英语,和生人说乌兹别克语,和旅行社经理说俄语,跟自己家人通电话则说一种卡拉卡尔帕克语和乌兹别克语的杂混语。
除了花剌子密,大中亚地区还出过两位世界级的科学家。一位是11世纪的医学家和哲学家伊本·西纳(Ibn Sina)。他是波斯人,生于今天的阿富汗,后来移居巴格达,写过《医典》,是阿拉伯医学的基本教科书;这本书12世纪被译为拉丁文,成为15世纪之前欧洲各地医学院的基本教科书。
另一位是帖木儿之孙,统治撒马尔罕的兀鲁伯(Ulug Beg)。他在撒马尔罕建立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天文台,并且亲自动手,带领团队测绘了1000多颗行星的方位,是哥白尼之前世界最有贡献的天文学家。伊本·西纳和兀鲁伯也都是伊斯兰教义的学者和哲学家,各有这方面传世的著作。
拉合尔所见所思
2005年秋天,我应邀访问巴基斯坦最有学术地位的旁遮普大学。当时巴基斯坦正由军人管治,校长是一位陆军中将。当他知道我对文化和宗教感兴趣之后,当即就要下属更改我的行程,把校内的几个参观合并为一个座谈会,增加校外参观的时间,还派一位青年教师和一辆汽车陪我。
旁遮普省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省份,拉合尔(Lahore)是旁遮普的省会和巴基斯坦的文化中心。从11世纪开始,拉合尔就是不同突厥裔穆斯林政权在印度的前沿基地,所以市内有不少宏伟的清真寺和广场。
帖木儿的第六世孙巴布尔失去故土之后,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和阿富汗北部游走多年。1526年,他在拉合尔站住了脚跟。这位能文能武的王子不但是莫卧儿帝国开国之君,还开创了以“察合台”突厥文写作的传统;今日的维吾尔文就是以察合台文为基础。
我在拉合尔的游走有两个收获。一是在博物馆里看到不少犍陀罗艺术的珍品,再就是私下乘出租车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边境去看降旗时的“爱国大秀”。我幸运地挤到看台上,看到巴基斯坦这边的军人表演得很不错。每当巴国(经过特别训练的)士兵踢正步踢到军靴比人头还高时,巴基斯坦的观众就大声叫喝,还夹杂着“真主伟大”的呼声,力图用声波战胜在关卡另一边表演的印度仪仗队。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独立时分为两个国家,是一个政治决定。巴基斯坦固然全都是穆斯林,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比巴基斯坦人口还要多。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是乌尔都语,但只有7%的人口以乌尔都语为母语;印度以乌尔都语为母语的人数比巴基斯坦要多出好几倍。如果避免使用乌尔都语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印度的官方语言)是一样的。
其实,绝大多数的巴基斯坦人说的是旁遮普语,而印巴边界的另一边是印度的旁遮普省,语言和巴基斯坦这边完全一样。边界口岸上演“爱国大秀”的双方演员是同文同种不同宗教的两家人。
中亚南亚唇齿相依
在欧洲人占领印度之前,印度的入侵者历来都是从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南下。2世纪时,贵霜王朝的月氏统治者就建立了包括塔里木盆地、帕米尔山脉、阿姆河流域、兴都库什山脉和恒河流域的帝国,把南亚和中亚连结在一起。
16世纪,巴布尔由兴都库什南下建立了莫卧儿帝国,从此中亚和南亚的关系更加密切,人员、物资、信息的交换非常频繁。17世纪,莫卧儿帝国开始衰落,波斯的纳迪尔国王发兵入侵印度,洗劫德里,把莫卧儿皇帝镶满了珠宝的孔雀王座当做战利品给带走了。
19世纪,拥有南亚的英国想北上中亚,统治中亚的俄国则力图防止,双方于是以阿富汗为棋盘,开展了国际外交史上著名的“大游戏”(Big Game)。
2001年“9·11”之后,美国立即出兵阿富汗,围剿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巴基斯坦是美国在这方面的盟友。但是,巴基斯坦国内也有塔利班分子,而且还有许多同情塔利班的人。苏联出兵阿富汗时,巴基斯坦人感到唇亡齿寒,在美国支持下协助阿富汗对抗苏联;美国在阿富汗用兵,就有巴基斯坦人在边境地区暗助阿富汗塔利班。印度有鉴于此,也特别对阿富汗政府给予援手,并且积极筹谋,以图长久。
2011年夏天,我们夫妇到塔吉克斯坦一游。记忆最深刻的是乘越野车从西部边境的彭吉肯特(Penjikent)到坐落于锡尔河上的苦盏(Khujand)。彭吉肯特在塔吉克斯坦的西部边境,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古代粟特人最东部的据点,现在还保留了一部分当初城堡的残垣。波斯的居鲁士国王建立了波斯帝国之后,农耕的粟特人和游牧的斯基泰人都向他臣服。在泽拉夫善河谷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彭吉肯特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粟特商人的大本营。
公元4世纪,粟特人开始在丝绸之路上活跃起来。有个从这里到甘肃武威做生意的粟特商人于313年写了一封家书。这封信没有投递到他家人手中而是被遗留在玉门关之西一个长城烽燧的底下,直到20世纪初期才被英国考古学家发现,送到大英博物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封信和其他几封遭到同样命运的书信终于被破译,让世人对当时丝绸之路上外国商人的情况多了些了解,也知道了这位先生对他自己钱财的安排。
我们行车途中到处是崇山峻岭,大半时间是面对空寂,有时偶见几户人家。经过了一条伊朗政府援建的隧道,完工才不过几年,路面就已经凹凸不平,并且严重漏水。还经过了两条中国援建的隧道,情况都很良好,所以附近居民对我们很友善,即使妇女也愿意和我合影留念。当我们在一个荒凉的大山中盘旋时,见到一队四川来的修路工人。和他们仅仅几句交谈,就感到很温馨。他们在异国荒山中的辛劳,虽然供养了老家的亲人,亲人们却可能无法想象他们的寂寞。但愿他们能受到本地人的感激。
传统与现代
哈萨克斯坦是大中亚地区地域最为广袤的国家,石油、天然气、铀、铬、钛等的存量和年产量都在世界上占很重要的地位。它也是这些国家中历史最短的国家。
哈萨克民族是在15世纪之后才形成,虽然它是一个突厥语民族,但是它的起始是由于蒙古人在南俄草原和中亚草原上建立的钦察汗国出现了分裂。
15世纪中叶时,哈萨克人还只是由术赤后裔领导的刚才形成的“乌兹别克”(汉文又称“月即别”)部落联盟的一部分。此后在草原上的斗争中,有一个蒙古贵族巴兰都黑裔脱离了原来的部落联盟,自己称汗。从这时起,所谓“哈萨克”是指那些“脱离”了原来的部落联盟的人。
哈萨克汗国先后遭到准噶尔和俄罗斯的长期进攻。哈萨克人抵挡住了前者,但是却节节败于后者。19世纪初汗王被废,全部国土为俄罗斯所占。在大中亚的各国中,哈萨克斯坦被俄罗斯统治最久,受俄罗斯影响最深。
它的前首都阿拉木图(Almaty或Alma Ata)是俄罗斯于19世纪中叶在丝绸之路的旧址上建立的新城市,作为俄罗斯在伊犁河流域和楚河流域的行政中心。1992年哈萨克斯坦独立;1994年宣布要把首都迁到国土中央的一个普通省城。不言而喻,它第一不希望首都离中国太近,第二想要以新建首都来带动经济以及国民建国的热情。1997年迁都,把原来的省城改名为“阿斯塔纳”(Astana, 意为“首都”)。这是全世界除了蒙古的乌兰巴托之外最为寒冷的首都,但是我在这里见到的建设热情可要比正被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闹得一肚子气的蒙古人要高的多。
我和妻子2011年从阿拉木图飞到阿斯塔纳,见证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大手笔,也深觉这座新首都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实验。首都的旧区是文化区,新区是行政和商业区。旧区里的文化并不怎么样,但是新区则给人以很大的希望。
一座六层楼高的大商场的外形是一个大帐篷,表现出哈萨克人并没有完全抛弃他们的游牧传统。以总统为名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有一个颇为完备的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是我的校友,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
我曾到阿拉木图的旧国会大厦拜会这座大厦的新负责人,英国籍的国际商学院院长。他告诉我,在哈萨克斯坦的四年多时间里,没有一天不为这个国家的新气象感到惊讶。他又含蓄地说,他在这个国度住得越久,就越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出于我的礼貌,也出于我对哈萨克斯坦的良好愿望,我没有告诉这位英国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中国已经被四五代人讨论过了。我只希望,有500年历史的哈萨克民族不会把下一个100年用来讨论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