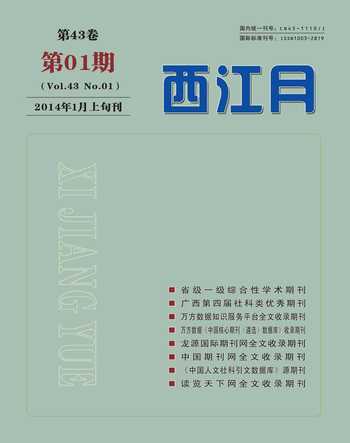雕虫赋文犹未过
杨梦皎
【摘 要】曹丕与扬雄、曹植等人针锋相对,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价值命题,孤悬一时。本文一从曹丕创作的时代政治背景出发,说明经国大业说只是曹丕思虑良多的政治策略,二以《典论·论文》的词句文法、语境联系和言意关系为论证基点,证明经国大业说也是客观造就的修辞策略。经国大业说具有言过其实、跳脱于字面外的复杂内涵,与雕虫小技说存在着互相沟通补充的成分。
【关键词】经国大业;政治策略;修辞策略;言难成意
《典论·论文》笔涉众多命题,引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专论之嚆矢,值得注意的是,曹丕还专就文学的价值功用进行了阐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句被认为是“提高文学社会价值”的明证。
与之相对,向前回溯,汉朝扬雄自命文学为“童子篆刻,壮夫不为”,同一时期,曹植更在《与杨德祖书》中声称“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显来世也。”两种说法大相径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调和的可能?论者认为这种调和是切实存在的,它首先表现为政治语境下曹丕对文章作用的真实理解,这就令文章价值不再是一个孤立并严密的命题,更接近一种双重策略性的时代话语,赋予其“经国大业”的地位言过其实。
一、“经国大业说”的政治策略
事实上,综合考察文章的历史功用和曹丕著文立說的背景,将文章抬至如此高位,是曹丕欲以副君身份聚合文士之力的政治考量,也多少包含着诱导文士专心创作,卸除文士参政威胁性的戒慎之意,兼有逢迎曹操之意。践祚帝位后的他,并未以文章治国,反而力推九品中正制,重用经学能士,前后反差,足见曹丕本人个中看法的偏差。
魏晋时期,向来被标举为文人与文章自觉的时代,“诗学政教观念相对松弛” i曹丕志高而意旷,有意要将文章从儒家传统的名教工具中解脱出来,改变汉代文人“与倡优同列”的局面。豪言中颇藏着一番开殊异之风气、摆脱复古观的壮志雄心。可以说,文章乃经国大业,看似是孔子诗教观的进一步深化,实际却更接近于扭转文学被动局面的极端性声张,非此文学自觉恐难实现。它着实不失为一种激奋人心的价值判断,但却缺乏事实支撑。如将杂芜的政治时局因素剥离开来,单论文章价值,曹丕恐怕并不认为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主要工具。反观曹植,他曾自明心迹“将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实有政治作为的抱负,然而文章之于他却只能是“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曹植曾位居要职,身处政治漩涡又憾然落败,何尝不能明白文章的真正功用,他热忱于文章之道,称文章为雕虫小技,自然不是鄙薄文学,而是以为文章大抵只能落实于个体的怡情抒怀,当被运用于治国时多是器具的用处罢了,“雕虫小技”的论调,沾染了曹植作为一个文人自悼伤怀的意味。
自曹丕之后,钟嵘受其启发,在《诗品》中将各类实用性文章统称为“经国文符”,两字变动,然而由“大业”至“文符”的更易,正点明了文章之于经国,是转换为文字性的载体来发挥作用,无法目为国之根本。曹丕本意实与钟嵘相近,“经国大业”不能真正落实于字句来考察。
另一方面,《典论·论文》的前后语境和修辞章法内部,同样自证了曹丕经国大业说的真正内涵,它不仅参合了政治话语面目模糊,也包含了论证时的夸饰、主观的有意遮蔽、遣词的策略等等,经国大业的相关论述,内核与时人的生命观相贯通,高标的功利价值多有虚设。
二、“经国大业说”的修辞策略
(一)以“文章”为中心的语词错位
探讨文章价值,恐怕难以绕过文章内涵的界定。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并没有直接言明。综合时人的认识,文章内涵的最大边界便是对各类文体的总称,郭绍虞就曾这样解释文章:“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 ii而曹丕特别提出“诗赋欲丽”的观点,创设性地强调了具有浓厚审美性的诗歌辞赋,那么文章乃经国大业的结论就分外值得推敲。诗赋显然无法承载起这样枢纽性的重量。受孔子诗教观的影响,诗歌辞赋确实有美刺讽喻的教化作用,但至多是寄意深婉甚至曲终奏雅的辅助文体,由此可见对应经国大业的“文章”概念,是相对褊狭的实用性文体。但其后的行文中,“不朽之盛事”所对应的文章,应是一切能使作者流芳于后世的个人创作,章表奏议况有其用,诗歌辞赋更能载誉千古,“文章”概念大大泛化,与前文不同。另外曹丕在《与王朗书》中也袒露:“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篇籍”自然不指一文一体。寥寥数字间,“文章”语义大幅变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论述也未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如果字斟句酌,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论调还有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内循环和内矛盾中:文章要发挥经国的作用,必须要负载大量的政治、思想文化乃至于经济、军事等各类要务理念(换言之,曹丕所称“经国之大业”的文章就是章、表、奏、议、铭、诔等实用性文体),这就使得文章的依附性大大增强,这就使得文章毕竟要以服从经国为第一要务,自然与文章独立,文学自觉的初衷相悖,与文章自我丰富完善之鹄的也不相符。许多论者言揣测其意,认为这里曹丕已将立言同立德、立功相提并论,没有看到曹丕的论述本身就将立言置于立德立功之后。当一种高远的价值期待变为价值藩篱,文章被横添过多功利色彩,其结果恐怕可以想见。这一点学界也有认识:“(曹丕)将之提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 不符合文学的实际,并且也是文学本身所承受不起的。” iii
“文章乃经国大业”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有着逻辑和语词上的来源,也与《典论·论文》部分的论述内容有关。
(二)价值说同《典论?论文》内部的文本冲突
《典论·论文》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谈起,由文人引出建安七子及其体气风格,接着就文章分类等阐发见解,关于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议论是全文的收束部分,它不仅仅隶属于文章价值命题本身,还集中烛照着时人重寸阴的生命观,对于《典论·论文》的开头亦有照应。但在另一方面,生命意识的灌注和前后相随的照应,与经国大业的价值说又有部分抵牾之处,反证着价值说的复杂与空疏。
其一,价值说带来的“文人相轻之变”。文章既是事功大业,那么各自在创作上研精覃思就能功名不朽,不必相互倾轧,如若关乎国家,也就能够超脱一己私欲。不可否认曹丕原意中包含了克服虚浮风气的初衷——今日之邺下文人,足能脱离“文人相轻“的循环律,但实际效果可能南辕北辙。能达到这一目标只限于“不朽”的“诱惑”,但文章功用至高,势必会走向以“用”论文、争夺高下的另一个循环中,乃至于令其人其文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刘希夷因一篇《代悲白头翁》而惨死其叔之手,昭昭然也。
另外需要看到的是,在经国大业和不朽盛事当中有着内在关联,它既是时人总体生命观的真切写照,又是魏初文坛的特殊生态。
一来,人们正是在慨叹岁月忽已晚的生命体验中,催生出建功立业、奋发有为的心志追求,这两者都是生命内在的流露和欲望,“形同草木之脆, 名愈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刘勰的论调无疑说明:以文章的形式足以不朽。但“经国”的欲望无法转换为“大业”的事实地位,这又是文士的普遍悲哀。
二来,建安文学能呈现出飘逸而刚健,哀恻又雄浑的法度,经国和个体不朽能相互勾连,有赖于当时特殊的时局。诚如部分学者所说:“曹操集团平定北方,乱世中有统一天下之势”。这就使得时局“乱而渐稳,变风变雅”,出现旷古未有的高蹈之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经国大业说蕴藏了文士立言垂范的衷心和途徑,这是切合实际的,但它首要的仍是将文章标举到治国枢纽的地位,抛离时代需要几无合理之处,时局加诸它以正当性,掩盖了论题本身的学理漏洞。我们看到,“经国大业说”飘忽而过,最终仍然从属于文学批评传统的立足情性的言说方式,终点是自我实现而非政治的大用。通俗地讲,或许正因为曹丕对“不朽之盛事”确有感触,真真切切,方能挥洒文墨,而“经国之大业”却多少脱离了他的真意,故而不予置评。
至此,我们可以将论题的真伪正误抛至一边,探讨曹丕遣词造句中所包孕的文学创作现象及创作习惯。它超乎于价值之上,是一种客观的修辞语境,与自古文人以言统摄己意的历史源流息息相关。
(三)对偶、偏义、夸饰的策略性修辞
曹丕洋洒数言论证文章对于个人声名的价值,慨叹年岁荣乐的“速朽”,全文中没有任何关于“经国之大业”的论述,未免令人疑窦丛生。
事实上,这首先是一种典型的偏义复指现象。偏义复词是汉语当中的独特景观,其实在语意层面也同样存在着不平衡、不对称的现象。“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重点在后不在前,
对于“经国之大业”段落中的偏义现象,学界一直有所关注。徐公持说:“从曹丕本人来看, 他在此处更重视的是‘不朽, 以下文字几乎全为演绎‘不朽‘而设” iv蔡钟翔也抱持此观点。
其二,它也是曹丕为求“句句相衔”、“字字相俪”对偶效果的策略性修辞。
试设想当时曹丕行文落笔到了最后,情发于中,声名不朽的内在冲动和年寿易尽的苍凉顿悟让他情难自禁地有了立文章为“不朽之盛事”的想法;时局危艰,文人位卑,期能“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一扫文学颓势,即使罔顾真实,出现情在理先的现象也实属正常。文人的诗性创作同时讲究“法”,“句法属于文体之“法”的范畴。而从创作技巧的角度来阐述它,则大致是指诗句中各类修辞手法的使用、节奏的安排、声律的运用、词语的搭配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上下句的体势以及句眼即字眼的安排和锤炼也属于句法的范围” v曹丕不可能置一般的创作性技法于不顾,于是先有后者慷慨悲歌,再遣一字同位同类者同“盛”相对,便出现了“经国大业”的说法。
其三,它还是带有夸饰色彩的弹性修辞。
通过前文分析“文章”在具体语境中的内涵,能发现文本内部存在着概念收缩变换的张力现象。“文章”概念由小及大,由偏至全,在一句间错位挪动,这是一种典型的语义跳跃和置换的现象。宏阔的想象,壮美的修辞,向来也是文人创作的各中一环,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中所说:“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可以说策略性修辞,同时更是富有张力的修辞,它上承庄子“汪洋恣肆,横无涯际”的文风余绪,下接“我手写我口”的创作自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曾这样说明文人的能动性:“知此义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四)言难成意的文论源流
曹丕论述中所蕴藉的种种修辞现象,在一个总体的意义上揭示了言语流于行迹的特点。于是我们看到,发出陆机《文赋》中如“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类感慨的创作者,多如恒河沙数。但曹丕的“言难成意”,却与一般意义不同。
一句“经国之大业”,让整个收束的段落和整篇《典论·论文》显得主次不明,散放不收。“经国大业说”既是曹丕有意为之,又非曹丕本意所就,真真是印证了“志隐约欲现,情悱恻莫穷”的况味。
后代多从读者接受多样化和言语的客观限度出发,去讨论言不尽意的命题,却忽略了创作者主观的统摄力。
“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也即是说:有些弦外之音因为种种原因,是不能为外人道也的,这是主观有意为之的隐没。就像曹丕身为副君,壮大文章声势的政治野心和复杂思量只能隐而不露。
中国向来有“避讳”的传统,有“虚指”的现象,汉语独有的一套表意系统,在文法上同样如此——语义内涵如若“不以为然”,那么遣词构句却可能虚美隐恶,乃至于振奋声辞。就如赋体文学极度铺张渲染背后,是文人为颂德而颂德的功利私心,乃至于真实的刺美意图,只能说十而讽一,仅仅泄露一痕一星。然而言语既可以被作者笼上重重迷障,同样可以在解读的过程中被层层还原。这使得语言具有了足以无限趋近于意的内在能力。
小 结
跳出论争夺之外,雕虫小技说最初是扬雄有感于赋体文学等繁缛富艳的弊病,但它毕竟说明了文学创作推敲考究的审美属性,囊括了“名教所不能尽” vi的部分。单从雕虫推衍来看,正因为它提供了文章有别于他者的特质,也正蕴藏了更为纯粹的独立性诉求,较之于“经国大业”可能带来的附庸性自有优势。雕虫恐怕同样带有技法论的色彩,对于“经国大业”的价值说是一种有益之补充,“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但都要依其理路,循其章法,下一番雕琢的功夫。
后世积极响应曹丕关于文章不朽的论调,“这样的观念,后代不乏其人”;但对于“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六朝及之后,仅有寥寥应者”这从侧面说明了“经国大业说”的学理的缺席,不过想来曹丕落笔飞逸,“经国大业说”的价值空位也不会拂时人之意,后人之意和一己之意,究竟有几分真实确在其次。但它与政治环境、文本其他部分的微妙关系,以及修辞上的隐藏景观却值得回味再三。这恐怕就是《典论·论文》作为一部发轫的尚不纯熟的文论专著所具有的魅力。
注释:
i.胡建次,邱美琼.中国古代文论承传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15.
ii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42.
iii敏泽.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卷)[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iv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52.
v谢群.中国诗学理论中的“法”范畴[D].复旦大学,2005:25.
vi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0.
【参考文献】
[1]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蔡仲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一)[M].北京出版社,1991.
[3]吳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M].北大出版社,2011.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选注[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章学诚,叶璞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四)[M].中华书局,1985.
[6]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卷十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M].大象出版社,2005.
[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M].1999.
[9]张振龙.“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再诠释[J].中国文学研究,2005(04):14-18.
[10]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1]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