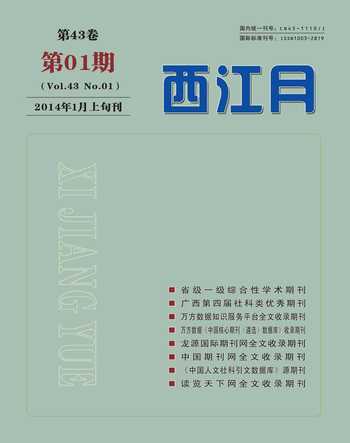全面解释犯罪描述词语的真正含义
魏超
【摘 要】将卖淫解释为同性之间的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属于当然解释而非扩大解释,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也不会侵害预见可能性。当然解释包括举重以明轻和举轻以明重,但对当然解释需要进行限制,既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要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
【关键词】同性卖淫;当然解释;罪刑法定
如今组织同性卖淫的案件屡见不鲜,而司法机关在处罚同性卖淫犯罪时却左右为难,其关键就在于,在人们心中,卖淫与嫖娼是一组对合词汇,卖淫专指女性向男性提供性服务,而嫖娼必然是男性向女性购买性服务之行为,故男性向男性卖淫成为了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为了保护民众的预测可能性,虽然此类行为严重危害了法益,也只能视为无罪。笔者拟从卖淫的真实含义出发,结合其长期被人误解的原因,人们解释方法的误区,解释方法的错误以及卖淫类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正确的解释方法和解释的实践意义等方面,说明同性卖淫并不属于法律所禁止的类推解释,也不是扩大解释,其本身就是卖淫行为的一种,属当然解释,从而探讨同性卖淫定罪的可行性,并提醒人们注意挖掘刑法分则中部分规范的构成要件长期被人们忽略的真正含义。
一、误解的原因
公安部早期發布的《关于对以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认为“卖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批复强调了发生性关系的男女的“不特定”性,且未限于男性给付金钱、财物,女性出卖肉体,此批复较好地界定了卖淫嫖娼与其他非法性关系之间的界限,揭示了卖淫嫖娼的本质特征。2001年2月28日,该批复被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所废止。后一批复认为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对性关系作了广义的解释,不限于异性之间的性交,而包括与性有关的行为;也不限于异性之间与性有关的行为,还包括同性之间畸型的性行为。但该批复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甚至不是正宗的行政规章,其法律效力有限。所以一直没有为法院所采纳。
由于社会思想沿革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的潜意识就是:卖淫必然是女性对男性的不正当性行为,且女性的行为叫做卖淫,男性的行为叫做嫖娼,因此在处理男性向男性提供性服务之时,法官便会产生疑问:如果将此类行为解释为卖淫,是不是类推解释?是不是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其实,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将自己掌握的有限事实强加于刑法规范,以自己所知道的有限事实限制刑法规范的内容。“将熟悉与必须相混淆”是人们常犯的错误。[1]人们在解释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经常会受到惯性思维和主观因素的影响,习惯于将自己熟悉的事实视为应当的事实,进而认为刑法规范所描述的事实就是自己熟悉的事实,这显然混淆了规范与事实,从而使规范处于封闭状态,因而会出现了明明属于此种犯罪构成的事实,却因为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而无法与法条结合的情况,以至于漏判误判。更何况,法条中并没有卖淫的定义,所谓卖淫的定义只是理论界的通说而已,而通说既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是不完整的,因为“立法者难以预见到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大量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情况”。[2]既然立法者无法预料,通说的提出者同样也无法预料到。
例如,通说对于抢劫罪的要求是必须存在“两个当场”,即当场对被害人采取足以压制反抗的暴力,当场取得财物,这便大大缩小了抢劫罪的处罚范围,试想:行为人对被害人采取了足以压制反抗的暴力,但是被害人当时身无分文,行为人只能勒令被害人第二日再将钱交出,此时如果判处敲诈勒索罪,则必然不符合罪刑相适原则。再如,人们一直觉得,故意毁坏财物只能是物理上的损毁,而非用法上的损毁,曾经发生在浙江的纽扣案,行为人将价值数十万的纽扣混在一起,公司老板花了十万元请人方将其分开,如此简单明了之案件,竟然让检察官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笔者认为,检察官显然混淆了事实与规范,而且使规范处于封闭状态。“刑事立法是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从而形成刑法规范,刑事司法是将现实发生的事实与刑法规范相对应,进而形成刑事判决。”[3]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新的犯罪,即使是传统犯罪,也不乏新的手段与方式。所以,人们所熟悉的只是部分有限的事实,而构成要件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个或者一种行为,而是侵害此种法益的整个犯罪类型,只要属于某犯罪类型,就应当且必然被描述该类型的构成要件所涵摄,换言之,如果人们能够充分认识到各类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任何犯罪,都可以将之“套”入法条之内。“所以,将规范的涵摄范围限定为解释者所知的有限事实,并不合适。” [4] 因此,将卖淫固步自封在仅限于女性向男性提供性服务的说法,只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形态,其他形态其实也是存在的,只是因为长期没有出现被我们选择性忽视而已。
二、解释方法的误区
有学者提出,此种违反日常理解的解释可能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应当通过两高或者人大做出有权解释方可以定罪。“学者提出这样的顾虑,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自己的解释结论没有法律效力; 二是因为自己的解释结论属于类推解释。” [5]换言之,人们要求有权解释时,总是因为觉得自己只是学者,解释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没有权利作出这种解释,希望有权解释的机关能够证明自己的结论;或者是出于对自己解释结论的不自信,认为自己的解释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属于类推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才要求有权解释。
但是,其一,刑法学者的解释结论只要具有合理性,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就可以指导司法实践, 并不是任何妥当的学理解释都必须转化为有权解释。[6]须知立法解释与立法具有同等效力,一旦做出便会起到指导作用,虽然立法解释具有追溯力,可以对当前处理的犯罪行为作出处罚,但正是因为其解释具有权威性,必将大大限制解释的范围,势必会限制到日后的司法机关处理案件,而且现在的事实证明,各类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法条,部分检察官唯解释是从,罪刑法定原则现在已经成为了“罪刑解释定”,这是非常荒谬的。换言之,立法解释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个案问题,但却过早的吞噬了法律文本的生命,消减了法律理论的繁荣,实在是得不偿失。“任何一种解释如果试图用最终的,权威性的解释取代基本文本的开放性,都会过早地吞噬文本的生命。” [7]如今社会犯罪种类日新月异,手段层出不穷,一旦出台新的解释,必然有高智商的犯罪分子会千方百计的规避解释使用新的方法实施犯罪,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台新的解释,固然给了国民足够的预测可能性,让他们清楚何种行为是犯罪,何种行为是合法的,但是亦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当他们用规避法律解释的方法实施犯罪后,便会洋洋得意的趴在法律解释上说:“你这个已经解释过了,要遵守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不能定我的罪了。”此时如果再次出台立法解释,反而会大大损害法律的权威,使法律的威严荡然无存。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指出:“法律的稳定是法律内在道德的要求,朝令夕改将导致人们无法遵守法律,这是对法律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破坏。如果有太多不一致而层出不穷的法律,那么实际上等于没有规则。” [8]拉兹、芬尼斯及我国学者提出的法治原则中,也均包括法律稳定。[9] 由此可见,立法解释并不是遏制犯罪的好方法,故笔者以为,最好的方法,还是 “就事论事”,只要是合理的解释,司法机关便应当采用,同时严格执行“罪刑法定”原则。如此,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不会受损,亦可以有效打击与预防妄想钻法律漏洞的犯罪分子。
其二,学者在理论上不能得出的结论,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也不可能得出。[10] 因为解释终究只是解释,只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而不是法律,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都必须遵循的罪刑法定原则,指的是刑法条文,而不是立法解释。因此,立法机关在制定刑法时可以根据侵害法益程度的相似性,或者为了节约立法资源,方便司法机关判处等目的,设立一定的拟制条款, 即使某种行为不完全符合某条款的要件,也可以规定按某条款论处(如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并不一定构成盗窃罪,但是法律任然规定以盗窃罪论处)。而立法解释不同。解释是对现有条文的解释,而不是制定法律。所以,“立法解释只能在现有条文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进行解释,决不能进行类推解释,否则就损害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害了国民的行动自由。” [11]例如,刑法许多条文中规定了妇女一词,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妇女解释为成年男子,否则必然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但是,立法者却可以另修改规定,将妇女修改为他人。由此亦可以看出,立法解释虽然具有权威,但是一旦做出,将会大大限制解释的范围,试想连解释效力最大的立法解释尚且受罪刑法定的制约, 司法解釋更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其后果将是各种新型犯罪的发生。
对此有人提出,是否可以修改立法?但是笔者认为,修改立法只是权宜之计,解释刑法才是刑法学者的职责所在。首先,基本法的修改必须由5年方召开一届的全国人大完成,必然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而且修改刑法的成本过高,远不如解释刑法来的经济快捷。其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 [12]。法谚有云“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而是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律不应受裁判,而应是裁判的标准。”笔者一直认为,法律工作者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而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他肩负的是整个社会的正义,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工作者都缺少正义,那么这个社会就已经无可救药。笔者也知道:“活生生的正义还需要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发现”[13],社会生活又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法律必须以固定的文字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并且适应社会生活。反复的修改立法,其实是对法律最大的伤害。英国人说:我们不希望英国的法律变更。我觉得中国人也是如此,朝令夕改是最危险的做法。依靠修改法律来适应社会生活,是不现实的。“法学的永久重大任务就是要解决生活变动的要求和既定法律的字面含义之间的矛盾”。[14]故笔者以为,一味追求立法来解决问题,不利于刑法学者提高刑法的解释能力与水平,只有解释,才能让古老的法律吃着新鲜的食物。[15]这就是前述法学的永久重大的任务。
据此,学者在解释时根本不必去要求有权解释或者人大立法,从某些程度上来说,即使他们做出了有权解释也不一定正确。因此只要根据常理做出合理的解释,便会有影响司法之功效,而且学理解释在外国影响有权解释或立法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故只要学理解释言之有理,必然可以推动立法进步。以日本刑法为例:“1907年颁布的日本刑法典第108条规定:“放火烧毁现供人居住或者现有人在内的建筑物、火车、电车、船舰或者矿井的,处死刑、无期或者五年以上惩役。”而95年以前,其第109条规定:“放火烧毁现非供人居住或者现无人在内的建筑物、船舰或者矿井的,处两年以上有期惩役。”显然,联系第108条考虑,第109条使用“或者”一词显属不当,因为现非供人居住的建筑物等可能现有人在内,因而符合第108条;现无人在内的建筑物等可能现供人居住,也符合第108条;只有烧毁现非供人居住并且现无人在内的建筑物、船舰或者矿井,才不符合第108条而应适用第109条。所以,日本的解释者一直将第109条的“或者”解释为“而且”或者“并且”。这是一种补正解释,这种解释后来于1995年被日本国会采纳,即1995年日本刑法第109条中的“或者”被修改为“而且”。” [16]
三、卖淫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及其对构成要件解释的指导
在公认的古代立法巅峰《唐律疏议》中,便有“诸断罪二五正条,其应出其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应入其罪者,举轻以明重”的归责原则,笔者认为,此原则现在依然适用,但是必须有严格限制。
首先,侵犯罪名的必须属于同一类行为,且原罪名与根据此原则确定的罪名必须属于同一罪名,即法无明文定罪的情况下根据此原则定罪的,只能以相同的罪名定罪。如我国刑法第237条虽然规定了猥亵儿童罪和强奸罪(包括强奸幼女的行为),却没有规定强奸幼男罪。有学者指出:“刑法,当然以文字为载体,不可能包含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因为那对于立法者来说是荒唐的,恰恰是‘不利于立法者的假定。” [17]根据此逻辑,强奸幼男属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科处刑罚。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放纵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这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强行与妇女或者幼女性交的行为固然成立强奸罪,但这并不意味着性交就不是猥亵行为。因为刑法规定了强奸罪与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法理论认为,猥亵行为只能是性交以外的行为。但是这种观点人为缩小了猥亵罪的构成要件和处罚范围,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猥亵是指以淫乱,下流的语言或者动作满足性欲的行为,那么不正当的性交,也就是最淫乱最下流的动作。换言之,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与普通的强奸罪都是侵犯妇女性的自己决定权,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特别关系,亦即强奸行为其实是猥亵行为的加重模式,这两者属于法条竞合中的包容关系。” [18] 故我们不应当说:强奸行为不包括强制猥亵行为,强奸罪与猥亵罪是对立关系;而应该说强奸是猥亵的一种,是最严重的强制猥亵行为,只是由于刑法特别规定了强奸罪,所以对强奸行为不再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换言之,两者是位阶关系,在以普通手段侵害妇女的性羞耻心的情况下,构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而在以足以压制反抗的手段及强奸行为侵犯妇女的性决定权的情况下,则构成强奸罪。但在刑法没有对其他不正当性交行为做出特别规范的情况下,其他不正当性交行为当然包括在猥亵概念之中。从实践上看,如果一概认为猥亵行为必须是性交以外的行为,那么,妇女对幼男实施性交以外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而与幼男性交反而不构成犯罪,这明显导致刑法的不协调。此时,便可以使用举轻以明重的原则,扪心自问,既然连猥亵儿童都要定罪,何况更严重的与幼男性交?但是此时定罪亦只能为猥亵儿童罪,否则便有违反罪刑法定之嫌。其实,刑法理论会出现如此问题,在于立法者既规定了强奸罪,又规定了强制猥亵妇女罪,部分学者才会以为强奸行为不属于猥亵。当然,也可能是立法者在设立法律时,并未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成文刑法是正义的体现。若此时以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为理由,不对这种严重破坏法益的行为进行处罚,必然有损国民感情,“纯粹从法律规范演绎出来的正义,将会是一种永久的、重复相同的僵化机械论,一种自动化或者是电脑的正义,一种非人性的正义。” [19]故在此时,应当适用类推原则,结合法条及正义原则,将立法者没有预料到的或者在立法时认为不必科处刑罚的严重破坏法益的行为加以惩处,“故从这个角度来说,成文刑法比立法者更聪明。” [20]
第二个要点在于,原罪名与根据此原则确定的罪名所侵害的法益必须是一样的。刑法第271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起刑为5000元,其侵犯法益为单位财物的所有权,而刑法264条规定的盗窃罪起刑金额为500元,此时倘若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4800元财物,而盗窃了300元财物,则无论如何也不能定盗窃罪或职务侵占罪,因为他们侵犯的不是同一个法益。但是在发票犯罪中,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规定,非法出售25份应当追诉,关于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本罪的发票50份以上应当追诉;而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中规定,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本罪的发票100份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试问,如果一人出售了20份增值税发票,80份普通发票该如何定罪?按照既定的司法解释,此种行为貌似无罪,但如果合理的利用举重以明轻原则,则可以将20份增值税发票视为20份普通发票,便可以定非法出售发票罪,因为他们侵犯的是同一法益,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当然解释之当然,是事理上的当然与逻辑上的当然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事理上的当然是基于合理性的推论,逻辑上的当然是指解释之概念与被解释之事项间存在种属关系或者递进关系。仅有事理上的当然,而无逻辑上的当然,在刑法中不得作当然解释。” [21] 笔者以为,“事理上的当然”便是指类推行为必须属于同一类行为,而“逻辑上的当然”便是指侵害的是同一法益。
刑法中关于卖淫犯罪共有2条,5个罪名,并且将其归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而非与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侵犯性权利的犯罪一起归并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当中。从立法机关将其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卖淫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卖淫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恶劣影响及善良风俗。当今社会,同性恋明显比异性恋更加不为人所接受,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同意同性婚姻,部分国家甚至将之视为犯罪,将受到拘禁至死刑的对待。在中国同性恋合法但不承认同性关系登记。由此可见,同性间的性交对社会的恶劣影响比异性之间更甚。对于如此侵犯法益的行为,如果不加以處罚,法律的威严必然荡然无存。故笔者认为,将卖淫解释为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完全符合上述当然解释的条件,因而并非夸大解释,更非类推解释。
有人会质疑,以上只是笔者的合理推测,没有说服力,在此笔者给出一个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刑法第125条规定了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有人提出疑问:非法制造大炮犯何罪?根据文理解释,大炮似乎并不属于枪支弹药,但是若合理使用上述原则,便可以得出结论:首先,非法制造大炮的行为与非法制造枪支的行为明显属于同一类型。其次,两者侵犯的法益也是相同的,都是国家对枪支弹药爆炸物的管理秩序。故可以根据举轻以明重原则来将其归于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2004年发布的《关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大口径武器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也证明了这点,全文如下: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你室《关于私自制造大口径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武器应如何认定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大口径武器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枪支罪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举轻以明重并不属于法律所禁止的类推解释,甚至不是有些学者质疑的扩大解释,而属于当然解释。
四、实践意义
扩大解释虽然是法律允许的解释,但是在实践中极易被人理解为类推解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且如今法官素质良莠不齐,如果碰上强势的律师而法官的职业素养不高,极易被律师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从而将有罪误判为无罪,使罪犯逍遥法外。如果能真正挖掘出这些词语存在而只是为人民所长期忽略的含义,结合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来定罪,则既不会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也可以做到不枉不纵,使真正的有罪之人得到追究,无罪之人免受牢狱之苦。“它对于那些容易产生偏袒和偏见的既软弱有动摇不定的法官来说,可以起到后盾的作用。通过迫使他遵循(作为一种规则)业已确立的先例,该原则减少了使他做出带有偏袒和偏见色彩的判决的诱惑。” [22]
【参考文献】
[1][3][6][16]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24,1,26,26.
[2](法)亨利·莱维·布鲁尔.法律社会学[M].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3.
[4]张明楷.正义 规范 事实[EB/OL].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36584
[5][11][13]张明楷.刑法学研究中的十关系论[J].政法论坛,2006(2).
[7][10](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M].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555,26.
[8](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商务印书馆,2005:84-85.
[9]夏恿.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1999(4).
[12](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台湾远东图书出版社,1954:89.
[14](奥)欧根·艾丽西.法社会学原理[M].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442.
[15]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三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
[17]邓子滨.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M].法律出版社,2009:187.
[18][20]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法律出版社,2011:787,237.
[19](德)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五南图书公司出版社,2000:122.
[21]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商务印书馆,2001:35.
[2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40-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