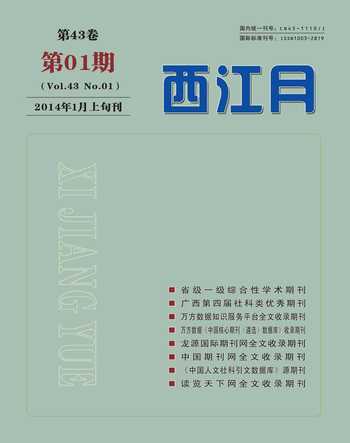撕碎客观现场的童真试验
杨梦皎
【摘 要】残雪早期作品《山上的小屋》里大量动作和言语通过背后锐利的意义碎片,对历史、生活等客观现场的方方面面进行撕扯和拼凑,残雪的作品始终存在于心灵和外物的互动关系中而非是纯主观的意识衍生物。她不惮以最大的恶意重构世界,也来自试验式创作的游戏动机,造成了一系列试验性的新颖结构,残雪的小说因此成为拒绝成长和被规训的扩展。
【关键词】《山上的小屋》;客观现场;试验;拒绝成长
《山上的小屋》是残雪于八六年发布的一系列短篇中的代表作,评论界冠以她先锋的名义和卡夫卡的模仿者,却被她不断打破并声称他们依然在自己作品的外围打转,这使得靠近其初衷变得艰难。
在这里,从禀有童稚性质的试验性写作去定位创作动机,并非强调其形式的陌生化,而是要突出残雪始终明晰着的自我力量——它形诸于小说的结构形态、小说的指向和小说的心灵表征。“试验”一词除却格式之“新”,还代表着完全主体化统摄的写作形式,代表着凭借个人意愿去安排一切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实现一种现实的不可实现,弥补存在于生命很久之前的不可弥补。
一、“试验”的终端——与客观现场决裂
现下关于残雪早期作品的苦难式解读(即控诉“反右运动”和“文学大革命”所造成的戕害)被认为是一种浅层次的阅读,我想它恐怕是对误读的误读。仅循创作者原意来看,它确实无法为残雪本人接受。而程光炜和黄子平认为残雪《山上的小屋》的一篇评述文章展示了“历史讲述如何从拯救行为变成‘攻击行为”的过程i。事实上,《山上的小屋》极力引进非历史的参照物,剖开生存焦虑于目前,确实使得小说不再具有诘难历史罪恶的宏观对应性,但却无法彻底剥离小说对客观现场的本然呼应。复现其客观性,正是在凸显作者主观“力的搏斗”。小说中活动着的客观世界由“我”与母亲、妹妹、父亲四人构成,这里毫无关爱痕迹,彼此猜疑,一个彻底虚伪、冷漠、阴暗的世界。毫无疑问它属于一种伦理拒绝,是残雪在怀疑温情脉脉的可能性,进而发出决裂的呼声。“仇母”、“仇父”的情绪,
可以看到,小说中针对客观外物的篇幅是不多的,成段落的主要是对话,少数的动作则以极精简的文字交代过去,客观世界被挤压,是作者有意用主观覆盖的结果,最终使客观世界以浓缩的状态出现。浓缩则无正当性,也折射出回避的心理动因,它仍旧属于强大的事实存在。
另外地,客观现场之所以不曾隐没,因为它通过了“记忆”这种方式完成了主观的客观化。从经验事实出发能够发现,历史坐标向来难以堂而皇之地浮现,表达它们的是细碎的事件、突然涌来的感觉、被放大的一件物品,乃至于本能的孤独感和被弃感,这正是无数客观事件的镜像重现。人类本不可能完全隔绝心灵于外,大历史退场了,它留下的应激性反应却从未消弭。诚如她个人所说,“由于这不可解的矛盾、我的个人生活变得很古怪:我热哀于吸收、玩味一切来自外界的信息、并清不自禁地卷入世俗的同时,我又随时冷酷地斩断自己与外界的种种联系〔甚至包括亲属关系)。”ii这段话亦很好地揭示了残雪的文学世界,它就立在主客观的中间,对客观作出反应和撕扯的选择,来来回回地疲于奔命和掩饰,从来不是心灵的自转。
二、“试验”的质料——再现式-提炼化的结构
《山上的小屋》全文虽然充斥着意识的流动,但仍旧具备精密而妥当的布局,残雪的写作亦充满匠心安排,只不过它以流泻的方式表露罢了。
首先,它表现为一种提炼化的结构。作品的外部世界,都凝聚在一个焦点上,那就是围绕“我”的家庭世界,这个焦点以外干干净净看不到一点社会生活的痕迹,这显得异常孤绝。一个焦点上四个人物互相拉扯,四个人物的活动和特点也完全提炼为典型,母亲虚伪(时常躲避着我的言语和眼神,却暗地里进行破坏),父亲阴暗(狼一样的眼神与斥责),妹妹直勾勾(从来不躲闪地盯着我,将母亲暗地里的小动作直截了当告诉我)。作品以“我”为中心的内部世界,可以直接抽取出小屋、抽屉、山、狼、井的外部概念,意识层面也囿于神经质、怀疑、恐惧等有限的状态。
其次,它表现为一种再现式的结构。再现式结构依附于作品的弹性和变化性而存在。
作品开头即称:“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这一表达客观现实的陈述句,在作品最后被敲碎:“我爬上山,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小屋似乎不存在,但小屋真的不存在吗?
我们接着看,清理抽屉是“每天”都在干的事,我决定到山上去看个究竟是“有一天”的事,我的确又上了山是“那一天”的事,就连文中四人什么时候吃饭(午饭还是晚饭)、“我”什么时候去了井边都无从确定,它揭示的既可能是共性的状态,也可能是特殊的某一天,某一刻。因而作品故事的结构变成了一个可以无数次再现的过程,而当“我”再一次的确又上了山,或许白石子的火焰不在了,山葡萄也不再有,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屋。
于是,作品的再现式结构是变化着、跳动着的再现,追根到底有赖于记忆的联想特征和不定性。小屋显然不是全部真实的代名词,而是印象的符号,记忆保留了它的某些特征,又在复现时联想到了其他特征,乃至因为不同情绪的参与而进行艺术化的想象重构。从这个意义讲,残雪也从小说的结构中脱胎出了记忆的结构、情绪的结构,让它们互证互现。
提炼式结构倒向程式化的特征,而再现式结构却偏向弹性化的变动,这两者不断博弈和填充,令小说如同不同质地、不同面积的点和块在糅杂运动,生出粗粝的美感。
三、“试验”的表征——童真与黑暗中的光明之心
“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当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我坐在围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听见呼啸声。是北风在凶猛地抽打小屋杉木皮搭成的屋顶,狼的嗥叫在山谷里回荡。”
“双手平放在膝头”是一种局促而紧张的状态反映,有时候它指向了做作行为——只是单纯去试验“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会听到什么,会不会每次都是“呼啸声”?这些毫末细节,参合着残雪的其他访谈言论,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此人的性格特征:她自信乃至自恋,总爱跟别人争论乃至于决裂,然后马上后悔;尽管她在国内的名声有些寂寞,却总不停翻看别人对她的评论文章、报道消息。她实在是一个太渴望和他人互动的人了,她的孤独也正来自于此。从根本上讲事后迅速后悔属于强烈的自责性人格,背后隐藏的是她难以持久的安全感,这类人常常同时喜爱标新立异,希冀在绝对的不同中稳固自信的屏障。各种文学作品、访谈录、文论著作,在一切纸面上她都坚持充满抗拒和否定性的修辞习惯,她曾訾议王安忆1990年后的写作再度退回复古主义的陈词滥调当中。两位杰出女性作家的特殊对话似乎让我们看到,她同时暴露了自己所不能的,那便是王安忆迅捷的适应能力和中规中矩的成熟形态,残雪缺乏变化的根源在于拒绝成长,这让我颠来覆去地阅读,总浮出一层悲哀的底色。我知道我在阅读曾经的自己,那些心灵感受简直再现了我童年不知其所来自的孤独与敏感,而我的童年其实非常幸福。这些情绪和记忆可能属于像我一样的很多人,而如果没有残雪的作品,将永远沉沦于成长的规训之下。
这正是残雪的意义所在,她不仅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学互通贡献颇丰,而且开辟了一种独我的心灵语境,唤询着人们关注缺失,她树立起醒目的批判地标,提醒着人们可能的迷失,即使她展示了“恶”,没有给出“善”。
注释:
i杨庆祥.小屋的恐懼和救赎——《山上的小屋》中的历史讲述[J].当代作家评论,2012(02):199-205.
ii卓今.残雪研究[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