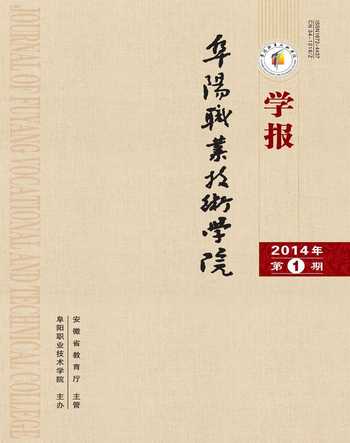南星诗歌的智性特征
王荣梅
摘要:在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营垒里,已经出现了体现情感和理智统一追求的智慧形态的诗。诗人南星是现代诗派的重要成员,他的诗善于凭具体物象和实境营造出一种整体性的境界氛围,从而生发出超越时空、与万物冥合的生命感悟。从诗思方式上说,他的诗具有感物兴情、物我交融的物感化特质,是典型的体验型主“智”的诗。本文立足南星一系列诗歌文本,研究它们主客相融、情理汇聚的智性特征及其区别于主“思”的诗及经验型智性诗之理论内核,从而阐发南星诗歌智性诉求的独特价值蕴涵。
关键词:南星;诗歌;智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14)01-0074-05
孙玉石先生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认为:“三十年代的现代派的诗多数表现了感情和理智统一追求的趋向。而主智一派诗歌大发展,更是对于‘五四以来哲理诗的更高层面上的超越。诗人把哲理思考完全融化在象征的意象之中,隐藏在抒情主体构造的深处。何其芳和戴望舒诗中亦寄寓人生哲理的思考,往往情胜于理。卞之琳、废名、曹葆华的诗,更多一些抽象的思辨和哲学的玄想色彩,但又并非以议论为诗,而为哲理的想象找到象征的载体,使智与情达到融化为一的程度。”[1]他不仅把握到了现代派的诗“感情与理智统一追求的”智性特征,而且敏锐地发现,一些诗人在情与理的融合上存在“把哲理思考完全融化在象征的意象之中”的体验型和“为哲理的想象找到象征的载体”的经验型两种类型。诗人南星是现代派的重要成员,著有诗集《石像辞》、《离失集》、《三月·四月·五月》等,他的诗有鲜明的智性特征,是典型的体验型主“智”的诗。本文立足南星一系列诗歌文本,从其诗歌的智性特征之理论内核、文本表现及价值蕴涵三个方面逐一展开论述。
一、南星诗歌智性特征的理论内核
中国现代诗歌中存在着主“智”与主“思”两类知性诗学形态。大抵上来说,1930年代是主“智”而1940年代则是主“思”的。[2]主“智”的诗,其物象不过多地承担超越其自身的本质性内涵,而是重在通过意象及其组合营造出整体性的境界氛围,升华出宇宙人生的智性体悟;主“思”的诗,则要破物之锢闭,着重从万物具象中领悟其背后的更为深广的内涵,逼问存在的真相,并以此返观自我的生存境遇。
南星的诗是典型的主“智”的诗,诗中的意象本身不过多承担隐喻或暗示的功能,它吸引人的不是思想的深邃度,而是一种弥漫性的境界氛围。南星的诗《忧虑》对“忧虑”的抒写与戴望舒的《我的记忆》中关于“我的记忆”的描绘颇为相似:“我认识你了,/这是一个最大的神秘。/为什么当你鸟一般飞落的时候/我觉不到对生客的微惊,/而且故意懒懒地延迟在床上,/如果你的来临唤醒我的小睡?”“我”的“忧虑”恰似我最熟稔的朋友,诗人通过四季的变迁,写出了物我交融中隐藏在抒情主体内部的复杂而深隐的智性感悟:“在拥挤喧嚣的街道上/我的没有闲暇的眼睛/会轻捷地选择出你的衣履,/若在阴晦多雾的深夜,/每一个路人失掉自己的影子,/我的嗅觉必应时地敏锐起来。//是很久了,我们这样地相识着,/但有谁在此真确地作证?/阶下正开着茉莉花么,/小道旁满架的茑萝么?/我相信它们醒着的眼睛/已看见我们一次又一次。//但我担心它们将受不住秋末的风,/将带着它们的记忆死去,/剩下无知的多枝的高树。/我欲依托那多枝的高树,/而它年老了,那时候只会叹息着,/为它丧失尽了的丛叶。”诗中一系列意象都是日常之所见的实境实景,没有负载特殊的隐喻功能,物与我、主与客、心灵与外界之间有一种深切的契合,抒情主体的内在波动与四季景物的自然变迁并列,二者受一种共同法则的支配,互相融合推进、相生相成。
南星的《九歌》组诗中的第一首在内容上与郑敏的《金黄的稻束》有相似的地方,不妨把二者作一比较,以帮助我们区分主“智”的诗与主“思”的诗。南星在诗中这样描写秋日的田野:“田野让行人显得渺小了。/草棉之丛是最后的站立者/用它們干枯的枝叶说深秋。/田边的古井终日无声,/井台上已有堆聚的棉果了,/谁是殷勤的采集者呢?/我看见一个屈身的女人,/停在她的棉田中如有所思,/于是我望着远处的列树/对那些长影子默默地说忆念,/直到天上有声音疾驰而来,/让我仰看无数山鸟之飞过。”在深秋的田野上,诗人温和而明亮的目光在草棉、田地、古井之间自由自在地游移,从井台边的“堆聚的棉果”,想到殷勤的采棉人,于是“屈身的女人”自然地走进视野之中,她的“如有所思”使得言说者也不由自主地沉入冥想之中,对着“列树”的“那些长影子默默地说忆念”。最后的两行,天空中疾驰的鸟声将言说者的思绪重又拉回现实世界,宁静素淡的秋日田园幻化成一个心灵的内在空间,升华出一种时空并峙、久暂共存的智性感悟。再来看郑敏《金黄的稻束》:“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是/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这首诗采用了“客观对应物”的“戏剧化”手法,即里尔克式的“把思想感觉的波动藉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而得到表现。……把搜索自己内心的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或动的,或静的)打成一片,而予以诗的表现”。[3]“金黄的稻束”象征着人的本体性“存在”,作为诗人主观思想情感的对应物,它承载着深广的理性内涵,具有鲜明的隐喻色彩。
孙玉石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在情与理的融合上存在“把哲理思考完全融化在象征的意象之中”和“为哲理的想象找到象征的载体”两种类型,可谓眼光独到。我们拿卞之琳的诗和南星的《夜宴》作一比较。《夜宴》收入《离失集》第二辑第五首,是一首极神秘的小诗:“今夜无意中开门:/土地是宽阔的冰河,/满天的月光凝冻了,/我如一个笨拙的雪人/拄树枝之杖姗姗而行,/千古的沉寂覆盖四方,/三更了,四更了…//但一声叫卖摇曳而来,/让这尖锐的声音为我招魂吧,/无限长的月光的冰桥/陆续渡来了远方的人和死去的人,/我用叫卖者的一担食物/为他们做成一席盛宴,/雄鸡请莫长啼惊了主客。”摇曳而来的“叫卖声”与卞之琳的《古镇的梦》中古镇三更时分“孩子的夜啼”、《距离的组织》中“我”在“午梦”时分,“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在内在结构上可谓异曲同工:突出的感性显示出强大的组织力、化合力,在一种突然透明的梦幻般境界中,从不同时间和空间而来的事物成为一种活生生的存在,过去、现在、将来汇聚在一起,处于我们意识活动的中央,直达我们存在的深处。这种“永久与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反复论证的“历史意识”,它对卞之琳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诗学本体意义上说,智性的体悟都需要借助某种整体性的“境界氛围”,艾略特在该文中同时提出了“诗是经验”著名论断:“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这种集中的发生,既非出于自觉,亦非由于思考。这些经验不是‘回忆出来的,他们最终不过是结合在某种境界中。”[4]主“智”的诗尤重诗境氛围的营造,《古镇的梦》、《距离的组织》等都是典型的智慧形态的诗,但这些诗“不是从情感的直接抒发入手,也不是从与情感记忆相联系的那些日常的景物、事件、日常絮语入手,而是从与生活感觉相关的智慧入手,藉由智慧引发读者对于生活的联想,对于感觉感受的联想,对于情感的引爆”。[5]这些诗并不是依循着具体的实境和事件的律动有感而发,而是凭感觉经验的跃动汇聚成新的整体,迫使事物之静动、久暂、内外的呼应在一首诗里发生,由此激发玄思,即所谓“玄思的感觉化表现”。袁可嘉认为卞之琳“诗艺最成功处不在零碎枝节的意象,文字,节奏的优美表现,而全在感情借感觉而得淋漓渗透!”[6]南星的《夜宴》则极富现实生命体验的感觉性和感受性,诗人跳过旁观的知,径直到诗境中去生活,诗的第一句“今夜无意中开门”已经决定了这首诗瞬间感受性,诗人内心的波澜与外界的物相互碰撞凝和成美妙的刹那,正是在忠实于现实的生命感受与体验这一意义上,南星的诗歌体现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品格。
二、南星诗歌智性特征的文本解读
南星擅长把隐藏在抒情主体构造深处的哲思完全融化在意象或具体实境中,并藉此生发出情味悠远的对于宇宙人生的智性感悟。收入诗集《石像辞》第二辑里的《忧虑》、《访寻》、《别意》、《诉说》、《静息》、《谢绝》等都是此类诗。如《诉说》:“我将对负着白花的老树/或新上架的牵牛/或久居在我屋檐下的/叫过秋天和冬天的麻雀/或一只偶来的山鸟/诉说我的烦忧和欢乐,/甚至是关于一件小事的:/一个小虫飞落在我的身上/或雨击打了我的窗子。//然后我向它问询,/ 如果有风吹它的细枝落地,/如果它的尖叶子偶然地/受了一个行人的摧折,/如果它的旧巢倾颓了,/如果它从山中带来了/往昔的或今日的消息,/让它殷勤地对我讲述,/用对一个友人说话的声调。”诗中物与我、内与外、心灵与自然之间有一种深切的契合,经由客观事物的洞照的心灵去体验客观事物,而那体验事物来的结果亦启发拓展了心灵的境界。南星不是纯粹从心智活动中去找感觉,而是从生活具体对象上把握到一些久暂合一、枯荣对立的生命感悟。其中《石像辞》第一辑中的《寄远》、《遗失》、《河上》、《城中》、《巡游人》、《石像辞》都体现出这一特质。《石像辞》这首诗中,“你”是“我”所在的园林熟识的访客,常来这园子里寻找“年轻的花草”,“我”则是久居这园里的一座石像:“你来过几次我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你足迹的数目,/无论留在草叶上或土地上的,/因为当这园林欢迎你的时候/我就要用力地低头了。//你将怎样猜想我的经历呢?/也许你以为我是一个新客,/还不如一株赤枫或一株白杨,/也许你的思想或记忆 /不会来到我的身上,永远地。”诗中的“你”事实上曾是“我”的过去一段现实存在,“你”对“我”的淡漠让我“对过去生出疑问了”:“我回想一些连绵雨的日子,/一些沉重的雪花封住全地的日子。/我曾看见秋冬的转移,/曾听见风歌唱着象一个牧者。//莫近前来看我吧,/这全身上的斑痕/会为我上面的话作证。/你第一次已是來迟了,/如果这园里没有年青的花草。”曾经的“你”如今成为了全身刻满斑痕的石像,“你”和“我”二者互为主客,过去、现在、未来仿佛不分彼此,共处同一时空,恍惚非意识,近于空虚的境界,于是“我”有了“非分的”希冀:“愿阳光以外的温暖/或一个生人的眼光/或虫儿们所不了解的声音/使我忘记自己的过去现在。”这种对于时空久暂的感知是在“以往”——“现在”——“将来”这样一个超越现实与历史界限的宇宙性时空视阈内展开的,生命的真实形态与终极肯定正在于这种统一,这是现代诗歌诗性智慧之达成的核心内涵。南星的《守墓人》是此类经典之作:“让我去做一个守墓人吧,/因为那坟园遥对着你的住处;/……/不说那坟园与我有了十载因缘,/也应说早住在记忆里吧,/我深信它是我的神秘的故居,/倘此时墓中有声,/必为我作真实之证语。//你在那儿寻找我的痕迹么?/我的气息留为墓地之风,/我的手泽是在每一方碑石上,/每一片枯叶上,每一棵树干上”,“从此你称我为安定的守墓人吧,/你认识坟园前的老屋了,/我将在那儿鄙视着年华,/只替你夜夜私窥月色。”诗中的“我”和“你”实际上是同一个人作为“生者”和“死者”的对话,抒情主体自我生命的律动——“我的气息”与宇宙自然的节奏——“墓地之风”契合得完美无缺。里尔克曾说:“未来走到我们中间,为了能在它发生之前就先行改变我们。”诗人并也不满足于这个时间世界,也不固定在其中,而是不断溢向过去的人,溢向生命的本源和那些走在后面的人,在那个广大辽阔的世界里,所有的生命都是“在的”,南星正是以如此痛苦、如此热情的方式抓住事物的表象,把这短暂而脆弱的世界铭刻在人们心中,并使它的本质再次在我们身上升起。
南星的诗中处处有一个沉思者,他既做演员又做观客。如《静息》:“ 如一个稳重的中年妇人,/梨树负着将熟的果实。/马缨花象是画在墙上的,/虽然它正在光荣的季节里。/ 幼年的白杨是欲睡的孩子/携带着活泼入梦。//在这样晴朗的天日下/它们有秋之预感么,/或因严肃的主人而静息?/我深怨这庭院的沉寂之形容,/但这主人只能在窗前/ 守望着它们,默默地。//那一双手何能再来呢,/ 它们会让梨树投下它的果实,/让马缨花飘散在窗格上和屋顶上,/让幼年的白杨摇摆而歌,/ 然后这儿有了清锐的笑声,/ 墙外的行人也会愕然止步。”这首诗与戴望舒《深闭的园子》在境界上颇相似:“五月的园子/已花繁叶满了,/浓荫里却静无鸟喧。//小径已铺满苔藓,/而篱门的锁也锈了——/主人却在迢遥的太阳下。//在迢遥的太阳下,/也有璀璨的园林吗?//陌生人在篱边探首,/空想着天外的主人。”这首诗中的园子的“主人”与“在篱边探首”的“陌生人”事实上都是沉思者自己,主人远走他乡,园子已一片荒芜,浪迹天外的主人,或许也在迢遥的太阳下成了“异乡人”,在另一座他人的园林外探首。南星诗《静息》中“严肃的主人”、“我”、“那一双手”、“清锐的笑声”、“墙外的行人”,他们都是沉思者自身的不同时空存在的思想情感的戏剧化的写照。两首诗中的物象情境与抒情主体之间有一种深切的内在契合和潜隐的息息沟通,作为隐藏在抒情主体的内在构造深处复杂思想情感的客观对应物,物与我似乎都受宇宙间某种共通的法则支配着,一种超越了梦与醒、过去与未来的同情的韵律在情境化氛围中流动着,生发出对于人世变异与无常的深切体悟与如梦般的淡然的接受。南星的诗歌往往人称地位颠倒错综,你和我都是一个人,新与旧、此在与他在都是一回事。如《访寻》、《不见》、《寄远》、《遗忘》、《遗失》等都是这类诗。以《不见》为例:黄昏中,“我”在村巷中行走,“用轻悄的生客之脚步”,要在黄昏雨飘起来的时候寻找“你”,为了告诉“你”:“篱上的豆蔓已互相缠结了,/花的深紫中透出离别的颜色……/葡萄架如弓背的老人/卸其担负于山鹊之口内。//青苔与香蕈是园里的先知/从容地为小道覆衣了”,所以,“我”希望“你”——“我的稀客”,“来一次园子里吧”。“你”在哪里呢?虫声唧唧,月儿朦胧,翻开一卷书册,“我”“恍然觉得千百年过去了”,使人茫然地忘了岁月。再如《寄远》中,“我”和“你”作为抒情主体不同思想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同为一人。诗中充斥着漂泊者“我”对故乡的“你”的喃喃自语:“记得你的故居么,/让我们同声说胡同的名字。/告诉你昨夜我有梦了,/梦见那窗前山桃花满枝,/梦见那阴湿的屋门/让你接这没有伞的泥水中的来客。/……但我的家乡在千里外了。/‘你是不会与大城为别的,/你是不会让幸福悄悄走过去的。/我听见你的声音沉重而柔和,/让我羞于报告自己的故事。”生活在大城的零落的异乡人“我”,最终回到了充满了异地人语的乡野,“把碎裂的怀想散播在田原上,/做了一个永远居无定所的人”,到冬天的末尾,“我”将投向何地呢:“愿意我做你故居的寄寓者么,/你就快回来敲[我的]屋门吧,/听两个风尘中的主客之相语。”
南星还写了一些词句清丽,思致缠绵的田园诗。吴兴华认为:“最近诗坛上的南星,可以说是一个最成功的田园诗人,他的大部分诗歌,如《响尾蛇》和《九歌》里的几首诗、《信念》都是极美的短诗。”[7]如《响尾蛇》:“田野是这么虚空的,…… 风留下低回的行音 / 浮荡着,从白天到夜间,/ 于是草叶更清凉了,/ 美好的噼啪之声蜿蜒而来,/响尾蛇的游行是不肯静默的,/ 在有月有星的夏夜。”再如《蛰居》:“夏天的落叶和鸡的足迹/参差地装饰了这场院。/青苔仿佛是随雨而来的,/给鸡埘染上一些岁月。//风不来吹午夜般的寂静,/我觉得自己早已睡了,/窗外有一声人语或一声鸡叫/轻飘在耳边恍惚若梦。”多么清闲洒脱的田园生活景致!两首简短的小诗,浅近的形式下潜藏着深挚的情绪,诗人精神生命的波动藉自然节奏的律动得到了戏剧化表现。田园诗英文写做Idyll,意思是一幅小小的图画或一篇短的写景诗。中国的田园诗在写自然景物时,往往掺入了一点哲理的成分。南星的田园小诗并不是在借描写景物来抒情、说理,从纯诗的观点看,它本身似乎就是由景物到观念的升华,我们仿佛被举到一个更高的气氛中。他的天才不在于象征了精神的产物,而在于诗化了精神自身,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兴华认为:“南星的诗好象冯延巳的词的‘堂庑特大,开有宋一代风气一样,……以他这几首诗,将来一定能开出一派田园诗人来。”[8]
三、南星诗歌智性特征的价值蕴涵
南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生活在沦陷区的诗人,在一个非常的年代里,他更切实地体验到了生命的个体性和本体性存在,他的诗将自己的主观世界建诸客观自然的基底,追索到了生命的更幽深的情趣,展现出人性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温情与美好。“温情”是南星诗歌最具个人化和持久性的特质。南星在《谈“温情”诗选》一文论及他要写一部《温情诗选》的理由:“普通说起来,许多人都觉得应该在安静的时候读诗,在美好的黄昏,在炉边或在雨夜,这是先使自己的心境适于或易于领会诗中所表现的心境。不过,严格说起来,好诗很足以使我们由纷乱入于宁静,由烦躁入于柔和,由空虚入于舒畅。我们无论过的是闲暇的或忙碌的生活,都愿意常常有一种‘温情陪伴着我们,使我们的心灵滋润。如果我们在寒冷的暗夜中徘徊,望见一个小小的窗子,其中透出淡红的灯光;如果我们走在远乡的道路上,临近自己的村庄了,亲切地看着道旁的一草一木,听着几声虫叫或蛙鸣;如果我们在春天黄昏的细雨中,打一把伞在林道上散步:我们不会觉得心里充满了‘温情吗?然而,这些情景是我们愿意常常有而不能的,只余下对于充满‘温情的新诗之渴望了。”[9]南星秉承了传统道家朴素悟道的精神气质,他以柔和温婉的心性和浅近细腻的思致,为我们留下了一篇篇“温情”之作,如炉火的温暖流进人们的内心,且听这样的诗句:“窗外的水滴落地结冰了,/炉火暗无颜色,/仍然是严肃的冬天,/在你遗下的大城里,/而庭院里雨如雪,/应是安睡的时候,/‘我听见夜里响尾蛇在游行了。/……殷勤怀念爱丁堡的夜,/炉火的温暖流进你的心/听敲击火箸之声,/翻开了记忆的书卷么?”这是南星写给友人的一首诗,微薄的温暖不仅带给他们一些隐秘的冬天的欢喜,而且使人们有特别的感觉能力带着浓爱翻开了记忆的书卷,去拥抱不同时空存在里的生命与形象,使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不同生命个体之间的隔绝与孤独是诗歌永恒的主题,每个人要全面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其奥秘正在于他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及万事万物发生契合与交融。 1941年,南星在散文《蠹鱼》中这样写他与曾经居住过的花溪的精神契合:“城中四分之三是田地。我看见自己做了一个清晨的巡游人,满脚是泥土,满身是露珠,禾苗如同美丽的海浪,一直涌到城墙的尽头。城角才有几间茅屋,静静的,连车轮声也听不见。树下有几只没有看守的驴在散步觅食,我也就在那儿久立不去。有时候黄昏,我的道路通着那个广阔的湖沼,水浅不能行船,但月亮把它变得又光辉,又神秘,我守在岸边,必须等到湖水暗下来夜风使人悚惧的时候。”[10]冯至的《十四行集》表达了人与人、人与万物息息相关的生命追求与宇宙感应,如《十四行诗·十八》:“……我们的生命像窗外的原野,//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又如《十四行诗·二一》:“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我们在灯下这样孤单,……/我们紧紧抱住,/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这两首诗将自我的生存融化在民族生存与时代历史之中,在一种广阔的宇宙生命的视野范围里,体味自身作为个体生命的脆弱与孤独。南星写诗有自己的哲学,正如他的好友张中行所说:“南星……是生于世俗,不黏着于世俗,不只用笔写诗,而且用生活写诗,换句话说,是经常生活在诗境中。我有时想,如果以诗境为标准而衡量个个人之生,似乎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完全隔膜,不知,当然也不要;另一种知道诗境之可贵,并有寻找的意愿;还有一种,是跳过旁边的知,径直到诗境中生活。南星可以说是最后一种”[11],诗人的天才使他本能地找到了人的精神的律动合于自然旋律的秘密,正是因为此,他才能在更深广的意义上,以跨越时空的宇宙视角从更本真的意义上把握个体的现实存在,以更广阔的心胸安泰地接受人世间的痛苦与变异。西方现代诗歌擅长通过纯艺术的力量在诗中营造一个艺术与生活二元的精神世界,其所构建的价值往往不是建立在世界万物的现实物质性的关联之上,而是存在于人的主观意志化的精神空间。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从前期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经瓦雷里、艾略特等后期象征主义者的发展,大体上呈现出一个不断摆脱物感化现实体验,不断趋向意志化经验的发展脉络。波德莱尔的“契合”诗论有着东方感悟式的物感色彩,这一点梁宗岱有切身的体会。而“魏尔兰和兰波在感觉和感受上继承波德莱尔,而马拉美在诗的完美和纯正方面发扬波德莱尔。”[12]瓦雷里则承续马拉美一脉,追求“纯诗”。瓦雷里的纯诗理论则进一步淘尽这种自波德莱尔以来的富于现世生命体验的感觉性和感受性,他认为:“在诗歌中,有些问题,是与被传统用个人经验及隐秘含义的瞬间感知所固定、所确立的原则相对立的。”[13]他更强调一种“非个人化”的“独立的诗情”,为此他甚至否认诗人的直觉与灵感,而以形式及逻辑加以取代,柏格森的“瞬间感知”也被看作是“与诗歌的本质相对立的”。艾略特提出要“像闻到玫瑰花香一样感受思想”,即把思想重新创造为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强调一种“诗的经验”,而排斥诗人自身的情感。他说:“诗人没有什么个性可以表现,只有一个特殊的工具,只是工具,不是个性,使种种印象和经验在这个工具里用种种特别的意想不到的方式来相互结合。对于诗人具有重要意义的印象和经验,而在他的诗里可能并不占有地位;而在他的诗里是很重要的印象和经验,对于诗人本身,对于个性,却可能并没有什么作用。”[14]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向诗人提供了统一凌乱世界的可能性和重认这熟识的世界的新手段,然而钻营过深同样会落入一种新的隔膜。宗白华在《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哪里去了?》一文中的开头曾引用诗人泰戈尔的一段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这是极伟大的一种天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人的“精神生命体合于自然的旋律”,[15]这种富于现实生命体验的感觉性和感受性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到之处。因为,诗歌依循着可触可感的具体实境来发展可以达到直接和存真,因为“一切超过于真实的就显得贫弱了”,而这正是诗歌的真谛,南星就是在这种态度下写他的诗歌:跳过旁边的知,径直在诗境里生活,南星的诗歌的智性追求正是在忠实于现实生存的感受与体验这一意义上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这是值得珍视的。
参考文献:
[1]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53-254.
[2] 贺昌盛.象征:符号与隐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0.
[3] 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6.
[4] [英]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王恩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8.
[5] 刘祥安.卞之琳:在混乱中寻求秩序[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6. 145.
[6] 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6.
[7] 吴兴华.谈田园诗[J].新诗,1937,2(2).
[8] 吴兴华.谈田园诗[J].新诗,1937,2(2).
[9] 南星.谈“温情”诗选[N].晨报副刊,1938-11-26.
[10]南星.蠹鱼[N]. 沙漠画报,1941-02-20.
[11]張中行.留梦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312.
[12]法国诗选[M].程曾厚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65.
[13][法]瓦雷里.瓦雷里诗歌全集[M].葛雷,梁栋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305.
[14][英]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王恩衷编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6.
[15]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