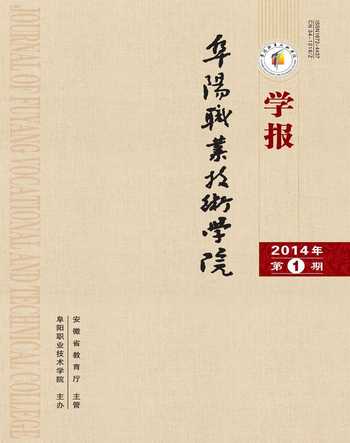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发展述评
摘要:安徽是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一度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事业之中坚。安徽农村合作运动是以农村经济衰败、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痛苦为背景的。从1931年至解放前,农村合作运动历经兴起与发展、动员与强化、继续与终结三个主要阶段,在改善农村经济状况、发展农业生产力、稳定农村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安徽农村合作运动虽然最终没有完成“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初衷,但客观上代表着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方向,它是安徽农村近代化、农业现代化一次有益尝试。
关键词: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14)01-0001-06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问题和农业危机日益严重,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呼声不断高涨。农村经济的急剧恶化,激化了社会矛盾。为缓解危机,巩固政权,尤其是抵御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持续二十多年的农村合作运动。安徽农村合作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一度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事业的中坚,因此对于它的考察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本文以安徽为考察对象,探寻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的背景、发展及实效,以期从中获得对这一时期农村合作运动历史发展轨迹完整而客观的认识。
一、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的背景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生产合作和采用合作,都是以社会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一般民众的痛苦作为它的背景的。”[1]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同样首先也是以农村经济的衰败,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痛苦为背景的。
安徽位于长江中下游,地處暖温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属于明显的季风气候:“地跨江淮,湖泊罗列,川渠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向有农业省份之称”。1926年之前,安徽普通农民生活,一向都是自给自足。据1926年的调查,在潜山等县,农民日常消费,除盐油奢好品外,如酱、醋、茶、酒、蔬菜、衣服等物品,皆自制自给。[2]1926年直鲁联军南下对抗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军是安徽尤其是皖北农村经济恶化的一个关键。皖北农村在此之前为小康时期,之后“战争频仍,水潦干旱,相逼而来,农村日趋崩溃”。[3]皖西是中国共产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国民政府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围剿,皖西在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连续作战,长期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破坏了皖西农民正常的农业生产,农民苦不堪言。
农民负担沉重是农村经济破产的另一动因。安徽为内陆落后省份,缺少大城市的辐射,农民收入多以农业为主,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租税剥削苛重,农民负担沉重,严重制约农民收入的增长。地租、赋税是农村剥削体系的核心,是压在农民头上沉重的负担。从地租形式来看,地租可分为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劳役地租,但近代以来纯粹的劳役地租已甚少见,因此安徽地租主要由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所构成。据统计,安徽1924年和1934年的实物地租同样占75%,货币地租则同样占25%。衡量地租剥削程度的标准是地租率。据1929年统计,安徽旱地的地租率平均达30%,而水田的地租率平均竟高达70%。[4]在农民的各种负担中,赋税更使其苦不堪言。其中,田赋是赋税的大宗,北洋政府明令地方有征收田赋附加之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延续北洋政府征收正附税的做法,而且大幅度提高税率。1931年同1912年相比,安徽每亩田赋的正附税总额,旱田平均上升了78.6%,水田平均上升了66.7%,甚至连山坡地也平均上升了20.5%。到1933年,在安徽全省60余县中,附加税超过正税的县份占一半以上。[5]而五花八门的临时杂捐或摊派,比正税和附加税更令农民难以应对。如粮米捐、酱油捐、土膏捐、杂货捐、店捐、车捐、戏捐、茶馆捐、乐户捐、饭馆捐,乃至鱼、肉、屠、柴、米、盐、茶等,几乎无物不征,无货不征,杂捐名称也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农民收入本来无多,而沉重的租税尤其是赋税又夺走了其大部分收入,农民背负很大的生计压力。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西方国家为转嫁危机,将生产过剩之粮食往中国倾销,使中国农产品价格不断跌落,生产利润降低,而洋货的不断入侵,使农村中的传统手工业趋于没落,农家赖为重要收入的副业也一蹶不振。这是一般所谓的“农村经济衰弱起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说法”。[6]安徽农村经济在这场危机中也是深受其害,特别是1931年江淮发生特大水灾,南京国民政府从国外购进大量粮食倾销国内,受此影响,安徽省内市场的粮食价格逐年下降,1934年与1931年相比,粮食市价下跌的总指标为13.37%,其中大麦为17.56%,小麦为4.52%,大米为17.56%,绿豆为4.35%,黄豆为8.19%,农民损失惨重。[7]
近代以后,安徽由于水利兴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自然灾害趋于频繁。据韩国学者金胜一统计,安徽在1911—1936年的26中,仅有4年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灾害,但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灾荒发生。[8]如1924年皖北及沿江一带皆被水灾。1926年皖北、皖中、皖南均被早灾。1929年全省水灾旱虫受灾区41余县市,灾民达5461882人。1931年特大水灾,全省60县有48县受灾,全省大小圩堤溃决3950余处,被淹田亩3282万亩,占全省农田的67.3%,灾民1073余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49.4%,死亡人口47277人,财产损失总计达4.46亿元。1934年特大旱灾,全省60县有49县受灾,灾民总数872万人,稻麦损失5680万担。[9]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救灾、救荒协会及其他人道主义组织积极投身于救济灾民的行列之中,其中以华洋义赈会所做的工作最为突出。
华洋义赈会,全称“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该会成立的初衷本为救灾,后来鉴于救灾不如防灾,而防灾之关键在于改善农民经济状况,遂开始提倡合作,创办合作社便成为其救灾防灾的重要手段。华洋义赈会初期组织的合作社集中在河北省境内,至1927年,河北省的合作社经华洋义赈会承认的已达359个。[10] 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安徽全省惨遭洪水浩劫,农村经济枯竭万分,农民生机几濒绝境。这次大水灾也成为安徽农村合作运动的分界点。在此之前,组织合作社不受重视,合作社数量较少,据统计,至1931年6月,全省只有农业生产合作社4个,社员48人(一说7社,216人),股金5500元。特大水灾后,南京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委托华洋义赈会于1932年春在安庆设立办事处,应用合作方式举办农赈事宜,于是安徽合作社开始蓬勃发展起来。[11]
二、1931—1936:安徽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国民安徽省政府对农村合作运动的督导早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出台之前就开始了。1930年5月27日,省府第108次常委会通过《安徽省农民合作社暂行规程》,对合作社的章程、目的、社员资格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保证了农村合作运动的规范进行。1931年的特大水灾则为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运动业务的扩展和安徽省农村合作事业的普遍兴起提供了契机。华洋义赈会1932年春即在安庆设立办事处,并从河北合作社抽调一百多名骨干,派遣到江淮各地,在受灾较重的怀宁、芜湖、东流、望江、宿松、桐城、宣城、繁昌、铜陵、无为、南陵、贵池、和县、当涂、凤阳、凤台、全椒、宿县、怀远、五河、寿县、泗县、霍邱、灵璧、阜阳25县指导农民成立互助社,并承借赈款。至1933年底,该会在上述25县共指导成立互助社2703个,社员155649人,提供赈款899498.20元。[12]农赈结束后,华洋义赈会将收回农赈贷款移充合作基金,继续推进合作事业,原设之农赈办事处改组为驻皖事务所,规定将互助社正式改组为合作社,继续指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以此壮大贫苦农民的经济能力。
除华洋义赈会外,当时还有农村金融救济处、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在安徽开展农村合作运动。1932年10月,农村金融救济处在武汉成立后,派员指导合作预备社办理紧急救济贷款,安徽主要有立煌、六安、霍山三县。至1935年底,农村金融救济处共设立预备社272个,其中六安131个,立煌106个,霍山35个。[13] 1933年9月,中国农民银行(时为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在安庆设立分行后,也开始派员下乡指导农民组织合作社,先后成立合作社61所,其主要业务为合作贷款。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南京金陵大学合作,在安徽和县乌江组织无限信用合作社22个,接着又在五河、怀远、凤阳组社,并在滁县组织耕牛会。[14]1933年,该行蚌埠分行农业科配备信用合作指导员5人,指导砀山、萧县等县组织合作社53个,翌年,又在凤阳、定远、滁县组社105个。[15]全国经济委员会只在安徽祁门组织茶叶运销合作社18所,业务量较小。安徽省内合作事业的快速发展对政府行政力量的介入提出了客观要求。
1934年4月16日,根据国民党江西南昌“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的《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合作社条例》的规定,国民安徽省政府成立了安徽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并分设县合作指导员办事处,以指导全省的农村合作事业。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成立后,省建設厅表示“自贵委会成立,(合作事业)即应改由贵会主办”。农村金融救济处、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在安徽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成立后也不再办理合作业务,并先后将已办合作社之指导权上交该会。而对于华洋义赈会所指导的合作事业,省农村合作委员会表示“本会成立之初,二十五县仍由其承办,但登记监督等行政部分由本会处理”。[16]可见,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已成为安徽省农村合作运动唯一之行政指导机构。
安徽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成立后,遂于4月底制定了工作计划大纲,以保证迅速而有条理地推进合作事业。这乃安徽行政机构第一次通过行政力量来统筹全省的农村合作事业。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成立当年即在舒城、六安、滁县、合肥、巢县、太湖、潜山、青阳8县设立合作指导员办事处;1935年增设霍山、立煌、定远、嘉山、来安、盱眙、天长、旌德、至德、宁国、休宁、庐江、含山、绩溪、黟县、歙县、祁门17县办事处;1936年续增颍上、蒙城、涡阳、亳县、阜阳、太和、临泉、广德、郎溪、泾县、石埭、太平11县办事处。并且,省农村合作委员会还兼办安徽西北边区各县农村救济事宜,在霍邱、寿县、岳西、桐城、宿松5县增设临时救济办事处,实施救济。至此,全省各县均设有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下属的合作管理机构,统一组织和管理合作社事务。作为全省合作事业的主管机关,安徽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有四:一是规划农村合作行政方针;二是指导农民进行合作事业;三是指挥监督各县合作主管机关实施合作行政;四是筹集及调剂农村合作事业之资金。在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的积极组织下,安徽农村合作运动发展速度惊人,合作社社数由1934年的1222个增至1936年的3993个,社员数由37752人增至200964人,股金数由92531元增至631861元。[17]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安徽农村合作事业规模已居全国前列,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的中坚。
安徽农村合作运动开展初期,业务上以专营为主,即一个合作社只开展一种业务,主要有信用、供给、利用、运销、兼营等形式,其中信用合作社是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据截止1936年6月底的统计,上述五种形式的合作社数量分别为2173,37,69,158,752。[18]这一时期安徽合作社的主要特征是信用合作社一枝独秀,主要原因在于安徽农村经济瓦解,农村金融枯竭,信用合作社满足了一般农民最直接的需求。农民参加合作社即为借钱,他们心中的合作社理论就是由于要借钱,才成立合作社,这是唯一的动机;由于要同银行来往,就必须组织合作社,这是唯一的方法。[19]鉴于信用合作社贷款业务沦为纯消费性质的可能性较大,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直接效用较少,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大力发展利于生产的利用合作社和增加产品收益的运销合作社,使合作业务组成趋于合理,如信用合作社贷款数额所占百分比由1934年的93.45%降至1937年的40.14%,其他形式的合作社贷款数额百分比则有所升高。[20]这一时期安徽农村合作社的一个重要业务是办理储押,即社员在秋收时将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储押于合作社,合作社预付一定之资金,待到来年春天价格上涨时再将其卖出,以此避免商人利用春秋之间的价格差价对社员进行盘剥。据统计,1936年底,安徽开展储押业务的县数已有25个,合作社302个,社员31864人。[21]
三、1937—1945:安徽农村合作运动的动员与强化
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使安徽农村经济问题有了明显的好转,特别是“1936年的农业大丰收使农村有明显的复苏”,但这一复苏势头很快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所打断。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安徽沦为战区,同年冬,省会安庆沦陷,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人员四散,以致主持乏人,翌年该会撤销,合作业务由省建设厅第四科接办。省建设厅接手指导农村合作运动后,便划分区域,成立合作指导机构,1938年在立煌等7县成立合作指导处,1939年增设合肥等14县合作指导处,1940年在桐城等6县以及未受日军侵略之县份分别设立合作指导处、指导队。至1941年底,全省共设有六安、霍山、立煌、霍邱、舒城、阜阳、太和、颍上、临泉、蒙城、合肥、无为、庐江、桐城、岳西、潜山、太湖、宿松、旌德、宁国、泾县、石埭、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太平28县合作指导处和涡亳县、全和县、寿台县、含巢县、至东、怀望、青铜贵、宣芜当、南繁、广郎10个合作指导队,并于较安全与近敌区县份联合设立凤合等14县合作指导队,辖35县。[22]至此,安徽战时状态下的农村合作指导机构已在全省范围内重新建立起来。
1942年8月,遵照国民党中央决定撤销所有合作指导处、队的有关规定,安徽于省设立合作事业管理处,于县设置合作指导室,推行新县制,在实施新县制的立煌等37县设置合作指导室,并在较安全的怀宁等10县设置合作指导员1至3人,其中休宁划归合作局设置直辖试验区。1943年郎溪、广德等县因战事关系撤销原合作指导室,派遣合作指导员1人,相机推进合作事业。在省建设厅的指导下,安徽农村合作运动有了较快的发展,合作社数目由1937年的4125个增至1945年的10574个,社员数由191000人增至874000人,人均认股数由3.3元增至51.7元。[23]
基于战时经济的特殊性,安徽这一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表现出明显的战时动员的特征,力求做到“增加生产,疏畅流通”,业务种类主要有生产、消费、信用、运销和供销。与抗战前相比,合作业务有了新的特点。第一,生产性业务重心向农村工业转移。为解决抗战时期物资被封锁而匮乏的问题,在省建设厅的指导下,全省各地农村合作社积极发展农村工业,以供给生活用品及抗战需要。如1940年8月岳西四会乡合作社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开办化学工厂,9月理事刘德卿购买原料70余担运抵事务所,一切设施12月1日开始工作,产品为墨水、粉笔、印色油、牙粉、雪花膏、肥料、洋蜡烛等7种,翌年1月开始将产品赠与大别山各机关、团体、学校。[24]第二,信用业务范围扩大。这主要体现在合作社储蓄业务的增长上。抗战前向社员放款是安徽农村合作社的主要信用业务,1941年,省建设厅要求各乡镇保合作社发动所属社员参加储蓄业务,每社员每年至少储国币2元,交由所属合作社收集保管与运用,确保无力者以劳动或物品代之。1943年,安徽合作社储存总额由1939年的16884元增至3072420元,社员存款业务增长显著。[25]除吸收社员储蓄外,国民安徽省政府1943年还制定各级合作社吸收游资办法,吸收对象为为合作社社员及家属之款项、邻社会及下级社之存余以及機关团体商店之款项。各信用社设置信用部,配合节约储蓄机关,推行储蓄运动。第三,供销业务开展。为促进省县间合作物运以扩大经济络脉、屯储重要物资以备不时之需、籍免农村金融之停滞,省建设厅于1939年设立合作产品推销所办理合作供销业务,主要包括合作产品的推销、供给和运输。由于内部组织简单,主任之下仅设总务、业务二组,人员不足,加之资金有限(总计3万元),业务未能普遍展开。1941年1月,国民安徽省政府决定扩大组织筹办合作物品供销处,该所行将撤销。但该所在1940年一年内的总交易额超过210万元,可见供销业务“前途之光明”。[26]1943年6月,安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正式成立,取代原合作产品推销所,其业务主要有供给与运销两种,代办时须征收手续费3%—5%。此外,供销处还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经济情报网,设物价调查员,并在江西、河南等周边省份及中央合作供销机构内设特约调查员,筹办物价通报,明了产品在各地的市场价格,以便供销。
四、1946—1949:安徽农村合作运动的继续与终结
抗战胜利伊始,南京国民政府即拟定了促进合作事业民主化、企业化和社会化的“五年计划”,大力发展合作金库、合作农场等业务。1946年拟定《绥靖区合作事业实施办法》,以合作事业配合军事行动,进一步简化组织合作社的程序,并组织临时合作工作辅导团四团,其中第二团就在安徽境内的宿县、灵璧、嘉山等县指导合作事宜。1946年11月,中央合作金库正式开业,于翌年4、8月在芜湖、蚌埠分设支库,主要办理侧重合作社生产和运销的短期贷款。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安徽农村合作运动在战后继续发展,合作社数由1945年的10574个增至1948年的11104个,社员数由874000人增至1074000人,人均股金数由51.7元增至6201.4元。[27]
然而,这一时期对安徽而言,内乱与“戡乱”才是最核心的内容。1946年国民安徽省政府即确定“半年来最中途要的工作,是清剿匪类”,而农村工作的重心则是“健全民众自卫队”。由于军费开支浩大,1946年10月以后国民党中央停借各种经费,国民安徽省政府各机因经费掣肘“极感苦难”,对于农村合作运动的努力空想多于实践。并且,信用合作业务也多因通货膨胀的原因而无从发展。[28]在这种情形下,安徽农村合作运动最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而终结。
五、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的实效
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虽最终未能达到“救济农村”、“复兴农村”之初衷,但合作事业倡导者、推行者“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美好初衷却是不容置疑的,当中很多热心的合作人士为安徽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振臂高呼、殚精竭虑、不畏艰难的精神及实践同样值得世人的钦佩与铭记。纵观民国时期安徽近二十年的农村合作运动历程,它在改善农村经济状况、发展农业生产力、稳定农村秩序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总体上看,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在改善当时安徽农村经济状况确实起到较大的积极作用。1934年以后,华洋义赈会、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等先后投入安徽农村合作社的放款中,充实了合作社的借款来源。由于农村金融的枯竭,安徽合作社的资金来源多依赖于以上社外资金,农村合作运动的迅速开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述社外资金的“输血博弈”。据统计,截至1937年止,合作指导机关和举办农贷的银行对安徽合作社放款总额累计超过700万元,部分缓解了日益枯竭的农村金融市场。[29]安徽农村合作社的借款利率较低。1934年合作社贷款月利率全部在1.2分以下;1935年月利率在1.2分以下的则占65.1%;1947年合作社利率虽上升至7.8%,但与当时长江中下游六省普通借贷利率14%左右相比仍较低。安徽合作社开展之后,农民有了低息筹集资金和存放余款的渠道,农民向合作社借款的比重加大。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調查,在安徽农户借贷来源中,合作社占8.6%,典当占6.9%,钱庄占0.5%,商店占13.1%,地主占30.4%,富农占16.9%,商人占23.6%。调查还写道,农民因贫困且对资金的需求是非常普遍且迫切的,诸多是告贷无门,农民所赖以流通金融者,大都为乡间地主、富户、商人、富农,他们成为农村高利贷“三位一体”的主宰者,农民借款来源,多操纵于他们手中。[30]而据《民国三十七年我国各省农村金融统计》载,在安徽农家借贷行为中,其中银行30%,合作社14%,私人39%,商店14%,典当2%,钱庄1%。[31]可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安徽农村普遍的高利贷在银行、合作社等新式借贷的冲击下,有明显之衰落。
农村合作运动对近代安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了信用贷款的支持,安徽农村合作社便积极致力于提高生产技术和改进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力得到显著的发展。合作社放款用于生产经营的情况最为普遍。据1933年10月安徽合作社贷款统计表明,放款总额61160.5元。其中,用于偿还旧债、修盖房屋、购买粮食及婚丧者6951.5元,占放款总额的11.4%;用于购置牲畜、农具、种籽、肥料、开垦土地、赎地、修圩等生产用途者52995元,占放款总额的86.6%;用于其他方面1214元,占放款总额的2%。[32]中国农民银行1947年办理的安徽淮汛重灾区贷款,用于种籽、农具、肥料、牲畜者占放款总额的99.9%,其他用途仅占0.1%。[33]以滁县为例,该县位于皖北,旱患特多,1937年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与中国农民银行商定贷款30万元,专为该县合作社举办水利之用,计该县所挖塘堰3375口,受益田亩达13400亩,从此该县水旱无虞,农产自可增加。[34]
农村合作运动在稳定当时安徽农村秩序方面还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合作社作为地方自治及管教养卫的基本组织,具有稳定乡村治安的功能。如定远西庄、李村两合作社组织守望队,购买枪支实施联防,盟约若一社业务区内发生匪警,他社应不分区域,自动驰援。[3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教育的不发达,安徽各地农村民俗尚未革新,民间各式陋习依然根深蒂固,不少农民虽贫困但却铺张浪费。如休宁农民多崇佛教,迷信之心浓厚。如遇某一神诞,自行大设铺张,婚嫁方面奢侈特甚。[36]伴随着农村合作教育和合作社福利事业的开展,这一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鉴于乡村一般贫农户因无机会受到教育,“乡间的文盲到处充斥,对于一切新思潮新运动,如什么叫做合作,怎么向银行借款等等他们根本就莫名其妙”,省农村合作委员会规定由合作社或区联会举办识字运动,并责成各地成立农村实验小学,设民众学校或成人识字班,强迫社员及其子弟入校学习。此外,该会还联合特种教育处,制定《促进农村合作及教育事业办法》,筹设中山民众学校,并派员指导,以期最大限度地向农民普及合作理念及文化知识。[37]省建设厅则组织合作社建立阅览室、音乐会及医务所等促进福利和文娱事业,1943年要求保社应设立医药室及举办壁报和音乐会,1944年应充实共同之福利事业,并办理较大规模之保健及文化设施。[38]一些合作社增设简易农仓,从事粮食储蓄,倡导节约。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的背景、发展及实效,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全新的旨在救济农村的社会经济形式是适应当时严峻的农村经济形势而出现的,政府在其中进行了主动而积极的引导,使之在缓和乡村危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农村合作运动整体体现出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改变农村现状的愿望及努力,国民党中央也将推行合作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事业来实施(1928年即被正式确立为七项国策运动之一),企图通过此举稳定国家政治经济局势,挽救农村危机,改善农村民生,建设新农村。从此意义上而言,合作运动不仅是一种普通的行政工作,更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或社会建设工程。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起源于民间团体自下而上的试验,快速发展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指导,但政府力量的过多介入恰违背了合作经济的理念及原则,而合作社经济的运行机制又有其自身固有之缺陷,再加上资金的缺乏和战争环境的限制等因素,多重困境下的安徽农村合作运动难以卓有有效地发挥其社会经济功能,并最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崩溃而终结。然而,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在安徽运行近二十年,遍及全省六十余县,在整合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经济、更新农民观念等方面留下深深的印记,客观上代表着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方向,可以说它是安徽农村近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 郑亦盛.合作论丛[M].福州:中国合作协会福建分会出版,1941:16.
[2]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Z].上海:黎明书局,1935:717.
[3] 经济资料:皖北农村近况[J].安徽地方银行旬刊,1937,1(7).
[4] 张心一.中国农佃问题的一点材料[J].统计月报,1930,2(6).
[5] 孙晓村.苛捐杂税报告[J].农村复兴委员会报告,1934(12).
[6] 蔡斌咸.现阶段中国农村金融恐慌的检讨[J].新中华,1935,3(13).
[7] 安徽省政府统计委员会.安徽省统计年鉴:民国二十三年[Z].1934:109.
[8] [韩]金胜一.近代中国地域性灾荒政策史考察——以安徽省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9] 王鹤鸣,施立业.近代安徽灾荒系年录[A].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第72号[Z].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9:224—226.
[10] 姜枫.抗战前国民党的农村合作运动[J].近代史研究,1990(3).
[11] 陈岩松.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276.
[12]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秘书处.一年来复兴农村政策之实施状况[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312—313.
[13]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8辑[Z].台北:文海出版社,1999:389.
[14] 实业部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1934年卷[Z].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159.
[15] 蚌埠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蚌埠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657.
[16] 马凌甫.安徽省农村合作事业概况[M].武汉:汉口新昌印刷,1936:4.
[17] 黄浪如.民国二十五年安徽省合作事业概况[J].安徽合作旬刊,1937,1(1).
[18] 安徽省二十四年度合作概况[J].合作月刊,1936(9).
[19] 邵仲香.合作社·借钱·银行[J].农林新报,1935,12(13).
[20] 汪效驷.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21] 黄浪如.民国二十五年安徽省合作事业概况[J].安徽合作旬刊,1937,1(1).
[22]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供销合作社志[ 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36.
[23] 徐旭.合作与社会[M].上海:中华书局,1949:171.
[24] 合作消息[J].安徽合作(半月刊),1941,2(2).
[25] 安徽省政府.安徽概览[Z].1944:259.
[26] 杨甲.本省合作供销处筹备经过[J].安徽合作(月刊),1943,4(7、8).
[27] 徐旭.合作与社会[M].上海:中华书局,1949:175.
[28] 李品仙.通力合作推进地方建设[J].安徽政治,1947,9(7、8).
[29] 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391.
[30] 中央农业实验所.各省农民借贷调查[J].农情报告,1934,2(4).
[31] 农业统计[J].中农月刊,1947,8(11).
[32] 实业部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1934年卷[Z].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141.
[33] 戴维德.皖省淮汛重灾区贷款的效果[J].中农月刊,1947,8(8).
[34] 安徽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工作概况[J].安徽合作旬刊,1937,1(12、13).
[35] 合作情报[J].安徽合作旬刊,1937,1(9、10).
[36] 舒尚志.休宁概况[J].安徽合作旬刊,1937,1(2).
[37]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8辑[Z].台北:文海出版社,1999:396.
[38] 安徽省合作建设三年计划大纲[J].安徽合作(半月刊),1942,3(1).
收稿日期:2013-11-13
作者簡介:窦祥铭(1986—),男,安徽太和县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