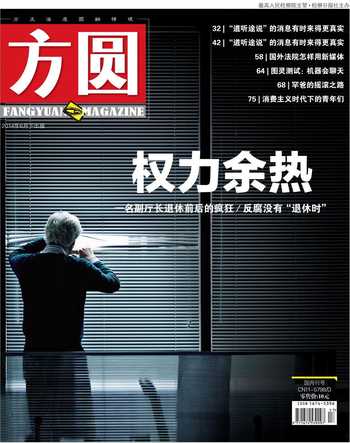锡都留守者
朱勋航
因没有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他现在仅靠每月两三百元的低保生活。因负担不起每月40元的房租,他搬出了期北山采选厂留下的职工房,生活如此不堪,甚至被和他围坐在一起烤火的人当作笑谈
云南省个旧市期北山,曾经是以锡矿而繁荣的“世外桃源”。但如今,随着矿产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此地已不复当年的繁华。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们,走的走、散的散,矿山之间,已罕有人迹。坚持在这里生活的,只有无力离开与割舍不掉故乡之情的人们了。
一场春雨后,期北山的天气骤然变得阴冷起来。高定文和五六个在矿山谋生的外地人围坐在一个火堆旁烤火、聊天。他们彼此熟悉,拥有同样艰辛的生活经历。
14年前,国有企业期北山采选厂破产后,曾有上千人的期北山矿区就一天天冷清下来。大部分职工被分流至其他厂矿单位,职工家属也随之撤离。只有少数像高定文这样自出生就几乎未离开过期北山的厂矿子弟,仍选择留守。
很难想象,眼前有些潦倒的高定文曾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他曾是云南锡业集团(以下简称云锡集团)的锡矿子弟。
在高定文的记忆中,他所在的期北山采选厂是个响当当的团级单位,从行政级别上来说,他们的厂长甚至可与个旧市市长比肩。而让高定文没预料到的是,日后他也亲历了期北山的衰败直至破产、关闭。
采选厂的黄金时代,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采选厂的工人与家属人数过千。繁盛时期,采选厂不仅建有职工宿舍,还有家属楼。那时的期北山是个繁华的小社会,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卫生所、商店、学校、菜市,还有电影院。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个旧地表砂矿的锡矿资源过早地采光了。1993年起,云锡公司连续几年巨额亏损,高定文的幸福生活也受到牵连。
1997年后,不堪重负的云锡公司开始了被称为“拆船造舰”的下岗分流,3年间裁减了1.2万从业人员,期北山采选厂随即停产。高定文不得不从一名国企职工变成了无业人员。
50岁的张云青,和高定文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他出生、成长在期北山,至今仍在期北山生活。唯一不同的是,张云青嫁给采选厂职工后,就在那儿开了一家小餐馆。
从并不宽敞的矿区公路边穿过一道低矮破旧的小门,才能看到这家小餐馆。环视餐馆:这是一间普通的红砖石棉瓦房,没有菜单,屋里唯一的客人是一名到矿山干活的村民,正在津津有味地划着5块钱买来的一碗米线。
像这样的客人,张云青的餐馆现在每天接待五六个,有二三十元的营业额。这与10多年前有天渊之别。那时期北山有三四家餐馆,竞争也很激烈,但张云青每天至少能迎来八九十名食客,营业额每天都在千元上下。
“期北山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在她的记忆里,期北山的好还不仅限于此。她小时候,这里的锡矿资源很丰富,全是露天开采,采矿工人将裸露的锡矿松动后,直接站在高处,用水将和着泥土的矿石冲到地上,然后遴选出锡矿。
如今,期北山不仅露天锡矿枯竭,水源也没有了。张云青每过半个月就得花200元买一车水。高定文家的用水量虽比不上张云青家,但干旱时节,他也不得不每月花上四五十元买水。
采选厂倒闭后,张云青的丈夫被分流到其他单位,张云青也想过要去其他地方打工,但因为“没什么技术,时间也不自由”,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
与张云青的自在相比,高定文的生活窘迫得多。因没有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他现在仅靠每月两三百元的低保生活。因负担不起每月40元的房租,他搬出了期北山采选厂留下的职工房。生活如此不堪,甚至被和他围坐在一起烤火的人当作笑谈。
更让人忧心的是,这种生活还影响到了下一代。高定文的大女儿草草出嫁,15岁的儿子也辍学在家。“打工也打不了,就是整天在外面混。看不到希望!”说起儿子的将来,高定文既担忧,又力不从心。
无聊、焦虑,这几乎是期北山居民的共性。矿山生活的乏味枯燥,更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围坐在火堆旁边的高定文却相信,矿山是他这辈子的最终归宿,不管矿山变成什么样,都改变不了他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