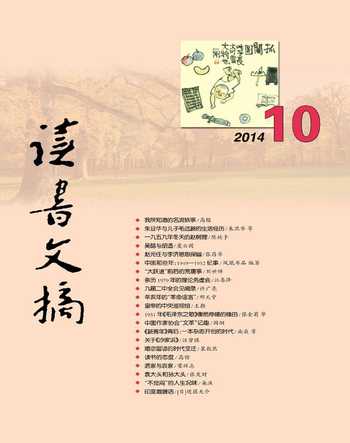赵元任与李济恩怨探幽
友人从台北“中研院”复制一帧赵元任(1892—1982)、李济(1896—1979)两对伉俪在史语所门前的合影惠我。四位老人神态祥蔼淡定面带微笑,比肩相依优雅无比。鬼使神差的我信手在照片的背面写上“泰山北斗 相逢一笑”八个字。
如果说把赵元任比作汉语言界泰山的话,喻李济为人类学、考古界的北斗,旗鼓相当。他们同为哈佛的哲学博士,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的导师,同为首届中研院(1948)的院士,在各自的领地享有各自的蓝天。
赵元任,著名的语言学家,会三十三种汉语方言,精通英、德、法、日、希腊多门外语。他谱曲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他》,世人十九耳熟能详,天下谁人不识君?惟李济(字济之)知者寥寥。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曾主持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墟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李济的名字被吞剥。一九五○年后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沫若文集》,与李济相关的文字统通被删却;鲁迅、李济与杨杏佛的合影,李济也被挖去。李济在大陆几近“销声匿迹”,只在近年又“活”了过来。
笔者将赵元任、杨步伟(1889—1981)与李济列在一起,并非故弄玄虚。盖中研院史语所历史上有一段他们的“故事”。有趣味,耐寻思。
抗战烽烟起,中研院西迁,颠沛流离,长沙、桂林,落脚昆明。流亡岁月的史语所转移时化整为零。赵元任人际关系广,寻交通工具便利,带语言组小分队捷足先抵昆明,与西南联大蒋梦麟、蒋廷黻一行同赁居拓东路; 李济率史语所大队人马跋山涉水绕道越南,1938年春节后方达昆明,栖居翠华街。史语所同仁历经艰辛,在硝烟中别后重聚,得以重整事业河山理当欢庆,孰料赵元任突然提出要请假出国。此举震惊中研院上下。其个中原因扑朔迷离,无人能言一二。直至三十年后杨步伟《杂记赵家》(《一个女人的自传》)刊布,大家始知赵元任与李济发生了摩擦。据杨步伟说,是因住房安置问题而起:“三月十日,李济之等到了昆明,可是一到就大发脾气,问研究院为何不搬到翠华街去住却住我们那儿(拓东路,笔者)!……我一看这种情势不好,不要因人家对付我们一家而害全体,不如离开为两全之计。”而且是剑及履及,说走就要走。赵、李毕竟是有二十多年交情的老兄弟,李济致信赵元任恳切慰留:“甚望兄能等孟真到后再走,此次兄请假出国想有若干重要事(如借款,笔者)必与其面商者,此决非弟所能代也。”赵元任执意并发气话,不接受同仁的饯行与送别。李济听罢“至感不安”,为表多年友情,从旧籍中捡拾殷墟古乐器图片若干相赠,以便赵日后讲音乐史参考。赵元任鸣谢。其间,傅斯年曾来电嘱李济转告赵元任,云他“上旬内可抵滇”。即在此时,赵元任仍举家离滇……
从杨步伟的表述来看,赵之出国纯因安置问题,未及其他,一时意气,而李济本人一直三缄其口,历无文字辩白或叙说。当事者如此,他人无从置喙。此事已过七十多年,成为历史化石了。笔者“好事”翻老账,并以小人之心妄测,这其中是否还有误会抑或其他,李济如何不作只字片语,有愧?不排斥赵元任出国为谋求事业的发展,也不排斥他对抗战前途的迷茫,以及难于忍受当时衣食难安的困顿,诸多复杂而现实的因素。李济背负“对付”之名是责当自负还是有难白之冤,是个“谜”。
赵元任突然要出国,他站在台前,幕后是否受夫人的点拨也未可知。
殊不知杨步伟毕竟是位大名鼎鼎的“我就是我”,不让须眉寸土的巾帼呢。杨步伟先生的天马行空可从她的“自传”中管窥一二。
她生于皖南望族,是南京著名的佛学研究机构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杨仁山之后。幼时家人给她取的诨名就有“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虽是昵称,但不乏烦言。她追求婚姻自由,自说自话一纸退婚书,休掉“三表弟”;她争取男女平权,在入新学堂考试作文《女子读书之益》时,石破惊天地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二十岁充任安徽督军父执柏文蔚北伐队办的崇实学校校长;在北京与友人创办“森仁医院”,是中国第一位女院长。她与赵元任结婚时,请胡适和朱徵大夫作男女方证婚人,自己掌勺做四菜一汤待客,自写结婚证书请两个证人签字,贴上四角钱印花税了事。婚后她与赵元任漂洋过海打天下,剑桥、清华、耶鲁、哈佛没个完。清华岁月与另两位教授太太开办“三太公司”,又办“小桥食社”,结果老本赔光,关门大吉。因清华住远郊进城不便,继而又想办汽车公司。有趣的是试办了个“节制生育所”,更有趣的是有人讽刺她自己生不了育却教别人节育,她赌气三年生了两个女儿。杨步伟自言“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她正直、热情——她的同学林贯虹病逝,她将其运回老家安葬,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只金戒指卖了帮助死者家属,因而得了“败家子”的诨号……
胡适曾戏问杨步伟在家里谁说了算时,她说:“我在家小有权,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此言真不虚,信手一例: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拟请赵元任当导师,赵还未表态,杨就说:“元任,你不答应,我得答应了!”
赵元任的为人与风格和太太则有霄壤之别。他天性纯厚,儒雅可亲,豁达幽默,从不与人争长短,是典型的妇唱夫随那一种。朋友笑话赵元任“惧内”,他毫不介意,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世俗。杨步伟的“自传”要出英文版,赵元任负责翻译并写前言。赵的第一句便说:“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太太,那么序论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要赶在赵写“自传”之前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也罢,“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她本是医师,与赵结婚后放弃自己的事业,一心当专职太太,四个子女后来在事业上也都有成就。赵元任的功勋章理所当然有杨步伟的一半。
据说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他只向她提出一个要求——“别逼我这辈子做官”。难怪胡适评价赵元任时说:“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由上述赵、杨性格来看,笔者斗胆臆测当年所谓“赵李矛盾”,从杨步伟“自传”中叙述“我一看这情势不好”的“我”字妄测,杨抑或为幕后人物或推手。再者,今人所言“清华四导师”一说,典出杨步伟的“自传”:“1924年正月,张彭春又来信决定办研究院,拟聘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其余的都是讲师或助教。”显然将李济排在导师之外,值得商榷。此言“许是杨的恣意发挥,文字中不难看出负气的成分”。时年二十九岁的哈佛人类学博士李济,是由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入清华的。当时清华设五间研究室,各居其一。李济的薪酬待遇与其他四大教授一样,月薪四百大洋,比吴宓还高一百。只不过李济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签约在前,对方付三百大洋,另一百由清华补足而已。有照片为证: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平坐者四位: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时陈寅恪尚未到校),后立者才是助教(《清华年刊》1925/26)。有诗为证。美国著名学者杨联陞在一首名为 《人文社会学院献辞》中写道,“清华研究院,五星曾聚并。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陈寅恪的助教浦江清和国学院第二届研究生戴家祥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到当时授课的导师是五位。季羡林在“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上也称“李济是五位导师之一”。
“李济与赵元任都是学术巨匠,个性独特,卓尔不群,加之赵夫人杨步伟个性强,异于常人。他们这种关系如同一个比喻,两堆篝火不能架得太近,否则彼此燃烧得不充分。”《李济传》作者岱峻这段话值得玩味。
笔者窃以为,杨步伟“自传”中涉及李济的文字,似乎少了点婉约与宽容。这恐是杨行事一贯风格。其实赵、李两家的友谊渊源还实在非同一般,且延续至今。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赵元任家居哈佛,杨步伟又有一手好厨艺,每逢节假日,赵家是中国留学生聚集地,特别是过年。友人都来此觅寻家的温馨。主雅客勤。杨步伟说“济之来得最多,胡玉祥差不多就是我们家人一样。”那时赵家长女如兰还小,大家都爱抱她,李济抱得勤。如兰稍长学音乐,李济教她学古琴,后来如兰就做了李济的干女儿。赵如兰后来成为音乐史家,执教哈佛大学。1979年赵如兰到台湾专门拜访李济,向他请益,请干爸爸讲述中国古琴(七弦琴)的发展史和自己早年习琴的体会。“那天李济的活跃超乎寻常”。
一九二五年初,赵、李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比邻而居清华照澜院旧南院。赵家平时对李家多有关照。1936年李济之父李权编《钟祥县志》,请赵元任提供方言内容。后来赵元任的《湖北钟祥方言》反请李权担任钟祥城内的发音人……次年,李济赴山西考察途中,患斑疹伤寒,重至不省人事。李济父亲李权迷信民间偏方而误诊,以致李济命悬一发。杨步伟急得冲着李权大喊:“您再不送他去医院,还要不要您这个独生儿子了?”杨步伟当机立断,自作主张找车将李济送往协和医院抢救,医生说幸亏及时,否则就完了。李济出院后,李权叫儿媳专事到赵家向杨步伟磕三个头致谢。据李济之子李光谟对笔者说:“据说先母确实向赵伯母边哭边下了跪,但赵伯母当然没有受她的叩头礼。”“这以后几十年里,李、赵两家夫妇有过很多亲密的交往,但也有过不少摩擦乃至争吵,有时甚至吵到难以开交的地步。”李光谟说,据他这个当晚辈的看,这种吵,主要是杨步伟与李济之间。吵架原因也无什么大事,主要是杨步伟总要以老前辈或李家“保护神”自居。自尊心极强的李济偏又不吃这一套。“在李济一度代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期间里,有些地方可能开罪了赵伯母,由此也引起一些无谓的纠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赵伯母到大陆来时我还问她:你们见面时还吵架不?赵伯母说:当然!我们一见面总还是要吵一吵的。”光谟对笔者再三强调说:“吵归吵,然他们之间的友谊却也是终生不改的。”
杨步伟正直、热情、大方,待友之诚之殷使她拥有广泛的人脉,当年的老友们到美国去都乐意趋访。某年,周培源携夫人王蒂澄赴美客居赵家,周夫人感慨良多。后来友人问王蒂澄对杨步伟的印象,她说“如同家人”,朋友说如何“如同”不见外呢,王蒂澄说,杨先生招呼我就像招呼她儿媳一样。一辈子争强好胜的杨步伟,她希望别人尊重她或顺着她,稍有所违,便不悦起来。一位前辈曾对笔者说,费正清夫人费慰梅是李济的老朋友。上世纪七十年代李济访美,客居赵府。费慰梅为《李济口述历史》稿赶去作补充采访。机会难得,费慰梅占用李济的时间长了点,杨步伟很不高兴,一本正经地数落费慰梅一番,弄得费慰梅几乎是哭着鼻子败兴而归。
赵元任自1938年赴美后,便没再回国内。1973年他曾携杨步伟回国,周恩来接见。1981年杨步伟去世后,受中科院语言所之邀,赵元任独自回国。他两次回国均向有关方面亲自点名要见世侄李光谟(李济之子),并与其餐叙。在1981年的那次餐席上,晚辈李光谟沿用赵家四位千金对父亲赵元任的爱称,亲切地称赵元任为“赵家Daedi”,席间,李光谟试问他的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是“教”还是“叫”。九十高龄的赵元任说:“过去也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我是觉得可以随自己的意(爱用哪一个都可以)。社会上好像用‘教字多一些,我自己有时也顺手写成‘教我如何不想他了。不过,我倒也觉得用‘叫字更贴切一些,你说呢?”李光谟认为老人回答很睿智、“高明”,因词作者刘半农的后人,在文中习惯写“教我”。多善解人意的老人。
李济、杨步伟和赵元任都次第而去,李、赵这两堆“篝火”已然熄灭,不再有不能尽燃之遗憾了。若他们在九泉下相逢,一定会“相逢一笑”,握手言欢。对我们来说,赵元任的可敬、杨步伟的可爱,以及李济的可人(宽厚)都是值得我们追怀的。
叫我如何不想他们。
(选自《清流远去——文化名人的背影》/张昌华 著/凤凰出版社/201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