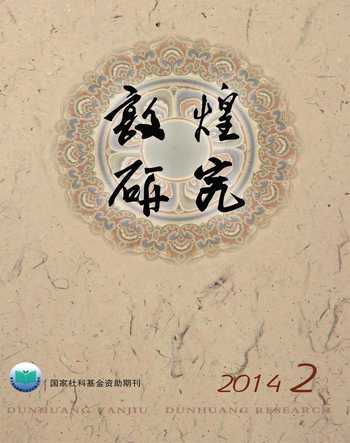高昌回鹘摩尼教稽考
内容摘要: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当地民众尽管大多都皈依了佛教,但回鹘王室仍延续漠北回鹃汗国信仰,以摩尼教是奉。汉文史书尽管记载鲜少,但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汉文、波斯文文献以及域外史籍对此却有不少记载,可填补汉文史籍的空白。从中可以看出,自8世纪末直到11世纪中期,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王国是相当流行的。
关键词:高昌回鹘;摩尼教;回鹘文文献;敦煌吐鲁番文献
中图分类号:B98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2-0068-08
Notes on Manichaeism of the Qoo Uighur Kingdom
YANG Fuxue
(Institute of Ethnic Religions and Cultures,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Since Bgü Khan, the ruler of Uighur Khanate (744-840), converted to Manichaeism in 763 CE, he quickly established Manichae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In 840, the Uighur Khanate broke down, and they began to move westward. Part of the Khanate moved to the present-day Xinjiang area, and established a regime centered on Qoo and Be-baliq, hence known historically as the Qoo Uighur Kingdom or West Uighur Kingdom. The Uighur royal family continued to accept Manichaeism. In 840, before the Uighur immigrated to the west, Manichaeism had been disseminated in the area south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 and Qoo became the center of western Manichaeism. During the Qoo Uighur Kingdom period, although most local people converted to Buddhism, the Uighur royal family still followed Manichaeism. The above mentioned events are rarely record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but the unearthed Uighur, Chinese and Persian documents in Turpan and Dunhuang as well as the Persian and Arabic documents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contain much information about this, which fills a void in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se documents we can see that, from the end of the eighth century till the midd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Manichaeism in the Qoo Uighur Kingdom was quite popular.
Keywords: Qoo Uighur Kingdom; Manichaeism; Uighur manuscripts; Dunhuang and Turpan documents
摩尼教是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创立的一种宗教,它融合了早已在中亚流行的祆教、诺思替(Gnostic)教、景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主要思想则为世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受波斯王巴拉姆一世(Vahrm I,274—277)的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进入河中地区,后逐渐传至中国内地,再于763年辗转传入回鹘,在漠北得到迅猛进展,迅速替代了原来盛行的萨满教而成为漠北回鹘汗国的国教 {1}。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瓦解,部众大部外迁,其中一支西迁新疆,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又称西州回鹘。在西迁各支中,摩尼教继续为回鹘王室所信奉,拥有相当高的地位。
一 高昌回鹘摩尼教的由来
如所周知,早在回鹘迁入以前,高昌地区已有摩尼教的传播。首先,高昌地处丝绸之路孔道,以理度之,延载元年(694)拂多诞携《二宗经》来华及开元七(719)年吐火罗国大慕阇之东行长安都应途次高昌。其次,8世纪末期,漠北回鹘汗国势力西倾,与吐蕃争夺北庭,至迟于贞元十一年(795)以前不仅从吐蕃手中夺得北庭,而且还占领了龟兹一带,已基本控制了天山东部地区,且势力向西延伸至中亚锡尔河流域[1] 201-226[2] 69-78。随回鹘势力的西倾,摩尼教向西“倒流”也是情理中事。其三,诚如羽田亨所言,吐鲁番等地有不少康国诸国的移民,可以推想,其中信仰摩尼教者当有一定数量[3]395-405,吐鲁番出土的伊朗语摩尼教文献或与之有关,如1904年出土的中古波斯语文献《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mag)》。该文献首叶为跋语,其中说到诗集抄于761年或762年,但未抄完,一直保存在焉耆(Ark)的摩尼寺中,直至Ai t?耷rid qut bulm alp bilg uy?酌ur qa?酌an在位时才最终抄完[4] 3-40。关于该可汗之归属,学界一直存在两种意见,一为昭礼可汗(824—832年在位),二为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由于昭礼可汗和保义可汗的尊号完全相同,x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早年,学界多认为这位回鹘卜古汗(ui?酌ur bu?酌ur xan)是牟羽可汗,羊年指767年丁未。后经进一步研究,被考订为回鹘怀信可汗(795—805),羊年则为803年癸未。后说可从,因为767年时吐鲁番尚为唐西州辖地,漠北回鹘汗国的势力远未及此[7]215-224。这一文献说明,八、九世纪之交,高昌已发展成为西域摩尼教的中心。803年怀信可汗曾亲至高昌,请求摩尼教的大主教——慕阇派遣三名摩尼师赴漠北传教。
二 高昌回鹘摩尼教的兴盛
回鹘西迁高昌以后,那里的摩尼教势力无疑会进一步壮大起来。敦煌出土P.3071卷背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载:
,说明在摩尼教中,日神的地位要高于月神,月神地位又高于天神。
与之可印证的是回鹘铸造的“日月光金”钱币。这种钱币原先较少见,且多为私人藏品。1979—1980年,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回鹘佛教寺院遗址发掘出一枚日月光金钱(图1)。此后续有发现,其中美国和蒙古联合考古队在蒙古汗国首都——哈拉和林城发掘出的这种钱币竟多达20多枚。此外,蒙古国近年还发现一枚花边形式的日月光金钱,属于私人收集品(图2)。钱币正面为汉文日月光金四字环读,背面铸有草体卢尼文,内容依次为?酌ur(太阳)、ükür(金星)、jaruq(光明)、ma?酌(月)、jama或jarma=jarmaq(铜钱)[20]42-44。由于原来本人所知的钱币大多发现于新疆地区,故笔者推定为高昌回鹘之遗物[21]60。考虑到蒙古高原发现的这种钱币数量更多,看来应以林梅村先生所推定的漠北回鹘保义可汗(808—821)时期更为可信[22]389。学术界存在一种说法,认为在摩尼教中,日月二神地位有别,“‘月的地位据说还要在‘日之上”[16]59。若以回鹘文木杵文书及回鹘日月光金钱观之,此说恐难以立足,否则就只能说是回鹘摩尼教对日月的崇拜已与原始摩尼教有所不同。
漠北时期,摩尼僧经常作为国使参与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外交活动,尤其是806年以后,几乎可以说是包揽了回鹘的外交活动。《宋史》卷490《于阗传》记载,建隆二年(961)于阗国“[李]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柙;玉枕一。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反映了于阗王国与北宋交往过程中摩尼僧的作用。至于高昌回鹘,史载未详,但通过各种记载的比对,仍不难看出,在与北宋的交往中,摩尼僧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如广顺元年(951)高昌回鹘入后周朝贡事。史书有如下记载:
《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广顺元年二月,[回鹘]遣使并摩尼贡玉团七十有七,白氎、貂皮、牦牛尾、药物等。”
《旧五代史》卷111《周太祖纪二》:“[广顺元年二月]辛丑,西州回鹘遣使贡方物……[丁巳] 回鹘遣使贡方物。”
《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广顺元年二月]辛丑,西州回鹘使都督来……[丁巳] 回鹘使摩尼来。”
《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周太祖广顺元年二月,西州回鹘遣都督来朝……回鹘遣使摩尼贡玉团七十七、白氎段三百五十、青及黑貂鼠皮共二十八、玉带、玉鞍辔铰具各一副、牦牛尾四百二十四、大琥珀二十颗、红盐三百斤、胡桐泪三百九十斤,余药物在数外。”
这次朝贡活动,有的指甘州回鹘,有的指西州回鹘。将上述四项记载记载结合在一起看,当以后说为确。从中可得出如下结论:广顺元年西州回鹘向后周朝贡;朝贡使团中有摩尼僧。
1981年,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粟特文摩尼教书信三封,其中,A、B两封的收件人同为马尔·阿鲁亚曼·普夫耳(mrrymn pwxr),系东方教区的慕阇。这表明,东方教区的慕阇一度驻节于柏孜克里克石窟。考虑到石窟居住条件的局限性,文献刊布者吉田丰先生认为,在高昌城的两座摩尼教寺院(遗址K和α)中应该有一座是慕阇的正式居住场所,需要时才到柏孜克里克石窟来[23]3-4。
如所周知,摩尼教的主教住于巴比伦,下辖12个教区,各教区设慕阇1人,统领全区。高昌有慕阇之设,体现了该地在摩尼教界中的重要地位。
三 摩尼教与多种宗教并存
上述记载表明,截止10世纪中叶以前,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王国一直享有独尊的地位。然而,自10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太平兴国六年(981),宋朝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对那里的宗教状况有如下记载:
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游,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24]30
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势力已超过摩尼教,相当强大,不仅寺院众多,寺中藏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许多来自中原的佛教经典与儒家著作,而且当地居民“群聚遨乐于其间”,说明成为当地老百姓的普遍信仰。“复有摩尼寺”一语说明当时回鹘之摩尼教虽不如佛教之盛,但势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波斯僧各持其法”说明景教势力也不可忽视。
上引11世纪中叶加尔迪齐著
在该文献中,对摩尼教徒的称呼使用的是Dīnāvarī,亦即敦煌写本宇字56(BD00256)《波斯教残经》所见的“电那勿”的对应词,相当于拉丁文之electi,意为“选民”,即摩尼教之僧侣。
上述记载给人的印象是,摩尼教在回鹘王室的支持下,虽持续享有较高地位,但已无法与佛教抗衡,同时,又不得不允许景教、祆教等在境内的传播。
早在回鹘西迁新疆前,佛教、景教、拜火教、道教都在这里已有数百年的传播历史了。回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接受外来文明的民族,当他们从蒙古高原西迁新疆后,很自然地受到了当地流行的佛教等多种宗教信仰的影响,大部分人皈依了佛教,另有一部分改从景教、拜火教和道教。回鹘统治者对任何宗教都不抱什么偏见,听任流行。他们“对于基督教显然加以优容,对佛教也加以奖掖”,而汗室贵族则继承蒙古高原时代的传统,仍然信仰摩尼教[26]104。
高昌回鹘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在吐鲁番所见摩尼教艺术品中也有突出反映,详见下文。总而言之,多种宗教并行不悖可以说是高昌回鹘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
四 高昌回鹘摩尼教艺术品与文献
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回鹘壁画中常可见到摩尼教遗迹。早在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就详细记录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8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25窟)的摩尼教壁画,经俄国学者奥登堡的仔细研究,此洞始被确认为摩尼教洞窟[27]44-46。在该窟的摩尼教壁画中“摩尼教传教士被一些穿着代表不同等级的白色服装的摩尼师与女弟子围绕着。这些人物,画得较小,胸口书写有美丽的粟特文字,标出各人的波斯语姓名”[28]58(图3)。
日本学者森安孝夫进一步研究认为:第38窟原为佛教洞窟,当回鹘人西迁后才被改造成摩尼教窟,后来,随着摩尼教的衰落,该窟再改回佛教窟。情况与此相类似的摩尼教洞窟尚有第27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17窟)。另外,第35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22窟)及第2窟也可能为摩尼教洞窟。其中,第38窟壁画中的生命树象征摩尼教所称光明王国,它有三杆,分别代表着三个方位:东部、西部和北部,窟中的其他壁画如寺宇图也属于摩尼教的内容[29]6-34。近年,晁华山细致地探讨了吐鲁番地区各石窟中的摩尼教因素,指出除柏孜克里克石窟之外,在吐峪沟和胜金口诸石窟中也有摩尼教壁画存在,现已觅出数十个摩尼教洞窟,其中39个大体上可以确认,另有30多个需再考察取证[30]84-93[31]1-20 。这一调查结果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但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许多学者认定这些石窟为典型的佛教洞窟[32]240-249[33]231-249[34]123-153。目前对摩尼教壁画的探寻,主要集中于吐鲁番诸石窟中。笔者认为,由于回鹘摩尼教深受佛教的影响,其艺术风格接近,而且摩尼教洞窟又与佛教洞窟混杂在一起,要准确区分出来,非为易事。除第38、27窟较为确定外,对其他摩尼教石窟的确定尚需进一步细致的工作。如吐峪沟42窟的半黑半白人骨像,吐峪沟石窟第42窟左壁有一幅半白半黑人骨造像,晁氏认为应来自摩尼教二元论,象征着人体所包含的明暗两部分[31]10。然而,摩尼教对二元论的表示并不用身体的阴阳,而是用两种概念化的树木,即黑暗死树和光明活树。该图像表示的应是不净观,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禅观思想息息相关,所依禅经主要有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和《禅法要解》等。属于佛教内容,与摩尼教无关。再如胜金口石窟北区第4窟也被定为“摩尼教窟”,依据在于该窟后壁上部所见两棵交叉树,被称作光明活树和黑暗死树。然二树所绘完全为写实手法,与摩尼教概念化用以表示善念与恶念的树木不同,树下所坐僧人为光头,不同于摩尼教僧侣的蓄发。足证胜金口石窟北4窟同为佛教石窟,与摩尼教无干[35]30。
在高昌故城,摩尼寺亦与佛寺比肩而立。在故城内K遗址正厅西侧的废墟中曾发现有一幅摩尼教女神像,头戴精致的白色摩尼教扇形帽,头后有日光光轮,细眉柳目,腴面小口,佩有耳环。她左手举起,作施无畏说法印[36]30,与龟兹佛画中的天女、菩萨几无二致。若非帽子上的标志,很难说这不是一幅佛教绘画。在同一遗址北部西南角,还出土了另一幅摩尼教众神像,上有三个女性头像,佩戴王冠似的头饰和包头布。他们圆盘大脸,与富有装饰性的龟兹、高昌佛教绘画中的菩萨极其类似,反映了回鹘佛教艺术对摩尼教绘画的强烈影响。
20世纪初以来,随着新疆吐鲁番等地探察与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大量的用回鹘文、摩尼文书写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相继出土,今所知的已达近千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部典籍:其一为吐鲁番、敦煌等地都有出土的《摩尼教徒忏悔词(Xuāstvānīft)》,系摩尼教徒忏悔自己罪过的一种文献;其二为吐鲁番发现的《二宗经
参考文献:
[1]森安孝夫.增补:ウィ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夺战及びその后の西域情势について[C]//流沙海西奖学学会编.アジア文化史论丛3.东京:山川出版社,1979.
[2]杨富学.高昌回鹘王国的西部疆域问题[J].甘肃民族研究,1990(3-4).
[3]羽田亨.漠北の地と康国人[C].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历史篇.京都:同朋舍,1975.395-405.
[4]F. W. 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ischen Hymenbuch (Mahrnamag),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2[M]. Berlin 1913.
[5]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C].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2.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6]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M].北京:中华书局,2012.
[7]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C]//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8]A. von Le Coq, Ein manichisches Buch-Franment aus Chotscho[C]//Festschrift für Vilhelm Thomsen. Leipzig 1912.
[9]J. Hamilton, Manuscrits ou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tome 1[M]. Paris 1986.
[10]牛汝极,杨富学.五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考释[J].新疆大学学报,1993(4).
[11]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12]V. Minorsky, Tamim ibn Bahr's Journal to the Uyghurs[J].Bulletin of School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2, 1948 .
[13]孙振玉.试论10世纪高昌回鹘王国在中亚历史中的地位[J].西北史地,1990(1).
[14]B. Dodge. The Fihrist of al-Nadim[M]. New York 1970.
[15]张广达.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下)[J].新疆大学学报,1984(2).
[16]陈俊谋.顿莫贺与摩尼教[J].新疆社会科学,1985(6).
[17]F. W. K. Müller,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APAW[M]. 1915.
[18]森安孝夫.ウィグル仏教史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书[J].史学杂志, 1974(4).
[19]杨富学.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铭文初释[C]//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20]努尔兰·肯加哈买提.日月光金钱胡书考[J].中国钱币,2007(1).
[21]杨富学.回鹘“日月光金”钱考释[J].西域研究,1998(1).
[22]林梅村.日月光金与回鹘摩尼教[C]//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3]吉田丰.粟特文考释[C]//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24]王明清.挥尘录·前卷4[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5]A. P. 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C]//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II (1982).1983.
[26]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M]. New York 1925.
[27]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 Русская т
уркестанскаяЭкспединция 1909-1910гг[M]. СПб 1914.
[28]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M]. London 1928.
[29]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M].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1991.
[30]晁华山.初寻高昌摩尼寺的踪迹[J].考古与文物,1993(1).
[31]晁华山.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J].中国文化,1993(1).
[32]贾应逸.新疆吐峪沟石窟佛教壁画泛论[J].佛学研究,1995(4).
[33]柳洪亮.吐鲁番胜金口北区寺院是摩尼寺吗?[C]//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34]Yamabe Nobuyoshi, Practice of Visualization and the Visualization Sūtra: An Examination of Mural Paintings at Toyok, Turfan[J]. Pacific World.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Third Series Number 4, 2002.
[35]侯明明,杨富学.吐峪沟半白半黑人骨像“摩尼教说”驳议[J].吐鲁番学研究,2013(2).
[36]H. J. Klimkeit, 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 [M]. Leiden 1982.
[37]L. Clark, The Turkic Manichaean Literature [C]//P. Mirecki & J. Beduhn (eds.), Emerging from Darkness. Studies in the Recovery of Manichaean Sources, Leiden/New York/Kln 1997.
[38]H.-J. Klimkeit,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nichaean Texts in Turkish [C]//耿世民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