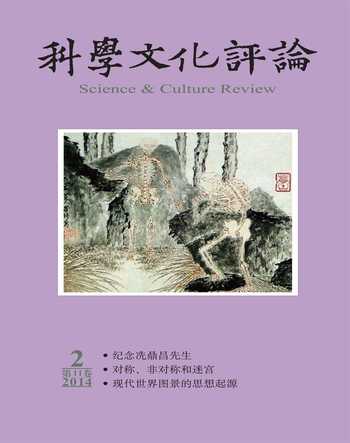革命与星命
陈婷 吕凌峰
摘要:1907年出现的彗星引起了国人关注,正在就清末新政进行论战的革命派和立宪派,巧妙地借助彗星抒发各自的政治主见。1910年,哈雷彗星的回归再次引发双方围绕彗星的交锋。革命派趁机散播彗星谶语,意图制造混乱,立宪派随即回应,但最终未能阻止谣言的愈演愈烈。本文即在晚清西学东渐和清末乱局的时代背景下,分析革命派与立宪派围绕彗星的一次政治交锋,进而探讨西学大量涌入时期,人们依然无法舍弃传统彗星占的原因。
关键词:彗星 灾异 报刊 革命派 立宪派
一、引言
作为异常天象的一种,彗星在星占学中暗示着兵灾、水火、饥荒、疾病,或者重要人物死亡、国家动乱等等。正是由于这种预示灾难的神秘力量,促使彗星在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中产生深刻影响。有些宫廷政变、政治斗争、朝臣攻谮或是民变起义,时常会利用彗星强调其行为合乎天理。
自明末始欧洲天文学传人中国,造成中西两种不同天文体系之间的冲突,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天文观念受西学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对异常天象的认识方面,徐光启、熊明遇转而接受西方对彗星的认识。然而,他们都未能超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徐光台2009,页544-545]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对彗星的认识取得新的进展。牛顿发现彗星循椭圆形轨道运行,他的好友哈雷用之计算,成功预测了1758年哈雷彗星的回归。这些近代彗星知识于19世纪中后期较为广泛地传人中国,多见于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的著作中,如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A.P.Happer)所著的《天文问答》(1849年)、英国传教士合信(B.Hobson)所著的《天文略论》(1849年)、美国教习赫士(w.M.Hayes)编译的《天文揭要》(1849年)、英国人伟烈亚力(A.Wylie)与李善兰合译的《谈天》(1859年)等。这些著作按内容深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有助于开拓普通民众和学生群体的眼界,其中较早介绍近代彗星知识的当属《天文略论》;另一类则充实详尽、专业性相对较强的西方天文学家的著作,最有代表性乃是《谈天》,该书主要供有一定天文或数理基础的人研习,有助于感兴趣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彗星等西方天文学知识。
相较于书籍而言,报刊在普及西方近代彗星知识的过程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19世纪初,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即刊登了《论彗星》一文。19世纪中后期,《遐迩贯珍》、《小孩月报》、《画图新报》、《万国公报》、《益闻录》、《格致汇编》等报刊大量涌现。彗星的基本信息,包括外形、轨道、周期,以及彗星的最新科技资讯,包括预测周期彗星回归、新彗星被发现、彗尾成分研究等等,都经由报刊一一传递给中国读者。加之这些报刊发行量颇大,以《大同报》为例,它自“刊送以来,南北各省,求者踵接,发行已不下七万余纸。”[江苏教育总会请将彗星劝告文送登华字报书1910,页15-16]因而,到19世纪末,近代彗星知识在中国已经得到相当的普及。
早期的报刊多为西方传教士所创办,而他们介绍近代彗星知识实际上是为了与中国的传统彗星观念相对抗。洋务运动开展后,中国人办报传播西学的热情也随之兴起。受教会刊物的影响,国人在介绍彗星科学知识的同时,通常也指出中国传统彗星占的荒谬。有趣的是,20世纪初,国人对于彗星的报道出现了新的趋势。虽然这些报道依然指出彗星与灾异无关,但是其中又掺入了若干政治主见。探寻这一现象的成因则需追溯当时的历史背景。
1890年,西方国家的侵略进入新的高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空前危机。持续的危机促使清末部分官员和社会精英的政见发生转变。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他们逐渐形成两个团体:立宪派和革命派。尽管两派均致力于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但因达成目标的方式不同而成为相互对立的两派。立宪派主张由皇权主导,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政府结构和职能的转变,仿效英国君主立宪制,在现有秩序下建立议会制度。而革命派则主张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日俄战争后,国内要求清政府施行立宪的呼声愈加强烈。面临深刻的统治危机,清政府不得不考虑立宪政体的可能性。1907年初,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立宪派随即积极响应,他们组织宪政筹备会、自治会等团体,为改革举动摇旗呐喊。另一方面,革命派开始加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采用通俗读物或政论文章等形式,向清王朝发起猛烈的舆论攻势。与此同时,双方又各自依托自己的媒介阵地向对方质疑问难,发生了激烈的交锋,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大论战。
当1905年至1907年两派论战正酣之际,丹尼尔彗星造访地球,钦天监占验的结果令清王室颇为恐慌,立宪派立即反驳彗星灾祸说,试图宽慰清政府,督促其继续推动立宪改革,而革命派则趁机暗示彗星灾祸说并未空穴来风。1910年,著名的哈雷彗星回归,革命派再次利用传统彗星观掀起社会恐慌。
二、惊慌与批驳:1907年彗星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丹尼尔彗星(cometC/1907L2)出现,根据各地方志记录[北京天文台编1988,页555],自当年四月持续到九月,在河南、广东、广西、上海、江苏、浙江等南北多省,均可以肉眼观测到此彗星。如此规模的异常天象自然是专司天象的钦天监所观测的重点。负责卜筮的官员经查验后,向清廷递交了占验结果,“彗见度数如以上者,主民讹言、国易政、宫中有乱、奸臣在君侧、兵起”。[陈旭麓等编1979,页65]
几乎与当前统治危机若合符契的彗星占辞,令早已如惊弓之鸟的清廷更加惶恐失措。慈禧太后先是欲下罪己诏,以缓和彗星可能带来的破坏,后“因庆邸之谏而中止”,接着又“拟告祭太庙,退居自省”。与此同时,“传谕军机大臣,谓上天告警,尔等位跻枢垣,皆宜省过自湔,以弭天变,嗣后务宜各发天良,力图振作,保持政体,共济艰难。尤以重公德、绝伪私为要,或可默迓天和,消除渗厉,是则朝廷所昼夜切祷者云云”。[佚名1907a,页1]如此种种,皆为慈禧试图采用躬身自省等方式消弭灾难。
高度紧张的清廷似乎忘记封锁彗星谶语的传播,交游甚广的芦汉铁路行车监督陶湘,暗地得知了此消息,他写信给亲信盛宣怀说:“现在西法畅行,此等谶语均目为迂阔,然何其巧也。圣人有数学,西人亦不敢竞谓数乃必无。然则天垂象而见吉凶,殆非虚语矣”。[陈旭麓等编1979,页65]信中所谓“圣人有数学”即是指利用事物的关联性来推算命理的传统“数术”,其中即包括利用彗星等异常天象占卜或解释人间变乱。这封信的内容或可反映时人对彗星较普遍的认识状态:西方彗星知识在中国广泛普及后,这类有关彗星与灾异的预言被认为是迂腐蒙昧,有识之士多数不再相信,但彗星出现与社会危机的巧遇,似乎又印证了中国传统“数术”思想的合理性。在没办法解释这种巧合的情况下,理性的认识发生动摇,又转向“存疑”的态度,甚至倾向于相信谶纬的某些合理性。
次年,发表在《小说林》杂志上的一篇短文也说明对彗星持有这种微妙心理的绝非陶湘一人。短文云:
彗星见则灾害至,父老恒道之。而方今天文家则不谓然。顷读东京朝日新闻纪亨一则,云,明治五年,彗星见。东京罹地震之灾。明治十五年,彗星见,时疫流行,死者无算。今年彗星见,大水,全国皆被其灾。函馆大火。小樽海啸,所损伤皆不资。天文家不审将何以解此迷信也。[佚名1908,页5-6]
这则短文引用东京朝日新闻的一条纪事,例举了彗星见与灾害至的巧合,反观当时中国水灾、火灾、海啸的出现也恰与彗星巧遇,恐怕天文学家也难以解释这种现象。
尽管如此,西方近代彗星知识在当时毕竟已经“畅行”。1907年,《万国公报》、《画图新报》、《教育世界》等多家报刊都客观报道了此番彗星的出现。有的报纸在阐释彗星的体貌特征和运行规律之后,也加入对彗星谶纬的讨论,如经逻辑分析揭穿彗星主灾异一说的荒唐,“若谓为水火兵灾则谬矣。浅言之,则彗星出现,全球皆见,若能祸人,当全球皆祸。水火兵灾,乃一方之祸,非全球之祸,则彗星之非妖异可知也。”[达生1907,页51-51]或将矛头直接指向持彗星是灾祸之因观念的人,“呜呼,何其愚也!然古代天文学未大昌明,其情形虽可怪,吾亦曾不之怪,独怪乎学术昌明世而仍少所见而多所怪也”[直斋1907,页109-110]。
对于清廷各种试图消弭灾祸的举动,各报刊也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广益丛报》评论道:“噫!政治不亟亟改革,日祷天象无益也。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欲求之天,当必求之民!”[佚名1907a,页1]作者引用《尚书·泰誓》中的话,告诫统治者应把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实际上是要求清政府推动改革,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而不是祈祷于虚无的天象。
《东方杂志》也刊登了一篇长文“论彗星之现无关于灾异”:先是介绍彗星的周期及轨道,力证其可预测性;然后从两个角度论证“彗星之现无关于灾异”,一方面,地球于天空之中,如同“一太仓之稊米”,而地球上某时某地发生的灾异与浩瀚的宇宙相比更是微乎其微,不足为道,因而,将在地球之外运行的彗星归为地球上灾异爆发的诱因自然变得十分可笑,“谓祸将及已,斯其情形之可哂为何如乎!”另一方面,若彗星果真能导致灾祸,那么全球所共见的彗星必然令全球皆罹难,何以此情境并未发生?何况水火刀兵无岁不有,彗星却并非年年都能看见,又怎能将彗星归为水火刀兵的起因呢?最后作者直接揭示彗星灾祸说产生的真相,“夫专制之世,君权无限,若不称天以临之,则将纵其欲而无所不为,故怀忠君爱国之心者,一遇天象有变,谆谆然,即借以为鉴戒”。
这些文字已将彗星灾祸说批驳的淋漓尽致,但这并非作者的最终目的。揭示古代以天象限制君权的实质之后,作者笔锋转向当下的立宪热潮,“今以圣明在上,迭颁明诏,行立宪,则深宫之修省早在于人事之实验,而不在于天象之空虚矣”,无疑是在鼓励清政府继续推动立宪改革。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借用天演论,进一步烘托改革的必要性,“夫国之能自强者,必其民有独立性质,执人定胜天之说,而能争存于天演中者焉。中国当此强邻交迫之秋,而欲发奋自强,惟在振兴国民之志气,使之能自立耳。其忍再以此信天之说挫折之乎?”[佚名1907b,页149-151]此即本文的真实意图,破除彗星谶语,安定人心,为立宪改革能有良好的环境保驾护航。
在诸多讨论彗星的文章中,有一篇标题为“戏拟祭彗星文”的短文显得颇为另类。它发表于当年第27期的《振华五日大事记》,作者署“一旅”,全文如下:
维某某年,岁次某某,七月某某日,某等肃备宝星之冠,谨以七星伴月。向东北方遥祭于彗星君之前,日:窃以祯祥妖孽,无定名也;凶星吉星,无定位也。纣王以甲子亡即武王以甲子与。此方之所谓妖孽,未必非彼方之所谓凶星;此方之所谓凶星,未必非彼方之所谓吉星。咄咄星君,胡为乎来哉?光芒闪闪俨然出一屈头扫把以相向。愁死伯爷婆,吓煞病坏衰君。按《天文良好,形象甚为壮观,它于4月20日过近日点,一个月后过近地点时彗尾长达125度~150度,距离地球只有2500万千米。《琼山县志》描述了其盛况“彗星见于东方,自寅初黎明,从奎宿起,红光甚远,射及牛女之界,彗星之巨莫逾于此”[北京天文台编1988,页558]。
彗星的相继出现引起报刊的广泛关注,所述内容大体相同,无非彗星的相关科学知识,追溯认识彗星的历史,报道彗星出现,西方学者对彗星的观测和研究进展,以及驳斥彗星谶纬的荒诞。其中,1910年的报道多数围绕哈雷彗星,以满足人们对它的认知需要,同时兼具破除迷信的功用。如英人高葆真在《大同报》上连续发表了至少十八篇系列文章“哈雷彗星历届出现之中西事迹考”,系统例举了历史上每次哈雷彗星出现之际,中西所发生的事迹,以此证明彗星实与灾异无关。《广益丛报》则刊登了“美国人避彗星之奇谈”,介绍美国西部的一些居民,因彗星出现而“掘地成坑,以身避入,以为可免彗星撞击之灾者”,并对此评论“不意文明国人,亦竟此谬举,诚可笑矣”[佚名1910a,页13]。
尽管舆论界普遍投入传播彗星的科学知识,但是其中也不乏别样的声音。此即1909年《女报》第5期所刊登的两则彗星短评:
其一:
据中国历史观之,彗星之现也,必有乱事,必有兵革之祸。今中国方有革命之恐慌,而又有彗星之出现,不知兵革之祸之兆彗星来欤?彗星之兆兵革之祸欤?
其二:
彗星,除旧布新之象也。今政府将有改革之风传,彗星之现或即主。然政府之所谓改革者,其果能除旧布新欤?抑或除新布旧欤?是又未可知也。
这两则短评的表达风格和结构一致,先摆出传统观念所认为的彗星是“乱世”、“兵革之祸”的预兆,或是“除旧布新”之像,然后将之与当时中国社会弥漫的革命恐慌以及政府正在推行的改革相联系。这种思路与《戏拟祭彗星文》颇为相似,联系此期报刊的背景,事实上,这两篇短文的确暗藏玄机。
《女报》当年元月才创刊,创办者为陈志群、谢震,二人曾与革命党人秋瑾多有来往,政见亦倾向于革命。这一期更是为纪念秋瑾、徐锡膦等领导的浙皖起义而特设的专辑。作者在此沿用了《戏拟祭彗星文》的思路,明确暗示彗星出现与人间灾异之间的联系。在其他报道都致力于消除彗星的迷信色彩,以稳定社会人心时,称这篇报道动摇人心,也未尝不可。
从《戏拟祭彗星文》到这两则彗星短评,倾向于革命的人士都在暗示彗星与灾异的关系,难道他们真的相信两者之间的联系,亦或是借题发挥,利用传统彗星观与当下时局的吻合来为革命造势?实际上,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已然透露了答案。首先,作者在叙述传统彗星观时,多指出是“按天文志所载”,或“据中国历史观之”,并未表明自身对此观念的认同,也并未肯定的指明彗星与革命的必然联系;其次,彗星的科学知识已经在中国传播了近半个世纪,加之革命派人士多有海外留学背景,受新学影响颇深,亦不可能真的认同彗星谶纬。革命派主张暴力革命,因此便有必要摧毁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破除民众对其权威的崇拜,进而煽动起民众革命的热情。为达此目的,他们甚至不惜借助古老的彗星谶纬的力量,尽管他们实际上未必相信它。
立宪派在这两年活动频繁,在全国掀起立宪请愿高潮,促使清政府在各省成立咨议局,并于1909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相对地,革命派的活动陷入低谷,发动的若干次起义多以失败告终。为尽可能广泛的扩大影响范围,革命派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制造言论,连番出现的彗星自然成为绝佳的素材,尤其是备受瞩目的哈雷彗星,直接被革命党人巧妙地编成了通俗易懂的彗星谣言。较早的谣言版本是“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即是说彗星此番出现预示着宣统的统治行将末路。革命党人景梅九在其回忆录中清晰的记录这一谶语的由来:
一日从友人张翊初家与诸同志畅谈晚归,我和仲虑路过南城门边,遇卖浆者。两人停止住,喝了两碗浆,仲虑忽然仰望天上彗星,东西辉耀,随即遣了两句谣言道:“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我附和起来,说:“这个童谣相传好久,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卖浆者很妙,便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清家快亡了!明朝不过:百几十年,清朝也差不多:百多年了,还不亡么?”我和道:“原来如此!”最妙是警察先生站在旁边,也说7两句赞叹的话。我却拉仲伏回寓,在路上很觉得有趣。过了两天,同志邹子良、李仲山等都来说:“外边流传一种谣言,很利害!甚幺‘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人心大摇动起!”我和仲伏只是暗笑,却装着不晓得的样子来道:“没听人说呀!”他们说得很有兴趣。又添了些:“明年猪吃羊,后年种地不纳粮”的谣言,那却不知是谁造出来的了?后来又改成“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这话更为传的远哪。[景梅九1981,页75-76]
景梅九的这段趣闻,还原了彗星谣言产生的真相,他还就此谣言作诗一首:。举首望长天,光芒射半边。彗星十万丈,宣统两三年。百姓方呼痛,官家正敛钱。也知胡运毕,何处不骚然?”
这些谣言简单明了,韵律干脆,令人过耳不忘,巧妙地利用了普通百姓所熟知的中国传统彗星观,连目不识丁的卖浆者不费思量即知其意,谣言不胫而走,致使“人心大摇动起”。虽然谣言并不能直接撼动统治者的地位,也未必能鼓励民众参与革命,但是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民众的心理,接二连三的天示征兆促使人们对统治者的信心进一步丧失。
谣言的疯传绝非致力于立宪改革的人士所希望看到的场面。他们一方面须要敦促清政府加快改革步伐,另一方面又须要为改革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倘若民众已然丧失对政府的信心,一心想推翻它,那么立宪运动注定是要失败的。
针对社会中流传的彗星谣言,立宪派的喉舌刊物《国风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哈雷彗星谈”的文章。此文开篇即交代了中西迷信彗星的渊源和历史,然而西方在牛顿力学诞生后,对彗星的运行轨道和回归周期有了新的认识。文中附有多张彗星图,并分别以中西历列出哈雷彗星历次出现时间表。文末点出:
迷信之陋习,除之非易也,窃尝论之,凡在专制之国,其国中无时不含有酿乱之种子。水旱疾疲刀兵无岁无之,其在不遇彗之年则置之不论,一旦遇慧则以为彗实使然。苟欲附会,固可以无所往而不合也?而桀黠之夫,好乱之民又往往利用愚民之迷信,借此以助其篝火狐鸣之势,而威其斩木揭竿之机。于是而彗星可以召乱矣。吾之草此文,岂徒以资谈助,亦愿当道者观此中消息而知所警耳![艺衡1910,页63]
作者在这里交代了写作此文的目的,不是“徒以资谈助”,而是告诫统治者,彗星谣言的出现不是偶然。“凡在专制之国,其国中无时不含有酿乱之种子”,彗星亦是酿造混乱的一个种子,以此敦促当朝及时改变专制,推行立宪政治。另一方面,作者也分析了谣言背后的动机,即“桀黠之夫,好乱之民又往往利用愚民之迷信,借此以助其篝火狐鸣之势,而成其斩木揭竿之机”,指出彗星已经成为革命派利用的工具,以达到“召乱”的目的。此文先是突出彗星的客观性,又指出彗星谣言并非空穴来风,而系革命派编造以蛊惑人心,实际上都是在宽慰清廷及民众勿被谣言所困扰,同时也是为督促清廷尽快施行立宪改革。
同年,《东方杂志》发表了叶青所著“记哈雷彗星之历史”一文,介绍了从汉成帝元延元年到清宣统二年历次哈雷彗星回归的情况。文后有附录两则,第一则“宝乐安彗星真说”,先是指出天文学家早在半年前便借助望远镜观测到哈雷彗星,经对其运行速率作了推算后,预测了本次哈雷彗星的回归。至于和彗星有关的谣言,乃是“今中国民智未开,诚恐好事之徒,遇事生风,藉此彗星捏造谣言,以致酿成事端。聪明爱国之士,固不屑为此,然人心不同,如其面然。今为杜渐防微起见,故特著此论,解明彗星实理,盼望阅者心中清晰,不再为无稽浮言所煽惑云”。[佚名1910b,页25-32]此文旨趣与“哈雷彗星谈”大同小异,均指出彗星谣言是“好事之徒,遇事生风”。第二则为传教士高保真所著“彗星无害说”,力辟哈雷彗星的谣言。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热衷于立宪运动,不赞成用激烈的革命手段去改变现状”[方汉奇2007,页297],所刊言论大多倾向于改良、立宪。以上文章亦可以代表立宪派人士对彗星谣言的普遍看法。
四、讨论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诸多西方科学知识和观念已经在中国进行了近三个世纪的普及与传播,甚或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国内已然“科学昌明”。恰好,1907年到1910年出现的彗星,提供了检验西学传播效果的试金石。国中一些已经接触并了解彗星科学知识的官员或知识分子,面对彗星谶纬与现实极其吻合而无法做出解释时,认知发生动摇,又转而认同中国传统占卜之术。与此同时,西学的传播者将传统星命观排除在外,而其所宣扬的西方彗星知识,违背了中国民众深信不疑的观点,多数人即使面对科学事实,仍旧极不情愿改变自己的观念。即便当时报刊上充斥着对彗星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对迷信彗星谶纬的批判,但实际上传统的星命观并未销声匿迹,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依然深深地植根于广大人民的观念中。
于是,革命派趁机利用彗星谶纬蛊惑人心,制造谣言。革命党人的小把戏如他们所愿,收获了剧烈的反响,不仅仅使得立宪派措手不及,制造谣言的人也始料未及。类似于“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的谣言,如果没有民众的心理认同,荒诞的谣言难以闹得满城风雨,人心大动。如此观之,传统星命观在此时期的中国仍然有一定社会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西学知识已逐渐普及到大众阶层,西方的彗星知识也被视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现象。在我们今天看来,彗星不过是沿着既定轨道运行的“脏雪球”,它的出现会导致灾祸的占言更是荒诞不经。清末彗星谣言致使人心大动一事似乎不会再继续上演,然而,前年世界末日的谣言又说明了即使是进入文明时代,人类依然走不出这种思维的怪圈。最直接也最容易理解的解释是人类内心深处对未知以及不可控的事物存在很深的恐惧感,“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促使其作出相应的行动。加之对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民众渴望封建社会的彻底崩溃瓦解。当彗星谶言出现,民众的这种期望被投射其中,晚清剑拔弩张的气氛更是强化和感染了民众,他们愈加笃信“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的谣言,于是几乎每个人都不自觉的成为宣传谣言的主体。
当彗星划破人类头顶宁静的夜空时,恰逢清末社会的危机和政局的动乱。只是寻常天象的彗星,却在中国引发了社会骚动并卷入了两种民主力量的交锋。利用天象作为斗争的工具或为政治目的服务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如汉成帝时期丞相翟方进竟为搪塞“荧惑守心”的灾异天象而被逼自杀,成为其政敌利用天象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黄一农2004]而清末这次立宪派与革命派利用彗星来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因此而发生的交锋,只不过是历史上这种斗争的重演。天上的星象变化与人间秩序的安排被再一次联系起来,星命与革命的观念紧密交织。发生在西方天文科学知识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的20世纪之初的彗星事件,与两千多年前汉朝的翟方进事件有类似之处,令今人玩味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