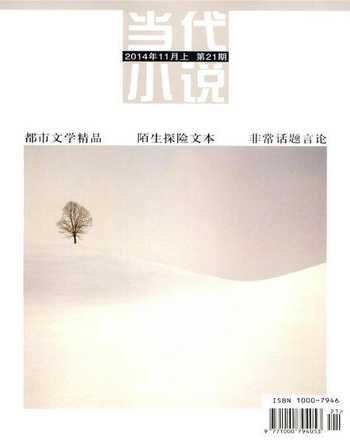希望的田野
汤成难
1
贵喜躺在床上第四天,村头的瘸四来了,在门外敲了一阵,没见动静,曲下瘸腿从狗洞爬过去了,进屋见顶棚漏下的光柱正打在老贵喜睁着的眼睛上,才抖嗦了瘪唇说起话来。瘸四说,还以为你死了呢。
瘸四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咕咕咚咚喝了,又舀一碗放在贵喜床边。瘸四说,庄上人都以为你死屋里了。停了一阵,又说,也真是的,一头死牛——瘸四说完把窗扇推开,把碍脚的东西踢到一边,然后又从狗洞爬出去。
瘸四走后,贵喜起来了,将那碗水喝个精光,浑身方才有了丝力气,他打开门,先用鼻子嗅了嗅,再迈出脚去。空气里干干净净的,除了冬天的干草味儿什么都没有,不像那几天,即使关上门,堵上窗,肉味儿直往屋里钻。贵喜在门边坐下,蜷了腿,身体缩着,这就看见脚旁有一碗肉。他猛地站起来,抬起脚,将碗踢翻了,白瓷碗悠悠荡荡在地上滚了一圈,把黑乎乎的肉块和汤汁涂了一地。贵喜傻愣了,然后哇地哭出来,他张大着嘴,大概过于悲愤或伤心,竟没有发出声音,哭了一阵,又蹲下去,把肉块小心捡起来,一块一块的,在碗里仔细放好。拿上锹,在牛棚下将肉连碗一同埋了。
埋了肉,在微微凸起的“坟”边坐下,转脸看见牛棚下的食槽,眼泪又婆娑了,他把食槽挪过来,一直挪到身边。食槽空的,觉得自己的心里也是空荡的,他说,牛死了呢——他对食槽说,食槽朝他张着大嘴。我的牛死了呢。他又说道,食槽沉默着,他絮絮叨叨说了很久,从来都没有这么的想说话似的,说着他死去的牛,说着过去的那么多年年岁岁,他抱着食槽,把头俯下来,好像要把肚子里的话一点不剩地倒进食槽。
2
老贵喜还是小贵喜的时候,就一个人过日子了,那时也不过五六岁,住在小王庄东边河岸上的土坯房子里。他的母亲早死了,生下他没来得及看一眼就咽气了,他的父亲老恩民在庄上一个叫朱伯富的人家干活,给二十几匹马和十来头牛喂料。晚上老恩民就挤在这些牛马之间,半夜再悄悄爬起来,把白天塞衣兜里的馒头或烧饼带回去。他坐在床边唤小贵喜,唤不醒的时候就把馒头或烧饼递到他嘴边,小贵喜竟也张开嘴,笑得咧着嘴吃个精光。第二天醒来时,父亲已经走了,只有齿缝里还留了一些残物。他用指头小心抠出来,还能辨得出是烧饼还是馒头,要是齿缝里什么都没留下,不知道吃下的是什么,只有肚子鼓囊囊的,就会懊恼起来,恨自己睡得太沉。
朱伯富朱老爷的家小贵喜也去过,七岁时,被老恩民牵在身后穿过朱家一进又一进的院子,一直来到父亲的牛棚。那一天小贵喜跟着父亲在朱家走进走出,吃了两个油饼,在草堆上睡了一觉,还看了一头母牛产小牛——朱家的几个佣人都来了,围着母牛站了一圈,小贵喜蹲在他们的身后。天黑时,小牛生下来了,也是一头毛色纯正的黑牛,睁着眼睛懵懂地看,小贵喜觉得那双眼睛是看着他的,他向它招手,它还是一眨不眨地看着,然后突然站起来向人群蹒跚走来,刚走几步摔倒了,被两个佣人抱到母牛怀里。这时小贵喜看见母牛的嘴边放了一个食槽,很漂亮,食槽底部箍了一圈铜皮。
没几天那头小牛就被抱到小贵喜的土坯房子里了。他的父亲老恩民死了,说是马棚的顶突然掉下来,砸死了。后来某一年小贵喜去过朱老爷家,特意去看了一下马棚,那个顶一直没修,漏出很大一个洞,他仰着脑袋看着那里,从洞里可以看见外面的天空,他觉得父亲好像是从那个洞里一跃,跃到天上去了。
送牛的人走后,小贵喜没有哭,而是把牛抱在怀里,抱了一会儿,突然对小牛说,我给你取个名字吧,以后就叫恩民吧。
后来,小贵喜发现恩民原来是个跛子,它的一条腿比另外三条腿细得多,走路时一崴一崴的,随时都像要磕下去。小贵喜抚着恩民的细腿说,没事的,你是跛子我也要好好待你的——
白天恩民被小贵喜带到村北的土坡上吃草,恩民走得慢,小贵喜不催,也慢悠悠地牵着。晚上他让恩民睡在自己的床板下,夜里听恩民呼哧呼哧地反刍,小贵喜睡不着,就把身子探下来,黑暗里抚摩着恩民的背。远处有人在拉二胡,悠悠荡荡地一直传到河的南岸,小王庄的瞎子又在唱歌了:大路弯弯啊一条龙,一家富裕啊九家穷。穷人半夜就起身,谁人睡到太阳红……小贵喜闭上眼睛仔细听着,这就想起了父亲,泪水从闭着的眼缝里往外流,止都止不住,于是把手又伸下去,一寸一寸地抚着恩民的背。突然有一天,贵喜感到身下的床板被恩民顶了一下,这才发现恩民已经长成大牛了。
长成大牛的恩民个头已经超过贵喜了,走路仍然一崴一崴的,但走得很快,走得快的时候,恩民就停下来等一等贵喜。他们从村北的土坡换到南面的河岸,又从南面的河岸转到西边的大堤上,贵喜好像要让恩民把村里每个地方走个遍。一次他牵着恩民经过打谷场时,发现聚了很多人,人群里有人说,贵喜你把牛牵来干什么,正开大会呢。于是贵喜就把恩民拴在旁边的榆树上,他也随着人群向台上看,竟看见了朱伯富朱老爷。不过朱老爷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太师椅上,而是被反绑在一张板凳上。说朱伯富绑在板凳上,倒不如说板凳被绑在他的背上,直杵杵的,好像是背上长出的一个犄角,这就使得朱伯富十分怪异了。
台上的人用桑树枝条抽了朱伯富,每抽一次,台下的人就振臂高呼,他们异口同声地喊着,打倒地主朱伯富!打倒地主朱伯富——贵喜不知道怎么就打倒朱伯富了?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跟着一起喊,他想到自己的父亲就是死在朱家的,心里十分悲愤,可刚要举臂,又看到恩民正在远处看着他。贵喜放下手臂,傻愣愣地站着,站了很久,被人群推来搡去,人群后来又调转方向,像水一样地涌向朱家。贵喜也跟着去了,他看见好多人砸着朱家的门和窗户,好像那些门窗是他们的仇人,贵喜不知道小王庄的人什么时候跟朱伯富有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朱家的东西往外搬,有人扛起一张榆木板凳走了,也有人揣了一把光绪年间的菜刀,贵喜什么也不想拿,却想起那年跟父亲来朱家的情景,好像都过去很多年似的。
他又穿过一进一进的院子,一直走到父亲的马棚,那些牛马都不见了,只剩下空荡荡的院子,有人冲过来,点着火把,又涌来很多人,用斧头朝马棚砍,砍断了柱子和马槽,正要敲碎一个铜皮紧箍的食槽时,被贵喜一把抱着了。后来,这个食槽就被贵喜带回了家。
贵喜在河里把食槽洗得干干净净,又用稻草将铜皮擦亮,他把食槽放到恩民跟前,说,还记得这个吧。恩民正低着头,抬眼瞥了一下又转过去。贵喜就往食槽里倒了一些青草,见恩民转过脸来,方才乐了,他一边看着恩民一边用手在它背上搓着。
没几天,贵喜分得一块地,地主朱伯富的。分到地的那天,贵喜把恩民带过去,在南坝上,地有七分,呈三角形。贵喜沿着地垄走了一圈,又牵着恩民走了一圈。地里正长着苜蓿,一尺来高,风一吹,起起伏伏的。贵喜的脚有些痒了,脱了鞋走进地里,土松软得很,从脚丫里绵绵地往上挤。贵喜又觉得身上痒了,便脱了褂子躺下来。这一晚,贵喜没回去,和恩民躺在苜蓿上一直到天亮。
贵喜在林子里相中一棵弯度合适的桑树,砍下来修成一架犁,又用一箩山芋换了个锈了的犁头,磨了两日才见白亮。贵喜把恩民牵进地里,架上犁,吆了一声,恩民就乖顺往前走了。地被翻开了,像水波一样向前涌动着,露出一片新绿。傍晚的时候,天边红彤彤的,小王庄瞎子的歌声从远处飘来:栀子花儿啊两头黄,油灿灿的肥肉把它尝,白天不再喝他稀汤粥,晚上不再睡他牛圈房……
很多年后,贵喜总是会想起这一天,想起这一天远处的火烧云映在恩民眼里的辉煌,想起白杨树伸向天空干净而明亮的树枝,想起连绵的大堤和大堤下他的七分地……
3
秋天的时候,贵喜在地里播了麦子,来年春上,麦苗拔节了,麦子磨出的面粉可以吃上大半年。割了麦子,再种上水稻,秋天的时候,又能吃上新米。但这一年,地里成熟的稻谷没有走向贵喜的粮仓,它们都去了“公社”,贵喜的七分地也归了公社,小王庄的人纷纷把灶都砸了,腾起的尘烟几天都没有落下,柴火稻草抱出来了,铁锅送到了炼钢厂,广播里有人大声播报:吃食堂了,今后吃饭不要钱了——
小王庄的人很久没有听到瞎子唱歌了,他的声音淹没在村头的广播里。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从广播里传出来,这些消息让小王庄的人振奋不已,炼钢的煤炭没有了,小王庄的人就把家前屋后的树伐倒抬过去;第一块钢铁快要炼出来了,需要大家敲锣鼓气,拿出家中能敲得响的铜盆、钢锅、甚至是锹头,贵喜也想把食槽拿出来,那个底部被铜皮裹着的地方应该也能发出声音。他摸了摸铜皮,还是将它悄悄藏了起来。整个小王庄沸腾了,各种铁器发出的声音尖锐刺耳,半天工夫,这些发出响声的铁器就被送进了炼炉里。
恩民也划到了公社,白天在公家的地里一遍遍地犁着,晚上就住在村委会隔壁的牛棚里。农闲时候,小王庄的人在南坝挖河修渠,下工了,贵喜就去看看恩民,抱一捆草,看恩民呼哧呼哧地嚼着。有时贵喜也把恩民牵到南坝的七分地,地里已经不再种水稻麦子,种上了公家的山芋,山芋的茎叶是褐红的,矮趴趴地伏在陇上。贵喜就坐在田埂上傻傻地看,看累了就躺下来,躺得久了再绕着七分地走一圈。
又过几年,七分地里的山芋也没有了,上一年撒下的稻种被人偷偷刨掉了,大堤下连绵的田野寸草不生,槐树榆树的枝头一整年都见不到绿色,路上走动的人少了,省着力气躺在屋里,广播也停歇了好多天,只有瞎子还断断续续地在唱:通洋河的水哎底朝天,小王庄哎遇灾年……那些听着瞎子唱歌的人,实在想不通这广袤无边的大地上竟刨不出吃的,他们一边想着一边走着,尔后,头一歪就倒下了。也有人爬上屋顶,把烟囱上积了多年的锅灰刮下来,黑色的锅灰让他们想起那些年烧煮的食物,于是一遍遍嗅着。吞下的锅灰使肚子涨起来,涨得走不动了,便坐在屋顶看着光秃秃的小王庄,看着头顶的太阳比任何一年都肿胀了似的。
公社的几头耕牛也宰吃了,只剩下恩民瘦得躺在牛棚里,贵喜不知从哪儿找到的干草,隔天就送来,他躺在恩民身旁,看恩民的骨头像要把皮刺穿似的。
冬天到来的时候,有人打起了恩民的主意,他们在二更夜钻进了牛棚,在恩民已干枯的腿上剐走了一块皮。第二天,偷牛肉的人被抓起来,绑在学校的旗杆上,脱了衣服用鞭抽,半个小王庄的人都来看这个“破坏生产力”的坏分子。教育过后,偷肉人放了,隔天,再被抓起来——太饿了,又偷。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那头跛牛不见了,牛棚里干干净净的,有人说是牛成了仙,驾朵云飞走了,也有人说牛被贵喜藏起来了。后一种说法的人拍着胸脯,称自己夜里起来撒尿看见的,贵喜扛着一头牛穿过了小王庄——
可是,一些日子之后,连说这话的人都感到怀疑了,他想那一晚自己是不是睡得迷糊了,还有,即使再瘦的牛,一个人怎么能扛得动呢。
然而小王庄的人已经不再谈论这些了,他们不愿把力气花费在这些不能填饱肚皮的事情上。每天都有饿死的人,用席子裹了扔在通洋河的堤坝上。春天的风已经吹来了,依旧没有改变小王庄褐红的土地,绿色逃走了,好像忘了回到大地了。
整整三年的时间,那些熬过来的人终于在这一年的春上看见了绿色——毛针草冒出来了,蒲公英冒出来了,巴泥草也从地下冒出来了,他们这才知道绿色原来是跑到地下去了,跑反了方向,跑得太深太深,跑了三年才找到回来的路。
4
堤岸上的垂柳又蹿出一人高的时候,贵喜和他的牛回来了,那天小王庄的人正在地里上工——收割大片的油菜,起先看到他们的是一个孩子,然后小王庄的人都往路上看过来,他们从那头牛的走路姿势判定它就是那头跛牛。
贵喜的土坯房子被雨水冲塌了,他在原先的七分地旁搭了两间草棚,碎石块垒的墙,芦苇盖的顶,贵喜每天牵着恩民在七分地周围转一圈,然后穿过小王庄的泥土路去北村吃草,人们不知道过去的那些灾年他们是怎么度过的。牛壮了,倒是贵喜,而立之年却腰弓背驼,有人说是背牛的那次落下的——说是贵喜背着他的牛一直往北走,一直背到牛恢复了精神气儿,他牵着恩民仍然向北,走到没有人烟了,走到水草充沛了。这个说法在小王庄逐渐散播开来后,甚至有人从家里翻出一张破旧的地图,查看并揣摩,他们的手指沿着弯弯曲曲的线条向北移动,然后又蓦地停下,若有所思地说道,贵喜怕是到国外去过了——
这一年,贵喜和他的牛在草棚里只呆到冬天,初雪覆盖时被带走了,恩民又归了公社,贵喜被关进学校废弃的一间屋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是瞎子,白天挂上“反革命”的牌子,押到各个村庄去游行批斗——他们的棉衣被铁叉撕开,带着冰冻的鞭子抽在身上。晚上又被赶到地里散大粪,瞎子看不见,背着粪筐跟在后面,两个人摇摇晃晃地走一段路,尔后都倒在田埂上了。贵喜把四肢摊平,整个人都贴着地面,由于寒冷,泥土都冻得硬邦邦的,像无数紧握的拳头。大地正在聚集能量。他想起自己的七分地,想起分得地的那一天,贵喜想不通那块地怎么又不归自己了呢?
后半夜时,露水渐重,打湿了衣衫,瞎子醒过来了,看看头顶寥落星空,突然唱起歌,瞎子的声音在田野上凄凄厉厉,瞎子唱道:万里西风啊鸟花香,鸣泉落水啊各登场。老牛还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贵喜转过脸看瞎子,月光下瞎子脸上泪潸潸的。
天亮时,瞎子死了,被人用草帘匆匆卷走了。
几年后,贵喜平反,又住进了草棚,恩民属公社的,住在原先的牛棚里。恩民老了,连草都吃不动了,但还是得赶到地里,架上犁,鞭子吆喝着。赶牛的人不再是贵喜,贵喜站在田边看,心里疼,晚上就抱着一大捆青草去看恩民。一天恩民犁地,突然跪了下去。赶牛的人给了几鞭,恩民方从沼地里站起来,刚走几步,又猛地一磕,这一次,恩民没有站起来。赶牛人喊来几个壮汉,合力抬,起来了,恩民继续往前犁,犁到田头,便一头栽下去了。
恩民死了,贵喜哭得十分伤心。小王庄的人说他的爹死了也没见这样哭过。
恩民也被抬走了,不是抬到通洋河的堤坝上,而是抬到了公社食堂。贵喜拿了把刀冲进来,说谁敢杀牛就和谁拼。有人说,贵喜你别胡闹,牛是公社的,再说,我们不是杀牛,牛自己死了。贵喜听不进去,情绪激动,将刀挥舞起来,然后架在自己脖子上。又有人说,贵喜你记不记得几年前你把公社的牛偷走的事了,上面还要治你罪呢——那把刀没有要了贵喜的命,也没有要了别人的命。贵喜被关起来了,绑在一根水泥柱上,两天后才放下来,放下来的时候整个小王庄正飘荡着牛肉的味儿,细细密密的,四处钻着。有人以为贵喜会闹到食堂,放他下来的人说,贵喜一下子傻掉了似的,也不说话,木呆呆的,朝他的屋子走。
5
第二年,在贵喜埋肉的地方竟长出一簇牛脚印草。这草小王庄的北坡到处都是,北坡是放牛的地方,地上坑坑洼洼的牛脚印,脚印低凹,容易蓄水,草最喜牛脚印。贵喜把牛食槽拿出来,将恩民坟上的牛脚印草小心移植进去。
七分地四周也长满了牛脚印草,高高矮矮地围了一圈,每棵草都长在低凹的牛脚印里,一个牛脚印就是一片春天。
春分过后,七分地里点上了棒豆,尖尖的绿芽戳上了地面,夏天过后,棒豆胡子红了,生产队的妇女们走下地里。棒豆秆儿高高的,没了她们的头顶,长长的叶儿就像无数的手臂。这些经历过灾年的妇女们,对粮食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她们一点一点地向前移,不放过每一株秆儿。突然,其中一个尖叫起来,她的尖叫里没有恐惧,而是一种欣喜,所有的人都以为掰到大个儿的了,有人向这边看过来,也有人直接跑来看个稀奇。她们看见这个尖叫的女人弯下腰去,双手沿着棒豆秆下移,小心地,再轻轻托起——女人抱起的不是一个棒豆,而是一个包裹得像棒豆似的奶娃。
这件事很快使小王庄沸腾起来,那个最先发现的女人把这个奶娃像上交棒豆一样交给了公社,公社的几名干部研究了半天,又将这奶娃送到贵喜的草棚里——他们认为没有人比他更合适的了。
小王庄的人这时才发现光棍贵喜已近不惑了。贵喜想给奶娃取个名字,公社的干部说不用了,这孩子叫国庆,贴身小袄上写着呢——贵喜点点头,说国庆好,国庆好。
贵喜上工的时候把国庆带着,国庆睡在小竹匾里,竹匾搁在田头。贵喜一会儿来看一眼,把个尿,喂点米糊。国庆不哭闹,睡醒了小眼睛愣愣地瞪着天空。再大一点的时候,国庆会翻身了,趴在竹匾里看着地里的人,要是贵喜朝他挥手,国庆就咧开没牙的嘴嘿嘿笑。一天,贵喜正在挖地,往后退着退着,突然踢翻一个东西,转身一看,原来是国庆,国庆竟然爬到脚下来了。贵喜把泥猴儿似的国庆抱在怀里,心里又疼又喜。
国庆到了学龄的时候,小王庄发生了一件大事,当然这事并不止发生在小王庄,广播里说,全国各地都在搞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新名词小王庄的人不太明白,但他们知道那些土地又要回到自己的身边了。
以抓阄方式分田到户,按人口,贵喜分得村北一亩九分地,那块地水土肥沃,尽管如此,贵喜还是用其中一块调换了门前的七分地。晚上,贵喜光脚在地里走着,走完又拉着国庆走着,这使他想起很多年前带着恩民绕着七分地的情景。贵喜说,国庆哎,这是我们的地了呢。国庆点点头说是的。贵喜说,国庆哎,你说我们往地里种点啥呢?国庆想了想,说种棒豆吧。贵喜呵呵笑了,说全部种棒豆。
爷儿俩并肩在田埂上坐下,远处大堤起伏,西山太阳将两个人影儿拉出老长。贵喜揪一把青草在手里绞着,绞完又在鼻下闻闻,他想起小王庄的瞎子了,还有瞎子唱过的那些调调——栀子花儿啊两头黄——贵喜转身对国庆说,国庆哎,给爸唱一个歌唻。国庆说唱一个刚学的吧,说完晃起脑袋: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贵喜突然打断国庆,问,是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国庆说是的,一片冬麦,一片高粱。贵喜点点头,脑袋也跟着晃起来,好像眼前正是那大片的冬麦和高粱地。国庆继续唱: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劳作……
太阳逐渐隐没了,白雾从四周升起,国庆的歌声飘荡在小王庄的上空,歌声之外,万物寂静。
第二天,贵喜有了个决定,他想买一头牛。贵喜先是去了趟集市,在一群毛色不错的小牛犊中看了很久,有的胸部宽深,有的肩峰高大,这都是长大后能成为不错的耕牛。突然,贵喜看见一头小黑牛缩在后面,身子瘦小,眼神怯怯的,再仔细看,竟是个跛子。贵喜心里一紧,想起恩民来了。他在牛群里看了一阵,在那头小黑牛身上摸了又摸,结果还是空着手回来了。夜里,贵喜睡不着,想恩民,想那小黑牛的眼神,天刚亮,贵喜就起身了,急急忙忙往集市赶,卖牛的还没来,牲畜交易市场空荡荡的,贵喜突然有些担心,担心过后又开始懊悔。好大一会儿工夫,白雾渐渐散了,牛群才从远处缓缓走来,贵喜一眼就看见走在最后的小黑牛了。
小黑牛被贵喜牵到了小王庄。国庆放学后就去放牛,小王庄的北坡,河的南岸,以及地头的水渠里,哪里的毛针草长出来了,哪里的苜蓿草最旺,国庆比谁都清楚。来年春上的时候,小黑牛已经长成大黑牛了,国庆骑在牛背上,嘴里背诵着刚学会的古诗,古诗里说“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国庆就想,要是他也有一支笛就好了。没有笛子的国庆就唱歌,他的歌声十分清脆辽远,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飘荡着,正在干活的小王庄人们,听到这样的歌声就会若有所思地看看远方,他们想起了很多年前的瞎子,于是一些在路上碰见贵喜的人,总是上前夸赞一句,他们对贵喜说,你家国庆灵光着呢——
灵光的国庆决定自己做一支笛子,他在通洋河闸的边上发现了一小片竹林,竹子细细的,做笛子刚好。国庆把黑牛拴在栅栏上,自己从上面攀过去。国庆一根竹子一根竹子地看着,他要挑一根光滑匀称的竹竿,他的专注使他忘了脚下的虚空——国庆跌进了水闸。这一天,小王庄极其安静,整整一个下午,人们都没有听到国庆清越悠扬的歌声,当人们找到国庆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了,小王庄的人把国庆捞上来,衣服被涨开的身子撑得紧紧的,有人说,跟当年捡到时一样,像一个大棒豆儿。国庆的黑牛还拴在铁栏杆上,系着牛绳的铁条已经被拽弯了,这时有人才回忆起刚刚过去的这一天,他们说隐约听见了牛无休无止的嘶鸣。
贵喜两天都没有说话,整个人傻傻的,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去了牛棚,牛棚里黑乎乎的,没有点灯,黑牛一动不动地站着,鼻子里偶尔发出呵哧的呼气声,贵喜把手伸过去,在黑牛脸上抚摩起来。他想对黑牛说句话,可舌头僵在嘴里,半晌,贵喜才说,又剩下我们了——
贵喜躺在黑牛身边,黑牛呼出的气间隔就喷在他的脸上,那种夹杂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贵喜说,国庆走了呢。说完转过脸去看黑牛,他仿佛看见黑暗中黑牛悲伤的眼睛,过了好久,贵喜才说,以后,你就叫国庆吧——
6
这一年夏天,小王庄发生了一次洪水,通扬运河的堤坝在一次暴雨后决开了,浑黄的河水奔泻出来,好像被阻拦得太久,洪水长了腿脚似的日夜奔流,奔向村庄,奔向田野,它们像是对小王庄充满了好奇,每一处角落都不落下,卷走了衣被,卷走了房梁,然后又匆匆奔向北方。小王庄的树倒了,猪圈鸡圈也倒了,人们纷纷跑向高地,带着他们赖以活着的粮食坐上屋顶。贵喜把国庆赶上一个土梁,国庆背上驮着面粉和大米。洪水没有消停的意思,水面越来越高,有人担心这样下去梁柱将要烂去,房屋将会倒塌。水已经跑到国庆的肚皮了,水蝇和水蜈蚣在它身上跳来跳去。国庆一动也不动,像长在土梁上似的。整整两天,洪水像是玩够了,才逐渐退回,国庆背上的面粉被取下来时,国庆累倒在了地上。
粮食冲走了,很多稻子经水浸泡后长出了嫩芽。小王庄的人又纷纷走下地里,重新开始耕作。秋天的时候,小王庄来了一辆机器,一些见过世面的人说,这叫手扶拖拉机。他们发现这个机器不光可以代替独轮车运送稻草,还可以耕地——把手扶拖拉机的头部卸开,装上犁头,它就突突突地在地里犁开了。
贵喜牵着国庆也过来看,他搞不懂这个家伙怎么造出来的,长得一点也不像牛,倒像个脾气暴躁的怪物,它朝着天上吐着黑烟,突突叫着,把地撕扯得稀烂。贵喜看不下去,牵着国庆默默走开了。
往后的日子,小王庄的人不再找贵喜耕地了,他们更喜欢把那个怪物请到地里,怪物耕地很快——人们多喜欢“快”啊,快快耕地,快快播种,快快收割,快快碾出面粉,再快快吃到嘴里——
那些原先拥有耕牛的人们,也纷纷把牛卖了,换上了怪物。小王庄只剩下国庆一头耕牛了,贵喜放牛到北坡,站在北坡上朝田野里看,四五个怪物在地里跑动着,它们不像是耕地,倒像是咆哮,将地撕开一道道生疼的口子。
不需要耕地的贵喜就只给自己耕地,他把国庆牵到七分地里。一夜的露水,泥土湿润而黝黑。贵喜给国庆套上牛梭头,枣木的,再架好犁, “哒——”的一声,长长的,刺破早晨的寂静。六只脚在地里一点点地走着,他喜欢这样一寸一寸踩过去的踏实,犁出的新土是温热的,像是带着大地深处的体温。贵喜看过怪物耕地,操作怪物的人坐在后面的座椅上,腿脚高高悬着,他想,这叫什么耕地呢。
又过了些年头,小王庄来了一些更大的怪物,它们把地里那些原本属于人们干的活都抢走干了,这些铁的家伙有的会犁地,有的会收割,有的还会脱粒,那些麦穗已经不需要从人们手里一一经过了,当黄灿灿的麦粒儿堆成山的时候,总让人感到极不真实。
这一年冬天,小王庄下了一场大雪,和这场雪一起到来的是一支石油开采队,四辆装载着工人和各种机具的卡车,从小王庄的西头浩浩荡荡驶进来,白色的雪地上,车轮碾下的轱辘印,如同两道铁轨似的,一直延伸到村北的庄稼地。小王庄的人跑去看了,他们不明白这些铁家伙是干什么的。车上的人把机具卸下来,一件件地砸在雪地里。有人上前问,回说是采油的。再问这油能喝么?说是能呢,专门给机器喝的。小王庄的人纳闷了,他们不知道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庄底下竟然还能冒出油。
一些麦地让出来了,平坦而广袤的大地架上了很多宛若铁公鸡样的怪物,没几天工夫,怪物就一磕一磕地干起活来。小王庄的人下地的时候,怪物在干活,小王庄的人从地里回来,它还在磕着。日日夜夜地一刻不停,像是要把地底下的东西刨尽一样。贵喜放牛经过的时候,会在旁边看上一阵,脚下的土地好像在震颤,在抖嗦。要掏空了吧——贵喜想,想着便把脚挪开,他感到脚下一点点地正在虚空,正在下沉,他拍拍国庆,然后赶紧往村里走去。
夜里的时候,贵喜睡不着,睡不着就去牛棚跟国庆说说话,他躺在干草堆旁,望着远处逐渐湛蓝的天,这让他想起小时候,那时也常常这样躺着,看天空越发明亮。再过一会儿,小王庄就要醒来了,人们会穿过晨雾笼罩的桑树林,穿过巴泥根草覆盖的田埂,像豆子一样散落在各自的地里。可是——贵喜想,现在那些地里杵着那多的怪物,它们比小王庄的人更高大和强壮,更加起早贪黑。他记得有一次,走过去仔细看了,怪物果真从地下刨出了油,黑黝黝的,这让他好几日都没能睡着。
贵喜被采油队捉住的那天,小王庄沸腾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出这个放牛的贵喜会去偷东西,更想不到为了偷油竟然从茅屋挖了一条长长的隧道。几个采油队的人和小王庄的干部沿着隧道爬了很久,他们匍匐着身子穿过了半个小王庄才到达怪物的身下。贵喜被带到村委会时,审问的人问油都弄到哪里去了?贵喜不说话,再问,贵喜才说,油被埋到地下去了。后来人们发现北坡被掘开的坑里果真有石油斑迹。
贵喜失掉半仓麦子作为罚款,也被关起来教育了三天。这年冬天,那些装载机具的卡车又从村西头缓缓驶来了,这一次是空车,它在小王庄的麦地里呆了整整一天,将采油工人和拆下的零件装走了。像几年前一样,小王庄的人又跑来看了,七嘴八舌地问着,得到的答案是,小王庄的地下已经没有石油了。
大地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那些被怪物刨过的地方没有再种庄稼,油污像身上的疥疮脓液四处流淌,一些地方变成了大窟窿,下雨的时候仿佛能听见那深不可测的响声。贵喜牵着国庆一个窟窿一个窟窿地看过去,再用脚踩踩满是油污的泥土——采油队不知又将去向哪里,贵喜坐在北坡上想着,他们像一阵风似的来了,又像一阵风似的离开了。
7
也不知道哪一年,小王庄的人开始喊贵喜为老贵喜了,人们早晨碰见了,就说老贵喜放牛去了啊。晚上看见又说,老贵喜放牛回来了啊。老贵喜的的确确老了,他和他的牛都老了,每天他们穿过小王庄的那条路,显得缓慢而悠长。
国庆不再犁地了,也没有地可供它犁了,小王庄的北边新建了工业园,原本长着麦子的地里砌上了很多厂房,有来来往往的人,也有进进出出的车,“小王庄”这个被叫了几百年的名字也被“城北工业园”代替了。几条宽大而厚实的水泥路从村里穿梭而过,老贵喜的七分地也被征用了,水泥将它们结结实实地覆盖在底下。他睡得越来越少,每天天还暗着就起来了,走在属于自己七分地的水泥路面上,水泥太硬,没有泥土从脚丫缝里绵绵往上挤的松软。他看见一些牛脚印草正从水泥路的侧缝往上钻,很艰难地挺出一两片叶子。再后来,老贵喜总是半夜醒来,他仿佛听到七分地在底下的嘶喊和呻吟,它们见不到雨露,也见不到阳光。
更多的土地被钢筋水泥覆盖了,水泥正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小王庄。北坡和南岸,那些曾经放牛的地方,都已经砌了厂房。老贵喜仍然从村里经过,他和他的牛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只要有一丝儿力气,老贵喜都要牵着国庆去吃草,每天早晨他们缓慢地穿过小王庄,六只脚冉冉又徐缓地走着。黄昏远去之后,他们又回到小王庄,老贵喜弓起的驼背和他的老牛一样,他们裸露着暗黑而微红的肩头,一前一后,在夕照里缓缓前行。老贵喜总是会想起很多年前的事,想起和恩民躺在苜蓿上的那个晚上,想起和国庆躺在七分地上的那个晚上,耳边有徐来的风,身下是绵软而踏实的土地,国庆在唱歌,声音是那么干净明亮,国庆大声唱着——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劳作……他和他的老牛一直向前走着,缓缓又缓缓,他们知道,穿过了小王庄,前面,总有一片土地青草正绿。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