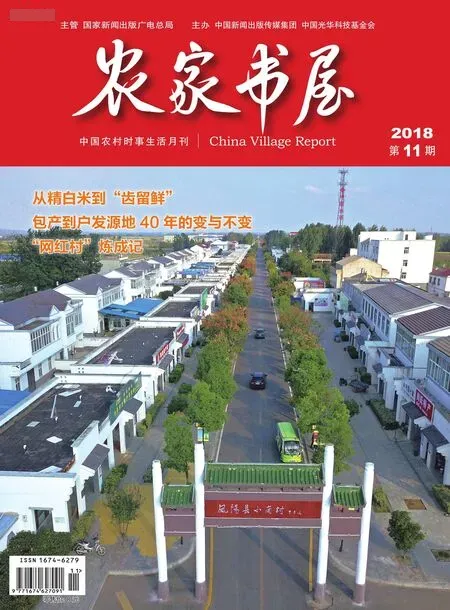环球新闻眼
逆境的作用
The New Yorker 《纽约客》 2014.10
由穷变富的故事是美国人传记的主旋律,多年来,它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19世纪的版本强调弥补不足的重要意义,宣称如果想出人头地,最好从底层做起,在此才能学到成功所需的纪律和动机。
如今这种理解已完全颠倒,成功被视为善用社会经济优势,而非弥补不足。社会流动机制(比如奖学金、扶持行为、住房津贴、照顾低收入儿童的启蒙计划)的目的,都是试图把穷人由长期处于局外变为局内人,将他们从看似无助的境遇中拯救出来。如今,我们不再从贫穷中汲取养分,而是要摆脱贫穷。大家认可的一件事是:充当局外人,在战略意义上是有价值的,相比富有,贫穷更能使人成功。从根本上说,弥补不足比利用优势更有用,也更有发展潜力。
为什么我只想活75岁?
The Atlantic 《大西洋月刊》 2014.10
75岁,这就是我想活的寿数。
这种偏好让女儿生气,让兄弟烦恼。好友们都说我失去了理智,口是心非;说我并没想清楚,世界丰富多彩,要看、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为了让我信服自己是错误的,他们列举了许多我所熟知的人,他们的年龄都超过75岁,但生活都过得很好。他们相信,随着我离75岁越来越近,我会将希望活的岁数先推到80岁,再推到85岁,也许还会到90岁。
没错,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死亡无疑是一种损失,它剥夺了我们的经历和参与重大事件的机会,剥夺了我们与爱人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光。一句话,死亡剥夺了所有我们所珍视的东西。
然而,有一种简单的道理,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都不愿承认:活得太长也是一种损失。它让许多人不是残疾,就是步履蹒跚、气息奄奄,这种状况尽管可能比死亡好些,但却剥夺了我们的一切。活得太长夺走我们贡献于工作、社会与世界的创造力和能力,改变了人们对我们的感觉,改变了他们对我们的叙述,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对我们的回忆。在他们记忆中,我们不再充满活力、匆匆忙忙,而是身老体弱、徒劳无益,甚至让人可怜。
我的大学是个实验室
nature 《自然》 2014.10
现代大学是上千年学术研究传统的继承者,但是它们同时遭到21世纪科技、经济以及社会剧烈发展的冲击。就像一个实验室,经过反复试练、犯错、再实验,如今全世界的大学正在寻找新的思考方法和行动方案,以待再次腾飞。
2011年,数所美国高校公开了首批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这些录制的课程被上传到网上后供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免费获取。其他的学术机构随后也开始尾随,各国媒体把慕课如何引发一场高等教育的全面转型捧得天花乱坠。
Mike Sharples对此持保留态度。他在英国密尔顿凯斯开放大学工作,该校已经通过信件、电视、电脑向全世界教授了40年的公开课。但受到已去世的英国教育心理学家Gordon Pask的鼓舞,2012年,担任该校教育科技部主席的Sharples加入了一个英国学者协会,决定创建下一代慕课,因为Pask认为学生会通过相互交流建立个人的知识体系。
而新的慕课将会把社会参与度放在公开课的核心,鼓励网上交流“像网络游戏一样活跃”。“这个过程就像赌博一样。”Sharples说,“现在看来,人们似乎很愿意谈一谈学习的事儿,不过一年前形势却不那么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