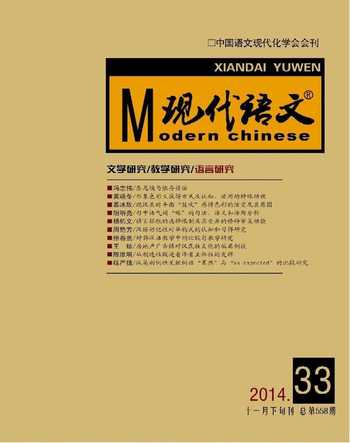从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陈维明 谌莉文
摘 要:翻译的“文化转向”使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重视。本文从创造性叛逆角度论述了译者的主体性,提出了主体性有其受动的一面,基于创造性叛逆的三种类型,即特色翻译、有意识误译和改编,以《红楼梦》英译本为语料,分析了译者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展现不同译文风貌的主体性翻译过程。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创造性叛逆 红楼梦 受动性
一、引言
自古以来,“忠实”被捧為翻译的金科玉律,从支谦的“因顺本旨,不加文饰”、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到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论”及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这些翻译思想无不将作者及原作置于中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抹杀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至于译者完全被边缘化。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把译者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贝尔曼(Berman,1995)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翻译主体”上,必须以译者主体为基本出发点,并提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操纵学派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这些观点使学界重新认识到: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原作和译作的中间人,是翻译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发挥其主体性。
翻译有创造性和叛逆性,创造性是它赋予作品崭新的面貌,叛逆性则是对原作的客观偏离,即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的提出,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认为,译者主体性不仅在于译者能动性的发挥,更体现在译者在翻译时的受动性会有意识地转化为能动性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正是译者进行创造性叛逆的过程。本文立足以上观点,通过选取《红楼梦》中体现译者主体性的若干例子,说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译文以何种形式呈现。
二、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
要了解译者主体性,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主体性。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自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简言之,主体性就是主体的本质特性。对于“译者主体性”,国内有多个学者对其下了定义。译学辞典对“译者主体性”的定义是:译者主体性,亦称翻译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性(方梦之,2004:82)。査明建(2003:22)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屠国元(2003:9)认为:译者的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
不难看出上述几个定义的相同点:都认为翻译的主体是译者,强调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主体性不仅只有能动的一面,还有其受动的一面。译者的受动性表现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原作者和原作的思想及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译者的主体性应该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创作译本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但受到原作的背景及其文化的束缚,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任意的。
“创造性叛逆”由法国文论学家埃斯卡皮(1958:137)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考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能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还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可见,翻译并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而是将原作置于另一个全新的语言和社会环境(即上文中的“参考体系”)中,参考体系的变化使得翻译由机械的文本对应转换为有意识的“叛逆”;在新的参考体系中,译作必将与目标读者产生新的文学交流,等同于在参考体系的变换中获得了新生,这正是创造性的体现。
国内研究“创造性叛逆”的学者谢天振提到,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再现原文的主观努力,而叛逆性则是对原文的客观背离,但两者无法分离开来,是和谐的统一体(谢天振,2013:106)。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译文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译者的主观意识,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肆意发挥、信马由缰,叛逆性是一种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如果译者过度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原作之上,那么其主体性就会走向极端,从根本上偏离了翻译这一本质任务。
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是判断译作优劣的重要标准和翻译成败的杠杆。那么,忠实是不是就意味着放弃译者的能动性?答案是否定的。“笨拙的‘忠实也许会导致叛逆,而灵活的‘叛逆也许正好揭示出真正的忠实。”(许钧,1997:41~42)当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无法实现其目的和需要时,其受动性就会有意识地转化为能动性。这种有意识的转换恰恰体现了“创造性叛逆”。
本文基于埃斯卡皮和谢天振的观点,结合译者主体性的特点,提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创造性叛逆:1.特色翻译;2.有意识误译;3.改编。在下一部分中将对其逐一分析。
三、《红楼梦》英译本中创造性叛逆的体现
本文选择《红楼梦》作为语料。霍译本和杨译本的《红楼梦》都享誉国内外,但风格形式迥异,体现了鲜明的译者主体性特征。下文将从创造性叛逆的三个类型看《红楼梦》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一)特色翻译
译者在践行翻译过程中会有自己的原则和策略,在处理相同的作品时,不同的译者往往会采取自己喜好的特征手段,本文称之为“特色翻译”。《红楼梦》中有200多首诗词,不但行文优美,而且大部分都有着深刻的内涵。在翻译这些诗词时,霍克斯和杨宪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例如:
(1)原文:仙袂乍飘兮,闻麝兰之馥郁,荷衣欲动兮,听环佩之铿锵。(第五回)
霍译:And a shadow athwart the winding walk announces that she is near,
And a fragrance of musk and orchid from fluttering fairy sleeves,
And a tinkle of girdle-gems that falls on the ear,
At each movement of her dress of lotus leaves.
楊译:Her fairy sleeves, fluttering, give off a heady fragrance of musk and orchid.
With each rustle of her lotus garments,her jade pendants tinkle.
“赋”是一种以“颂美”和“讽喻”为目的的有韵文体,多用铺陈叙事的手法,必须押韵,这是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主要特征。与其他诗歌文体一样,赋也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经常采用排比、对偶的手法。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诗歌中精炼的文学形式和丰富的内容紧密结合,译者在翻译时,若保留了内容,可能破坏形式;若顾及形式,则可能有损内容。从上文的《警幻仙姑赋》选段翻译可以看出,两个译本在内容上都忠实于原文,但却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译法,译者的主体性在不同层面上得以发挥。霍译本沿用了原文押韵的方式,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杨译本在形式方面虽稍显逊色,但细细品读,亦有优雅婉转之感。
(二)有意识误译
误译可分为有意识误译和无意识误译。无意识误译不符合翻译的要求,其成因是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内涵和文化背景没有足够深入的了解。这种译者主体性的错误发挥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而且在翻译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有意识误译,顾名思义,即译者“有意而为之”的误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体现和译者主体性的正确发挥。
《红楼梦》第一回有这样的描述: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两位译者对“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的翻译大相径庭。霍克斯译为“seventy-two feet by a hundred and forty-four feet square”,而杨宪益译为“a hundred and twenty feet high and two hundred and forty feet square”。根据中国古代的度量衡,1丈等于10尺,3尺等于1米;在英语中,1英尺等于0.3048米。因此,12丈=(12*10)/3米=40米=40/0.3048英尺≈131英尺。同样地,24丈≈262英尺。不难看出,霍克斯翻译的石头尺寸相比其真实尺寸大大缩小,属于无意识误译。杨宪益的翻译虽然接近真实尺寸,但也不算精确。根据《脂砚斋》的注解,原文的“十二”与“二十四”暗指金陵十二钗正册和副册。杨宪益已有所意识,故对尺寸稍加修整,以彰显其内涵,属于有意识误译。
在《红楼梦》中,作者用了大量的颜色词来描写服装、建筑、环境等,其中红色是贯穿全文的主色调。而在霍克斯的译本中,首先在书名的翻译上有意避开“红”字,而采用《石头记》这一书名,原文的“怡红院”“怡红公子”被译成了“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和“Green Boy”,“红色”被误译成了“绿色”。根据霍克斯的观点,红色在英语中有“危险、暴力、愤怒”的含义,如果把原文中的“红”译成“red”,很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误解。常规的译法已经无法传达原文的意义,因此为了迎合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霍克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避开直译,采取有意识误译,这一过程体现了译者的受动性向能动性的转换。
(三)改编
改编不仅是作品文学样式、体裁的改变,也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中国人讲究和谐美,很多对偶的表达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红楼梦》中亦有不少例子。
(2)原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第十一回)
霍译: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
杨译: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3)原文:凤姐儿笑道:“我看你厉害。明儿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别抱怨。”(第四十三回)
霍译:“Youre a hard woman!”said Xi-feng.“One of these days when I have you at a disadvantage, you mustnt complain if you find me just as much of a stickler.”
杨译:“What a terror you are,”protested Xifeng, smiling.“Dont complain next time youre in trouble if I put on the screws.”
从上述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霍译本基本放弃了原文的对偶形式,采用了通俗的句式翻译,杨译本也没有全部保留原文的形式。但是不能就此断定两位翻译大家没有能力再现原文的对偶形式,恰恰相反,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些句子虽为对偶,但都是出现在口语表达中,若是按对偶形式翻译,不免有文绉绉之感,失去了口语表达的随意性和自由性。鉴于此,两位译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使之为读者所接受。
四、结语
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码转换,更是围绕原作进行的再创作。再创作的过程是译者发挥主体性的过程。本文以《红楼梦》英译本为语料,从创造性叛逆的视角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研究发现,两个译本的《红楼梦》均体现了不同程度的译者主体性,展现了不同的风貌,说明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还能决定赋予它们以何种生命,也说明了译者只有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性,敢于叛逆,敢于创造,才能让《红楼梦》这部鸿篇巨著为更多的外国读者接受。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
版社,1958/1987.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3]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
[J].中国翻译,2003,(1):19~24.
[4]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5]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
2003,(6):8~14.
[6]谢天振.译介学(增订版)[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7]许钧.我和翻译[A].戴立泉,杨怀宇.江苏学人随笔[C].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杨宪益,戴乃迭.A Dream of Red Mansions[M].北京:外文出
版社,2003.
[9]Berman Antoine.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John
Donne[M].Paris:Gallimard,1995.
[10]David Hawkes& John Minford.The Story of the Stone[M].
London:Penguin Books,1986.
(陈维明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谌莉文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31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