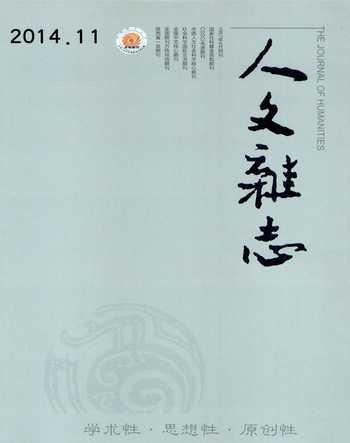具体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休谟问题”核心含义分析
徐冰
内容提要 “休谟问题”有因果性的必然性问题和具体的因果关系问题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在因果性的必然性层面上,又有人类因果性思维的必然性和现象的因果性必然性两层含义,在因果性思维形式之下才有对现象之因果必然性发问的问题。但仅凭因果关系的普遍性也说明不了具体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在具体的因果关系层面上,又有着具体的因果关系、具体的因果关系的现实、用具体的因果关系接受的特殊现象这样三层含义。休谟问题的核心含义是具体的因果关系的必然性问题,能针对这一层次做出回答才算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这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既不是可以经验到的,也不是可以完全抽象的认识,而是属于关涉到“存在”本身的本体认识。
关键词 休谟问题 因果问题 因果必然性 具体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B561.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1-0007-08
休谟以彻底经验论的态度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进而对归纳法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此即“休谟问题”。休谟问题一直是近现代哲学史上研究的重点课题,影响深远。休谟提出的疑问深刻地揭示了理论和实际的矛盾。对因果关系和归纳法的运用可以说是人类赖以前进的基础性工具,但却无法从理论上逻辑地说明之。这种滑稽的事情,使哲学家们痛心疾首,他们费尽一切心机,提出一个个方案试图解决,可是结果并不乐观。面对休谟问题怀疑主义结论的困扰,分析哲学的领军人物罗素曾无奈地说它“既难反驳,同样也难接受。结果成了给哲学家们下了一道战表,依我看来,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够上对手的应战。”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00页。现在,几十年又过去了,分析哲学可以说也已走入了后分析时代,有没有够得上的对手的应战呢?我想,今天重提罗素的这个论断仍不能说是过时的。且当代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对休谟问题的研究有一种科学主义态度和技术化的倾向,实际上也就把哲学意义上的核心问题抛开了,遮蔽了其作为认识论研究的本来面目。故我们认为,对休谟问题的内在涵义很有清理一下的必要,以揭示出其实旨所在。本文力图澄清问题本身,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对“休谟问题”研究的反思
以往对“休谟问题”的研究,从研究路向上可以分为以“归纳问题”(the problem of induction)为中心问题和以“因果问题”(the problem of causation)为中心问题两条路径;从研究方法上则大致主要有前提设定、逻辑和语义分析、反归纳等三类方案。以路向和方法为经纬,分析以往的解决方案,可以说不管是康德的认为因果性是“先验范畴”的先验论,还是穆勒(密尔)主张“自然一律性”为归纳推理的基础的演绎主义,还是罗素为科学的归纳推理设定的五个共设,还是金岳霖提出的归纳法的永真原则——因果关系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等,都是想通过把归纳推理的基础归之于某种先在的大前提。而不管是卡尔纳普认为通过制定概率演算的形式系统的“概率逻辑”,还是赖欣巴哈基于实用的“无损失”原则提出的“频率极限”解决,都是想提高归纳前提和结论之间的确认度,制定出一套形式化的达到演绎般精确清晰的归纳逻辑。刘易斯的反事实条件因果观、克里普克的因果模态逻辑及戴维森、麦基(J. L. Mackie)等则是从语义学、解释模型等方面分析因果解释的结构和类型,他们着重分析的是因果关系的定义上的问题。 Davidson,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Secon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pp.149~162.以上方案不管何种办法,在对休谟问题的立场上是积极的,而波普尔采取的则是消极的反归纳主义立场,要用“证伪主义”取消掉归纳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科学实际上是在猜想与反驳的交织中前进,但他却又无法解释那未被证伪的猜测的可信度又是如何提高的。这些方案在历史上都曾领一时风骚。平静下来审视,虽然这些方案中“不乏对科学思维有价值的见解,但它们或者方案本身有明显缺陷,或者试图改变、消解、甚至拒斥所讨论的问题,因而都未能对休谟的问题给出真正满意的回答。” 周晓亮:《休谟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耻辱。” “每一新的科学发现,每进一步从哲学上对归纳法的探讨,似乎都越来越证实哲学家布罗德(C.D.Broad)的这一论断: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耻辱。……”参见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iiller):《归纳问题:休谟提出的挑战和当前的回答》,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7页。具体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休谟问题”核心含义分析反思以往的研究,在科学哲学那里,“归纳问题”已成为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能够最终得到解决,其他许多科学哲学问题(如科学划界、不充分决定性论旨、相对主义等)都能迎刃而解。”⑤ 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但是,可以说直到最近流行的贝叶斯主义,不管分析得多么繁冗细致,说到底都是外部的解决方式。一言以蔽之,科学哲学的研究越来越不是纯粹哲学意义上的了,这种方法是不可能最终从根本上解决“休谟问题”的,“归纳问题或验证问题不能最终归结为逻辑与数学的运算”,⑤且有离题之嫌;而在分析哲学那里,虽然恢复了对因果问题的研究,可他们手里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研究工具却并无改变,他们的工作总体上还是既定因果关系下的形而下的科学性分析,并非形而上学意义上对因果关系问题本身的思考。刘易斯的反事实条件因果观、克里普克的因果模态逻辑及戴維森、麦基(J. L. Mackie)等都是从语义学、解释模型等方面分析因果解释的结构和类型,他们着重分析的是因果关系的定义上的问题。他们只是在那里无穷无尽地去分析因果关系,举出很多例子,设置很多奇奇怪怪匪夷所思的场景,然后提取出来形式化的东西作为结论。他们的工作虽然对我们清楚认识因果关系概念的确切含义很有意义,但毕竟是在因果关系之下的讨论,而非对因果关系本身的研究。他们的解决方式虽然把问题分析得很细致,制造出新的概念,转换出新话语方式,但是似乎在问题的根本层面上并没有纵深的新突破,虽细致却不深刻,且失于繁琐,问题本身反倒淹没在他们精细的术语之中了,易被人诟病为无关宏旨的“学术游戏”。的确,经过分析哲学家们的努力,形而上学再也不能因袭传统的表述方式,但他们的工作同样证明,形而上学问题却也并未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就此消失。 关于历史上对休谟问题的解决方案,多人都有过总结。最近的研究,可参见周晓亮:《休谟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M.J. Loux. Metaphysics: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韩林合:《分析的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陈晓平:《贝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对休谟问题的思考》,人民出版社,2010年。
二、“休谟问题”的两个层次:因果性的必然性和
具体的因果关系
休谟在《人性论》第一卷第三章“论知识和或然性”第三节中对因果关系的必然联系(necessary connection)问题他提出两个疑问为纲进行阐述:
第一个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每一个有开始的存在的东西也都有一个原因使这件事是必然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断言,那样一些特定原因必然要有那样一些的特定结果?我们的因果互推的那种推论的本性如何?我们对这种推论所怀的信念又是如何? D.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 House,1999,p.78.
第一个问题即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的质疑。这是第一层的问题,即无论什么事物,凡是我们经验到的总是有原因的,总是某一或某些原因的结果,绝无无原因而存在的东西。其必然性何在呢?对这个常识认为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道理,休谟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凡是承认这个原理的人,既举不出任何证明,也不要求任何证明,就把它认作理所当然的,这是独断论。若需要证明,人们会说,这个命题是建立在直观和理性证明的基础上的。休谟对此提出了反驳。他反驳了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四种对因果关系必然性的证明,这里不必细说,我们着重要探讨的是休谟把第一个问题过渡到第二个问题的问题。
因果关系既然只能依靠我们的经验来说明,可是根据其心理原子论,经验在本质上都是个别的,经验中并不提供普遍的东西,因此无法用经验来说明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那是“不方便的”。于是,休谟就将如何用经验来说明“凡事物开始存在必有其存在的原因”的问题“降低”为说明“为什么特定的原因必然要有特定的结果”,“为什么形成特定的因果推断和信念”的问题,即由第一个问题向第二个问题进行了过渡。这个过渡是很成问题的,但似乎前人少有关注。我们认为,一方面,普遍的因果关系问题与特别的因果关系问题是相关的,可以由对后者的说明来反诸前者。但是,另一方面,二者毕竟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不能由下一层面的讨论代替上一层面的讨论,因为第一条的问题是原则上的问题,故实际上是休谟在这个过渡中把第一个问题轻轻地就给放过去了,下文完全是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讨论了,甚至在作为《人性论》知识论部分简写本的《人类理智研究》中对于这个问题也只字未提。这样,虽然休谟明确提出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但是在他那里两个不同的问题就已含混不清了。笔者认为,这对后世造成了很大误导。面对因果问题,往往把其中一个问题的解答当成问题的全部解決,典型的就是康德的解决思路。康德实际上说明的是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问题,即说明因果范畴的先验性,进而说明人类知性结构中的各种先验范畴。但这并不能说明特别的因果关系问题,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与休谟相反,康德又把第二个问题给丢失了。休谟是把第一个问题混同于第二个问题,康德则是把第二个问题混同于第一个问题。康德的工作意义是第一层因果性的必然性问题的现象的因果性之必然性问题的解决上。康德之工作对具体的因果关系的解决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解决不了第二层具体的因果关系必然性的问题。康德指出了因果关系有其先验性,但是这不同于具体的因果关系之必然性,仅凭因果的普遍性说明不了具体的因果关系之必然性。下面具体来分析。
三、因果性的必然性问题
因果性的必然性问题实际上又包含着两层问题,即“因果性思维的必然性问题”和“现象的因果性必然性问题。”
1人类因果性思维的必然性问题
休谟这里第一条问题是在问因果性之普遍性必然性的理由问题(注意:这里不是原因(cause),而是理由(reason)),即无论什么事物,凡是我们经验到的总是有原因的,总是某一或某些原因的结果,绝无无原因而存在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其必然性何在?那么这个“为什么”就不同于问具体现象的因果关系的为什么,是从抽象的整体意义而言的,那么这里就隐含着一个更为前提性的问题——因果性思维的问题。但休谟并未意识到此。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休谟第一条问题是想从根子上对因果性发问,可是他用来质疑因果性的工具恰恰就是因果性本身,他没有意识到他对因果性发问本身就已经是对因果性的运用了,即在追问因果性之原因,按康德的概念来说,即你已经在使用着因果范畴了(休谟在因果关系上的这个毛病正如笛卡儿在反思问题上的毛病)。故人类因果性思维之必然性问题是关于因果性问题之完整严密无漏之逻辑体系必有之前提问题。也正是在此,康德意识到了休谟的漏洞,由此入手来解决休谟问题。在人之因果性思维形式之下才有对现象之因果必然性发问的问题,这时,对因果性发问就不再是问“因”而是问“理”。按康德的方式就是说因果律是先验的,而理由律是先天的。而休谟手里拿着因果性思维的先天的理由律去质疑先验的因果律——现象的因果性的必然性。
很显然,在人类的因果性思维之必然性问题上,因果性思维是有着无可逃脱的先验性:质疑因果性本身就是运用因果性思维的结果,没有因果性思维,根本就不会发生质疑这回事,质疑因果性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悖论。故在这一层次上休谟的质疑也就不攻自破了。
2现象的因果性必然性问题
就普遍意义上现象的因果性的必然性而言,康德的论证已成为常识,我们不必再详述,这里关键要分析一下其对“主观相继”和“客观相继”的区分问题。因为康德的论证出发点是试图从对象是否同现象相继一致做出“主观相继”和“客观相继”的区分进而解决休谟问题。康德对休谟问题之集中分析和解决主要是在“先验分析论”的“原理分析论”的“经验的类比”的第二类比——“根据因果性规律的时间相继的原理”一节中。为了反驳休谟把因果性解释为人心中观念的重复而形成的习惯性联想,康德认为休谟的错误在于把观念的主观经验联系同对象的客观必然联系混同了,也即把“主观相继”与“客观相继”混同了,故康德首先对二者进行区分,由此来解决休谟问题。
康德的办法是先指出“对显象的杂多的把握在任何时候都是渐进的。各部分的表象相继而起”,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34页。这是从休谟立论处出发的。但他下面提出表象相继是否也在对象中相继的问题,这样他就预设了一个无来由的确定的“对象”,虽然他在第二类比这部分一开始就“预先提醒”了在第一类比里阐明之实存原理,但实体之有并非具体对象之有,但他就以之为基点了。这样他确定了对象之客观性,于是就有了“主观相继”与“客观相继”区分的问题:表象相继不在对象中相继即“主观相继”;反之,表象相继也在对象中相继即“客观相继”。
其实康德的这种区分误用了因果律,这两种“相继”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差别,都是客观的认识,都是本身被主体所认识到了的真实对象中的变化的认识,二者并无实质不同。正如叔本华所说:“在我经过一队士兵和一队士兵经过我之间,是既不存在任何差别,也没有任何差别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直接在对象中产生并不依赖于主体意志的连续,这里没有因果联系,却是正确地认识到的联系。这样,叔氏就用康德的例子驳斥了康德的证明。所谓“一个跟着另一个”并不一定就是“一个来自另一个”。白天和黑夜彼此相随,“这是一切连续中最古老的并且是最不可能有例外的一个”,然而“却从未使任何人陷入把它们当作彼此互为因果的错误。”③ [德]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陈晓希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93页。
康德之证明的实质是循环论证。因为如果我们象康德那样认为认识连续的客观实在性的唯一手段就是必然性的因果关系,那么就不能有因果关系以外的连续了。这样,说一个状态跟随另一个状态和说一个状态来自于另一个状态就成了同语反复,因为二者是一回事了。但这样一来,其实恰恰就走向了康德所要证明的反面,到休谟那里去了。因为休谟对因果性的怀疑也正是建立在否认连续与因果之区别上的,他说我们只能经验到一个个现象的相继出现,哪里能经验到其中的因果联系呢,所以他宣称一切后果都不过是一种顺序罢了。这样,康德和休谟在他们各自的证明中,就正好犯了彼此相反的错误,“休谟主张一切后果都不过是单纯的顺序,而康德则认定一切顺序都必定是后果。”③
总之,康德试图从对象是否与表象相继一致来反驳休谟,但在“主观相继”中却无法确认不与表象相继一致的对象;在“客观相继”中,因果关系问题却又不与对象同表象相继与否的问题有实质的联系,即使对象与表象相继一致也不能说明相继的必然因果性。说到底“因果范畴”之确立也只是解释一件事情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充分地说明一具体事件的发生,就须进一步说明具体的因果关系的问题。
四、具體的因果关系问题
1两种不同的“必然”
对具体的因果关系问题,首先要说明一下“必然”的问题。因果关系背后的必然性一度被当做严格决定论取消掉,“严格的因果性观念应予放弃,概率规律把以前为因果性占据的地盘夺过来了。” [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8页。卡尔纳普提出“统计规律”的概念来理解因果性,也即因果性不再是指原因怎样必然地产生出结果,而是指原因产生结果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因果关系不再意味着必然性,而变成了有一定概率的偶然性了,“全部科学规律在这种意义上都是统计性的”。 [美]卡尔纳普:《因果性和决定论》,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77页。可是正如石里克早已在《普通认识论》中所明确指出的,概率对归纳法既构不成支持也构不成反驳。一般所理解的骰子掷出六点的概率是六分之一之意思,通常的解释是说在一个很长的掷骰子的系列中,掷的次数越多,每一面向上出现的次数就越接近于总数的六分之一。但这种表述是不严格的,因为“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实际上永远不可能给出无限多的事件,求助于极限并无所助益。 [德]石里克:《普通认识论》41节“关于归纳知识”,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70~472页。不可能提高所谓的逻辑确证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不管概率的数理统计方面的意义,就认识论上而言,概率并无实际意义,说色子的一面朝上的概率为六分之一,或者赖欣巴哈“明天太阳很可能也从东方升起”之谓,除了能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外,又有什么实际预测的意义呢?“如果A与B真正存在,那么,断言A与B有某种概然的联系就是毫无意义的。”“断言一个陈述可以不仅是真的或者假的,而且也是概然的,这根本对现实毫无所述。” 洪谦:《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7页。正如波普尔批判归纳逻辑者的,把逻辑问题和心理问题混淆了。 K.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24~25.
那么,什么是必然性?可以说:一种是不关实现的必然,如1+1=2之类,可谓纯理,因为1+1不存在一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等于2的问题(问1加1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等于2,那只是脑筋急转弯)。不必要非先拿出一个,再拿出一个苹果摆在桌子上,才可知道1+1=2。休谟自己也说,“这类命题,只凭思想的作用就能发现出来,而不以存在于宇宙中某处的任何事物为依据。纵然在自然中并没有圆形或三角形,欧几里德所证明的真理仍保持着它的可靠性和自明性。” [英]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页。另一种则不然,是要关实现的必然,则存在一个实现与否的可能性的问题,存在一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的问题。既如此,则你不能因为不实现就否认有这种必然,就否认这种因果关系。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和实现与否是两回事。并不是说因果关系不成问题,而是说休谟用经验去质疑因果关系是不合法的。经验是具体的,关时空的,必然性则是不关时空的,不能以关时空的现实的实现与否去质疑不关时空的必然性。也正因这种必然不同于那种必然,金岳霖把它称之为“固然”,但是反过来说,不实现固然不能说没有这种与经验现实相关的固然之理,可是仅仅指出休谟的对两种必然的混淆也并不能立刻就说明就有这种固然之理,这也同样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但金氏到此为止了。 金岳霖:《知识论》, 商务印书馆,2004年。在金岳霖的《知识论》那里,这种理却就是已认的了,他并没有进一步给出论证来说明之。我们认为金氏最终还是丢掉了问题,或曰用对休谟以特殊之实现与否来质疑理之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取代了、掩盖了何以有此理的问题。对这样的必然性我们称之为具体的因果关系。
2具体的因果关系的层次
(1)具体的因果关系
我们说甲因必有乙果,实在是说某因有某果,故这里已不是从经验世界整体上而言的因果关系,而是具体的个别的因果关系,有此因果关系与彼因果关系之别,即休谟所说的“特定的因果关系”。在此,现当代分析哲学家们对具体“因果关系”的类型进行了很细致的语义分析,大致有三种:一是认为物理对象(physical objects)是真正的因果关系项,如齐硕姆(R.Chishom);二是认为事物具有的性质(properties)才是因果关系项,如托雷(M.Tooly);三是认为事件(events)或曰事态(states of affair)才是实际上的因果关系项。我们用卡尔纳普的石头砸玻璃的例子来分析。要寻找“玻璃破碎”这一结果的原因时,是石头这个对象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呢?还是石头具有的坚硬度这个性质是原因呢?还是拿石头砸玻璃这一事件是原因呢?我们认为“性质”因果关系说是把握住了因果关系核心层面的含义,因为“石头砸玻璃,玻璃破碎”这一事件发生实际上可以说是由无数个原因造成的,如麦基(J.L.Mackie)所说的“因果场”(causal field),或者金岳霖所说的“因果底背景问题”。石头硬固然是原因,难道玻璃脆不是原因吗,空气的阻力不是原因吗,地球引力不是原因吗,抛石者的力量大小不是原因吗?等等背景问题是永远也分析不完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起作用的毕竟是各自的性质,虽然最终是无数个表现出来的事物的性质共同造成了玻璃破碎的结果。但是性质因果关系说虽然找到了真正的因果关系项,可是这还并不是我们这里要说的具体的因果关系,里面还有更核心的一层问题。我们单取出一条原因来分析,石头的坚硬性质(也可取出玻璃的脆性等等皆可)固然是造成事件发生的一个原因,但石头具有的坚硬性质本身并未在此得到说明,而这才是最关键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具体的因果关系。也即石头何以就有着坚硬性呢?至于说肯定了此层面的因果关系之下的引起别的什么结果那又是等而下的事情了(分析哲学家们的研究偏颇即在这里,只是分析下一层次的因果关系)。
(2)具体的因果关系的现实
而对这样的具体的(特定的)因果关系,还要作两层区分。一是与具体时空无关的“特定”,我们用A-B来表示(A表示原因,B表示结果),它应是某一具体自然律(the law of nature)背后的原因;二是与具体时空相关的“特定”,即具体的自然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我们用A′-B′来表示,在此层面上也就呈现出具有坚硬性质的石头来。这个区分是个关键,也正是本文的重点。我们反观以往的研究就会发现,不管是在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还是现在又重新以形而上学的态度研究因果关系问题的分析的形而上学那里,终究没有把与具体时空无关的“特定”从与具体时空相关的“特定”,即具体的自然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中剥离出来,没有发现在具体的自然律之后还有个更为根本的东西,还是把A-B当成了A-B,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这个层面上的问题。当然,即便是具体的自然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说是超时空的,否则就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自然律意义上的超时空只是超越一次次特殊的时间、空间,就它所涉及的物理现象,共相的类而言,它还是必须要具体到此类上,不可超出。而作为A-B层面上的因果关系,则不管这些东西,它更抽象、更纯粹。不理解此不同的话,则就能貌似成功地驳斥了休谟。对休谟的一种批判就是说太阳升起是有条件的,只要满足条件就能预测明天太阳必从东方升起。但这种批判实在是把具体的因果关系问题的第二层的问题混同于第一层的问题了。岂不知地日关系之出现本身就是或然的,也是早晚要解散的。不明白休谟真正质疑的乃是具体自然律背后的原因层面上的因果关系。还比如上面分析过的石头砸玻璃这个例子,如果仅分析外在的情况,那么永远也分析不完,因为不管怎样,石头也有可能砸不碎玻璃,如果距离太远或者玻璃太硬或逆风顺风之类等等千变万化的情况。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石头具有坚硬的性质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把这一层次的因果关系解释得了,下面的事情也就势如破竹了。
(3)用具体的因果关系接受的特殊现象
用具体的因果关系接受的特殊现象才是与特殊的时空中的现象相关的因果关系,我们用a1-b1 来表示。在此层面上才与归纳方法发生关系。休谟就是在这里指清了由归纳法归纳不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关系,即因果关系是不能由归纳法归纳出来的这个人们习焉不察的认识误区,而反过来归纳之为真却要求着以必然的因果关系为根据。而在这一层次上的情况那就无穷无尽、千变万化了。著名的“拉普拉斯妖”就是坚持这一层面的因果決定论(the causal determinism),相信如果有那么个知道在一定时刻的自然界里一切的作用力和组成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的位置,且又能够用数学分析处理这些数据,把宇宙中的一切运动形式都包含在一个公式里的“精灵”,那对它来说,整个世界就没有不确定的东西,过去、未来都会了如指掌。显然,这是把用具体的因果关系接受的特殊现象这一层的问题同具体的因果关系的现实这一层的因果关系混淆了。按金岳霖的理论,即把“理有固然”同“势无必至”两层混淆了,把“理有固然”等同于“势有必至”了。另外关键的是,即便是有这么个神通广大的精灵存在,手里抓住那统摄宇宙的公式,的的确确整个宇宙都呈现在它面前,那又能怎么样呢?他能解释这个公式吗?运用公式和解释公式是两回事。也即还是回答不了核心层面上的因果关系的问题。
这样我们再来分析那个著名的太阳升起的例子,也就可以理清楚了。的确,“‘太阳明天将不出来这个命题,和‘太阳明天将要出来这个断言是同样易于理解的,同样没有矛盾的。因此我们要想证明前一个命题的错误,将是徒劳的。如要论证它是错误的,一定要证明它包含着矛盾,并且决不能明确地为心灵所构想。” [英]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20页。但是,太阳明天升起与否之问题根本就不是A-B那一层上的问题,它是在一定时空内的,虽然时间长,空间大,也不是A-B,因为A-B与时间、空间无涉。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这一判断,是特别的A-B之理落实到特殊的时空中的具体自然律A′-B′,而某一天之a1-b1则更为A′-B′实现之特殊。这里是三层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自然律的太阳升起,还是要涉及时空的,或曰就是时空中的,还并非A-B。A-B是什么呢?A-B是说,只要有天体满足太阳、地球这样的物理关系(这就隐含着必须涉及到实在),比如在银河系的另一个地方,或者别的什么星系中,那么类似的情况就还会出现,这才是背后真正的必然。这层上的必然才是因果关系的核心问题。何以有这个“必然”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而具体到某个特殊的事件的发生总是或然的,不能用特殊之发生的或然性去质疑因果必然的成立,因为特殊无法必然,只是或然。休谟用特殊事件的发生之或然去质疑b之发生,进而质疑A-B之因果关联存在,这正是其误区所在。也即休谟不可以从b发生之或然性去质疑A-B之一定性、固然性。从经验上讲特殊无论如何没办法必然,它的实现总是或然的,从经验这一层去质疑没有意义。那么只有从何以有此A-B之理上去质疑才合法,这才是核心,即A何以致B。
五、具体因果关系与本体认识
至此,我们已经一层层分析清理出了“休谟问题”的多层含义,最后把核心的问题逼显了出来。可以这样总结:因果关系成立的核心是必然性,必然性成立的关键是具体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也即休谟质疑的核心问题还不是人的因果性思维的必然性或者认为世界存在着普遍的因果关联,或者认为因果律的普遍性,或者特殊事件的实现与否,而是指某一具体的、特别的因果关系A-B的必然性何在。而这种具体的因果关系既不是可经验到的,也不是可以完全抽象的认识,而是涉及到“存在”本身的认识。就此我们剖析一下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对休谟问题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休谟的问题在于他以演绎之必然来要求归纳,休谟问题背后隐藏着演绎主义。问题本身就是不恰当的,混淆了归纳和演绎两种不同方法的逻辑特点,要求归纳具有演绎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因此在休谟所要求的意义上给出满意回答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他以及他之后的几乎所有人都坚持关于归纳辩护的演绎标准,所以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现在休谟问题研究很强的一种理论倾向。 周晓亮:《休谟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我们认为这种反驳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码文只不过是把休谟质疑的归纳方法硬性确立起来而已。先规定好归纳法就是或然的,然后再驳斥休谟质疑或然,这只是玩定义游戏。关键在于要指出不能要求或然如必然的道理在哪里。更有甚者,甚至说“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 陈波:《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这简直就是暴力逻辑了。实际上都又回到了休谟的出发点而已,休谟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以演绎要求归纳。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A-B这一层的麻烦上,它上通下达,它一方面是A—B因果关系的时空世界中的现实,一方面又规模着特殊时空的经验现象;它既不能彻底落实到休谟得意的经验世界,又不能完全脱离感性经验,达到与经验世界无关的必然。
另有人反求诸休谟哲学本身,认为休谟之问题在于他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在于他不承认抽象概念,不承认共相,无法理解不可经验到的因果关系。亦非也。可以说,即便是承认抽象思维,也不能就解释得了,我承认有抽象之A—B的因果联系,但并不等于我就明白何以有此必然关系,即能解释A-B,这是两回事。我看到“神州十号”飞入太空,这是事实,我怎么能不承认呢,但这就表明我明白“神十”是如何升空的吗?按有论者的逻辑,我就应理所当然地懂得了,这种结论又何其荒谬哉!我在这里操作着电脑,我就懂得造电脑之理吗?这是两回事。休谟虽然指出不能由以往一直相似就推出将来与现在和以往相似。但是这里他毕竟也得承认以往是相似的,关键在于这个已是事实的相似我们也并没有解释何以相似,若能解释,那也就无关乎什么以往、现在还是将来。承认世界有齐一性,事物有相似性,并不等于就能解释世界何以齐一,何以相似。休谟的逻辑是,我们既然解释不了世界的齐一性,那就不承认这种齐一性。我们的逻辑是既然世界有齐一性,那你就不应该再质疑。既然如此,那么思维方法上难道还不是一样的吗?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保持对宇宙的敬畏之心吧。
这样就凸显出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方式这个根本的认识论问题: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两种认识方法是完备的么?或曰综合知识和分析知识两类知识是足以描述世界的么?从我们的结论就可以看出在核心问题上它们是捉襟见肘的。我们知道,作为彻底的经验主义者的休谟本人怀有着强烈的非此即彼的信念,他的《人类理智研究》的结论就是如果一本书中既没有关于数学方面抽象的知识,又没有关于实际事物的经验知识的话,那它就应该被扔到烈火里去。也就是说,他似乎否认外乎此两种认识方法的可能性。那么对于宇宙的神秘性,是否可能有什么新的认识办法呢?休谟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理性在探讨这些崇高的神秘之事时,由此觉察到自己的鲁莽。于是,离开那个充满晦涩和困惑之地,谦虚地返回到它的真正而恰当的领域,即对日常生活进行考察。在这里,它将发现足够它进行研究的各种难题,而不必驶入一个充满疑惑、不确定和矛盾的汪洋大海。如果理性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太幸运了。” [英]休谟:《人类理智研究 道德原理研究》,周晓亮译,沈阳出版社,2001年,第97~98页。这段话里透露的信息其实就是后来在康德那里明确指出的知性能力的有限性,所以才要批判理论理性的纯粹性,也就是说人类的知性能力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本体界,试图用它去思考本体界的事情,就是“鲁莽”地闯入了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那个充满晦涩和困惑”的地方。如前所论,其实具体的因果关系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涉及到“实在”本身,而这属于本体界的领域,就人的知性能力而言,具体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实属其能力之外。在此意義上,世界就是神秘的。故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就不是经验现象上的认识,而是本体认识的一方面。休谟通过对因果关系的思考已经从负面指出我们的“理性”不能鲁莽地驰入其无能为力的本体界,只可承认归纳和演绎两种认识方法;但从正面来看,我们能不能拥有认识本体的认识能力和方式呢?康德虽然指出实践理性的纯粹性,可在他那里作为实践理性可能的根据的“意志自由”只是理论上必须的设准,至于人能不能实际地拥有这样的“意志自由”,康德认为这是“实践哲学的极限”,而把它悬置起来。如此,则关于本体的认识说到底还是空谈。而关于本体的认识的可能根据和方法路径等问题的思考恰恰是中国哲学的胜场。吸收中国哲学的智慧,或是回答休谟问题,为科学奠基,洞彻现象认识根源的出路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责任编辑:无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