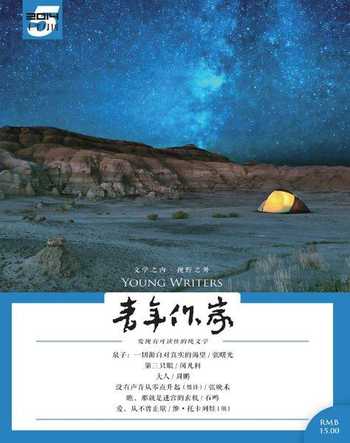瞧,那就是迷宫的玄机
多年以后,当我们在忙碌或慵懒中听闻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幸辞世的消息,准会想起青春年少时初读《百年孤独》的那种兴奋和悸动。当时,社会刚刚走出长久的混乱和封闭,我们对西方的一切经典都如饥似渴。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引进,几乎每一部都能引起我们极大的阅读热情,而在范围之广、持续之久上最能体现出这种热情的烈浓度的,无疑就是《百年孤独》了。它扑面而来,让我们看见了另一片风景。我们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另一块土地上,文学之花竟然开出如此绮丽瑰幻的花朵。我们仿佛被它指引着看见了一片新大陆,它调整了我们注视世界的目光,让我们知道这世界没有所谓的唯一的中心。
我在这里用了“我们”这个复数词而不是“我”这个单数词,是因为这种记忆和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我们那个时代(1980年代)所有作家、文学青年和很多非文学青年的一种集体记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刻骨铭心地记得,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是一个理想的成长有着丰饶土地的年代,新知识、新视野、新思维自由地来到我们面前,在我们面前展开,让我们去接受、去亲近、去热爱、去进入。世界的阔大是早就存在的,但我们却似乎是那时才突然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不免感到着急,不免出现一丝慌乱。不过,也正是这种着急和慌乱,激励了无数人去借鉴、去创新、去追赶。
那个时代是能让一切经典放大的时代,以西班牙语初版于1967年的《百年孤独》没有更早而是在19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也可谓恰逢其时。这不仅因为我们拥有巨大的热情,更主要的是,经过此前几年的人文启蒙,我们已培养出了一些思考的心性。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在当时的中国成为了一种现象,它所触发的思考,最主要的也许还不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一个穷困小国的作家能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是这个作家为什么能以其描写拉丁美洲苦难历史的作品征服全世界的读者。他是怎么写的?他是怎样进入拉丁美洲的历史与现实的?我们也能以扎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作品征服全世界吗?如此等等,我们开始自问。于是,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百年孤独》的影响至少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有了积极的体现,它不仅诱发了诸多优秀作品的诞生,甚至一度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文学创作的生态景观。当然,不可否认,一个不良的现象或心态也同时在滋生:既然一个旮旯小国的作家都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一个泱泱大国的作家为什么不能?这种滋生于偏见和自大的心态不仅扭曲了一些作家的写作,说不定也是中国文坛三十多年来浓重的诺贝尔情结的源头。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作家分为两类:写作的作家和不写作的作家。”显然,他本人正是一位写作的作家。除了政治原因而封笔数年,他一生的时光都在写作中度过,在写作中享受着孤独,直到上帝带他远行。生命的形态有时往往又那么奇妙,它不会一成不变地仅仅依靠物质的存在而求证生命的存在,相反,在很多时候,它更能以精神性的存在跨跃物质的束缚而让存在具有恒久的时间属性。作家的创造力和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一种存在,马尔克斯用他的创作、用他对世界审视的目光,让他的生命拥有了恒久的时间属性。
我一直在用“我们”这个词,下面,我开始用“我”这个词。
我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接触和认识比很多人晚一些。我读到的他的第一本书自然也是《百年孤独》,时间却不是该书刚出版的风靡之时,而是一年多之后。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其一是不知道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其二是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正风靡,其三是我手头没有这本书,而我们当地的图书馆里,似乎也没有这本书。我是高三时在我一个同学家里发现这本书的。于是,一段时间里,在同学们埋头背历史、背政治、背地理、背英语单词一心一意迎接高考的时候,我时不时地开小差跟着奥雷连诺冒险,在叙事的密林中穿行。现在我手头拥有的这本1984年十月文艺出版社版的《百年孤独》,扉页、书名页和人物表页,每一页都盖了一个红红的章,同一个印章,刻“周天军”三字。是的,这本书是我的高中同学周天军的,是他送给了我,还是我借了后未曾归还,多年前就已记不清了。现在,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周天军同学万一看见了这篇文字,不要来把这本书要回去。虽然我现在并不缺一本《百年孤独》。新经典文化经过艰难谈判终于成功引进《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书的版权后,我一一重买了这些获得作家本人正式授权的著作,以示对作家和著作权的尊重。亲爱的加西亚,我们现在不会再未经授权就擅自盗印了,请你原谅我们曾经的鲁莽。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完整地看完《百年孤独》。在还剩下几页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个“百年里诞生的所有的布恩亚当中唯一由于爱情而受胎的婴儿”(新版译:布恩迪亚家族中“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在爱情中孕育的生命”)呱呱坠地的时候,我让自己的阅读停了下来。这源于我一个固执而可笑的想法,那就是对一些有意味的作品,我不希望一次就结束阅读,而拉长阅读最好的方式,就是留下几页,等待将来的某个时刻来最后完成。这个带着爱情基因呱呱坠地的新生婴儿却长着一条猪尾巴,他会为故事带来变数吗?现在,我想我应该阅读最后几页了。
《百年孤独》被称作是“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于是它风靡之时,“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也突然有了某种亲切感。想去想来,那也是文化断了代的缘故。或者说,是我们一九四九年以后将丰富的传统文化阉割,并将其粗暴、简单地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因为这个人神鬼共在的奇妙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讲本不应该陌生。我素喜前人的志怪笔记,所以《百年孤独》中见到血可以自动行走、俏姑娘在收床单时突然飘上了天、婴儿长猪尾巴之类的奇景,倒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小时候听到的一些鬼怪故事里,这些也是经常发生的。我惊讶的是,这个可爱的哥伦比亚人把这一切变成了日常,从而铺展开了现实的另一个维度。一个能勾引出我们的文化回忆、连接上我们并不十分久远的文化传统的维度。是啊,你看,在中国古代,人们不是也把这些都看作是日常吗?所以莫言说他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发而回归中国民间传统,正是对这一现象的一个总结。有时候想想看觉得真有意思,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一个拉丁美洲人启发我们连接上了传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回归总是需要外力的刺激呢?
我手头另一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其实也是强从一位亲戚家征来的。这本书我自己买过一本,但后来不知被谁借去了未还(我也因此立下一条规矩:好书概不外借),再买又不可得,心中一直怅然。某一日去亲戚家偶然看见,心中大喜,于是据为了己有。真不道德。
《霍乱时期的爱情》被誉为写尽了爱情的各种形态,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杰作。而我对它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么一件事。数年前的一天,一位女性朋友问我有没有什么书推荐给她看看,于是我推荐了《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个星期后我们见面,我问她看完没有,觉得怎么样,她把书从沙发角落抓起来扔给我说,这个混账男人简直是虚伪透顶,他和几百个女人上床,居然还有脸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撒谎说他为她保持了童贞。你们男人就是这样,动物!她一激动,顺带着就把所有的男人这样骂了一句。
我立刻就明白,激怒了她的,是弗洛伦蒂诺?阿里沙的这句话:“那是因为我为你保持了童身。”这是漓江版的翻译,出现在该书第365页。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9月新版的翻译是这样的:“那是因为我为你保留了童贞。”我觉得这翻译更好。这句话是弗洛伦蒂诺?阿里沙经历了漫长的爱情等待后和费尔明娜?达萨躺在一起时,当费尔明娜貌似随口地说出她从未听说过他有女人时,他“立即连声音也不变”(新版翻译为:“她以一种随意的方式提及此事,而他立刻做出了回答,声音中没有一丝颤抖”)地回答费尔明娜的话。这句话回答得坚定、果断、胸有成竹,毫不迟疑,毫不拖泥带水。我想,正是他的这种回答态度,激怒了我的女性朋友。
她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站在她一个女人对爱情充满纯情憧憬的角度来看,她确实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浑球,因为他实实在在记录在案地和那么多的女人上了床,而且还导致了其中一位姑娘的自杀。我想,如果他的回答是迟疑的、掩饰的,也许我那位朋友还会稍稍原谅他,因为女人有时候往往会心软地原谅男人迫不得已的撒谎。但在这里,她没有看到迫不得已,没有看到内疚,因为他的回答毫不迟疑,好像他从来就没有和任何一个女人上过床。我的朋友彼时正处于憧憬爱情的甜蜜时期,对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这件事有意思的是,她的气愤其实正好触及到了一系列爱情形态的关键词:爱情、肉欲、精神、肉体、忠贞、背叛、忠诚、虚伪、诚实、撒谎……每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期待都不同,所以站在各自的角度和立场看,这些词放在弗洛伦蒂诺身上都是准确的。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爱情最真实的形态又是怎样的呢?费尔明娜相信她最后迎接的就是真正的爱情吗?如此等等的疑问,与其说是对小说故事和人物的追问,不如说是对我们自身境况的追问。所以《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揭示出了爱情的所有形态,还在于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身与心是否可以分离?灵与肉是否可以划开?忠贞与背叛如何界定?道德评判和爱情评判如何协调?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最终触及到爱情最真实的核心。
我后来才知道,我的这位女性朋友没有看完全书,她的阅读止于弗洛伦蒂诺?阿里沙的那句话。我为她感到遗憾,因为她错过了最后部分爱情那动人心魄的力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情感的愤怒有时会让我们无法看见爱情最真实的形态。所以恋爱的人儿,一定不要被愤怒遮蔽了双目。
《迷宫中的将军》是我们谈论得比较少的一部作品,究其原因,也许在于它是非虚构作品,而作为一部人物传记,加西亚?马尔克斯不避尊者讳地写了一个赤裸裸、未被衣服遮饰的玻利瓦尔,不太符合我们书写英雄人物尤其是革命英雄的习惯,因而被我们的研究者选择性地忽略;也许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理想的失血,在于近年来人们不再对理想主义充满热情,因此对一个耽于理想的孤独者,也就缺乏了投注关切的热情。我也许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将原因归之为后者。《迷宫中的将军》完成出版于1989年,当年就被翻译成汉语带给了我们(感谢敬爱的译者,很遗憾我没有记住你的名字)。我尤记得1989年我刚刚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在院子里的一个葡萄架下,我穿着松松垮垮的汗衫,窝在一把竹编躺椅上看着玻利瓦尔梦呓般的絮叨,竟感受到一丝凉意侵袭。这位可怜又可敬的将军视死亡为无可挽救的职业冒险,一心想着整个美洲的自由与统一,在理想的燃烧中亢奋,又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饱受熬煎。他坚定而无私地为美洲而战,却又忧伤地坚信将来必定会穷愁潦倒、赤身裸体地死在自己的床上,而且得不到民众的谅解。他的孤独让人心碎。《迷宫中的将军》以玻利瓦尔黯然神伤地躺在浴缸中开始(这个古怪的将军每天都要洗澡),弥漫的草药味儿一开篇就让空气显得滞重。在每一部作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都对开篇的第一句话极为重视,有时光是推敲这第一句话,就得耗上几个月的时间。我很想把这开篇在此刻重读一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想这部作品刊登在1989年的《世界文学》上(感谢《世界文学》,多年来它一直刊登着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但令人失望的是,我找遍了书架,也没有找到这本书。二十多年来,我搬过几次家,这本书难道在某次搬家过程中不小心遗失了?我很不甘心。我希望有一天它能突然在书房里冒出来。
我以仿写《百年孤独》开篇的方式展开这篇文字,以此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敬,也以此纪念一个伟大作家的溘然长逝。这个有名的句式曾经被粗率地仿写,散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量作品中。于是,就像美食被滥派,锦衣被乱裹,好东西终于被我们败坏了。《百年孤独》的开篇是一个简单的句子,却有一份让人惊异的魔力,它让我们知道,作家可以跳出线性时间的限制而让叙事同时洞悉时间和命运的奥秘。他可以同时在现在看到未来,并在未来看到过去,他是孤立的时间,也是所有的时间。他能洞悉众生的命运,也知道命运的轨迹,他将这一切为我们呈现出来。这世界为我们建造了迷宫,却不曾为我们演示通行的路径,而在交错的迷宫中,总有一些伟大的作家,可以通灵般地触摸到迷宫的玄机。加西亚?马尔克斯正是这样一位通灵者。
4月18日上午,加西亚?马尔克斯因病去世的消息通过网络传来时,我正在准备第二天下午的一个音乐分享讲座。要在古典音乐海量的曲目和版本中选择既有代表性又能控制住讲座时间的音乐颇为耗时,我在众多的唱片中选选停停,不时在唱机上放上一小段。也就是在播放其中一小段音乐的时候,我打开手机订阅的腾讯新闻,看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幸离世的消息。消息附了一张加西亚?马尔克斯1989年4月15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哥伦比亚人穿一件松大休闲的白衬衫,衬衫左边的口袋,放着眼镜,夹着一支钢笔,右边的口袋,放着一本书。老人向右凝视着远方,浓黑眉毛下的双目充满坚定,却又透出几分忧虑。他双唇微启,似乎在述说什么,又似乎在感叹什么。我看着手边的唱片,突然想放一段音乐,为老人送行。我选了肖邦《降B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葬礼进行曲》。这首寄托哀思的音乐我有多个版本,柯尔托、巴克豪斯、鲁宾斯坦、阿格丽希、阿希肯纳吉、伯格雷里奇、奥尔加?科恩,风格各异。我选择了奥尔加?科恩,和柯尔托、巴克豪斯等演奏弥漫着浓重的英雄主义的悲壮不同,奥尔加的演奏在悲伤中更多地流露出类似于亲情与友情温暖的抒情性,我觉得这正适合加西亚老人,因为他不需要过度浓重的悲伤。音乐响起来,就像加西亚老人会在小说中描述的那样,一个个音符一个个乐句汇成了溪流,缓缓地向远方流去。在溪流途经的路上,我仿佛看到一位银发老人在迷宫中前行,戴着黑框眼镜,抽着烟,突然在前方停下来注视着远方,然后狡黠地回眸一笑,仿佛在说,瞧,那就是迷宫的玄机。
[作者简介] 石鸣,祖籍广东佛山,生于四川绵竹,现居成都。文字和摄影作品见于多种书刊,著有《现实与抒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