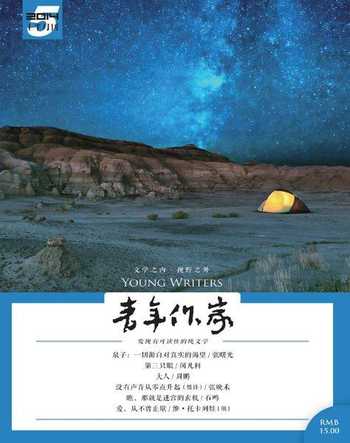逍遥游(组诗)
[耽爱]
有些事物似乎注定与春天无关:铁
喜欢生锈。四月到来时,路边的针叶林
醉心于唱响挽歌。背对大道和喧嚣,
他耽于躺在微风吹拂的岸边,
透过铁丝网护栏的方孔,向河那边了望:
倒影里,金字塔形建筑的间距和轮廓
开始露出犬牙和锯齿。
紫薇园码头河堤下,潮水退下一个梯级
一只白鹭趁虚落足,在此陷入冥想。
它的翼展和俯视下,低沉的天空
在河面铺开画卷:空阔,深入,晴转多云……
6:4:3,一场低烧以这样的音步在持续。汽车偶尔驶过,在杯子里惊起涟漪。
他清楚地感受到,一丝震动
来自东门大桥略显松弛的腰身。
杯中雾霭袅袅,一声不易察觉的叹息,
让身后的蕨类植物颤如笛膜。
仿佛某个有风的黄昏,一位盲乞丐
从桥上走过时,曾这样将它吹奏。
从他梦魇般深陷的眼窝里,
他瞥见令毕达哥拉斯狂醉且惊骇的真理:世界之本质即零。
死囚临刑前必经的旅途上,风声和苇叶
弹奏着他们千百年来的呢喃和微笑。
流水日夜砥砺,这弓形河岸
是怎样的力使它如此弯曲、平静,
如言归于好的情侣。
雾状时间消弭一切:柱石上的凿痕,
虫洞,剪刀差和海伦的木马玩具。
一页晚报盖在他脸上,那上面的新闻
让晨跑者的目光在陌生人墓碑前停留:
醉驾、车祸,追上来的另一辆重卡让围观者倒下。
他耽于旁观,但无法理解:
怎么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奇数和偶数结合的漩涡?
[如是我闻]
黑色枝条在窗外延伸。一只尺蠼
悄悄开始了它一天中的必修课:练习瑜伽
或顶礼。时辰到了,一件寻常的事
让他吃了一惊:指间滑落的挂面
在沸腾的锅沿旋转、散开
倾斜着排成一个有着神秘韵律的数列
恍若遥远海岸古老神庙的廊柱的阴影……下夜班路上,高速旋转的轮毂上崩脱的辐条坠地前就迈着这样的舞步
他为此着迷,并暗自惊叹:
“噫!这暗藏的美和真理
我曾在哪里见过,并将其拥入怀中?”
镜中微笑重现,如同灰尘叹息的地下室他陷入沉思,浑身沾满被囚禁的痕迹
热气在眼睑和印绶纹深处升腾,弥漫
将他的脸和整个身体吞没,消失
在暮色里,一条轨道徐徐弯曲
时辰到了。它伸向远方的双臂张开又合拢薄雾中温柔的弧度
为他摆下一个有关生命的谜语……
他为此着迷,并暗自惊叹:
“噫!这暗藏的美和真理
我曾在哪里见过,并将其拥入怀中?”
透过衣裳的纹理,凉意沁入肌肤
一滴墨落下,在纸页背面构成或然的曲线
记忆的旷野上,他是一棵失去了故乡的树
时辰到了。风吹过铁栅栏和年轮
那些蜂巢状的庭院、石桥和世代绵延的生活被压缩在一个楔形中,为谁替罪?
河面倒影里,另一个城市被折叠,搓碎
又恢复原状,这过程无限循环
仿佛一个时间的诅咒,在眼前重复……
他为此着迷,并暗自惊叹:
“噫!这暗藏的美和真理
我曾在哪里见过,并将其拥入怀中?”
[逍遥游]
樗树枝条末端的黄昏,一个理想国闪着静物的光辉。
仰望和冥想,为他找到打开并不存在的大门的钥匙。
收拢,张开,透明触须布满吸盘和刻度。
任时间的微粒之流倏忽闪过,记忆留下空白。微弱的鼻息里,墓地和城池渐次擦亮人间灯火。亚麻布衣裳隔着一条黑暗河流。
身上的暖意和雷声,远远的
如萤火虫,或者少女盛满罂粟的血唇,
试图吻他盛放在长条椅上的块茎似的头颅。
如果红砂岩的孔隙蓄积了足够多的潮湿,
黏液质的冬天叙事曲,就将在沉默中转向、分岔。
基因决定命运。他的臭皮囊
已经覆盖了云母和蜥蜴的彩色鳞片。
似乎可以让他一直坚持到阿拉法特。
苔藓在脚下任意铺展,超过了柏拉图的虚荣心。还在冬眠中,它们就开始篡改版图,
这伟大的繁衍和征服,
将止于一个旁观者周游列国的足迹。
站立,行走,眺望……身体打开一把折刀,
开阖渐趋吃力,偶尔折出的火花或楔形文字,头发花白的伪币铸造者,他的豁齿读不出其中的钝痛。
花瓣掠过鼻翼。想起某年某月某一天
一张火车票穿过剪票钳,带他踏上陌生旅程。风吹皱面庞,而思想的血槽更深,更隐忍。
当光跃入水面的一刹那,世界暗了下来。
就算是盲人,也感到有一种速度已经放慢步伐。一块冰凉岩石梦见他。
问题是他能否坚持到阿拉法特。
直到最后找到它,将其推上山顶,并唤醒,
刻下:1970年X月X日—20XX年X月X日,XX到此一游。
注:阿拉法特,山名。位于沙特阿拉伯麦加以东40公里处。山下平原约7公里宽,13公里长,亦名阿拉法特平原。阿拉伯语“阿拉法特”(Arafat)含“相认”之意。
[冬至]
——献给青白江。赠胡仁泽、李龙炳。
亲近就是亵渎!或许一开始就应该放弃
以宏大叙事的口吻铺开你的画卷。
当北风和计划体制重新逼近身后,
祈祷唤醒记忆的合页:
鸟语林、毗河、烈酒、桃枝低垂。
车辆匆匆来去,将岸上陌生人
带往下一个现场。遁世者面前
盖碗茶冒着往日的雾气。它们胎体单薄,如何挽留住一个时代的体温?
老人们的牌局,在鸟爪上组合、变换,暗示一个王朝已经捣不出新意:
淡薄的文身和账簿,
在开场白中,说书人已经不屑于提起。
烟囱还在向天空倾诉心事。高压线
穿过女孩的梦境,在她的月亮和翅膀上
缠绕成一个蝮蛇结,等待谁
为它系上一枚象牙鸽哨。
笔误出脱的偏旁,丢弃在哪个火车站?
一条名叫青白江的河流,还在星空下仰望。城厢镇的旧戏楼早就空了,躬身穿过时
他们仍满怀敬畏。谁的唱腔和水袖
还在地方志线装的纸页间萦绕。
孔雀石的裂纹铺向曼陀罗的根须。
油菜地为天幕涂上一抹明艳。筛沙机器
停止了轰鸣。公路桥短暂失忆
一片红色丘陵,将红树村的酿酒作坊
悄悄隐藏。八阵图的杀气
被车辙和弥牟河的泥沙带走。家珍公园
一道红墙将柳色、蝉鸣与市井隔开。
耍蛇俑脸上,暧昧的微笑
还在玩味人生三昧。
在绣川书院夤夜长谈,他听到
冬至的步伐,在一条鱼的尾鳍末端凝结,消失于绣川河的波澜。
浮沉于永逝之激流,动脉中
血还在衔枚疾行,暖暖的,不曾封冻。
翠鸟的身体里,碳元素和羊叉河相互替代。一间陋室,他曾有缘进入。
迷惘的画架上,受潮的风景
沿一排红砖楼和倒影杂乱叠现。
那个迷幻的夏天,他一路向南。
踏过生门和死门,来到长满白杨的平原,
沿卦象指点的方位,却没有找到
占卜者许诺给他的命运。空气中
充满铁的燃烧,重力牵着湖江河的鼻子。天空下,高压线展开的黑色曲谱,
只有北风懂得阅读,并日夜弹奏。
他知道,到了冬天
一个男人应该学会沉默,
竖起衣领,继续走那没有走完的路。
[作者简介] 胡马,男,汉族。生于1970年3月。爱喝茶,爱旅行。有小说、诗歌、随笔等在《四川文学》《青年作家》《诗歌报月刊》《中国诗歌》《诗选刊》《诗林》《星星》诗刊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