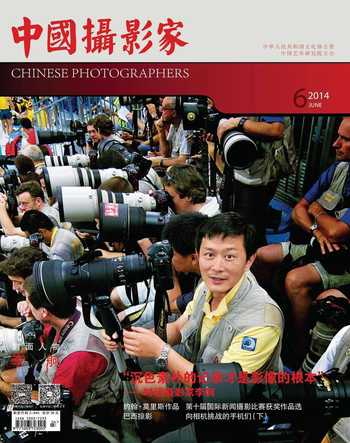中国摄影在当代的文化自觉
孙慨
中国摄影在当代的文化自觉,来源于三种意识支配下的行走路径。一是20世纪80年代面对国门打开后西方摄影文化的东进浸染,国内摄影界以积极姿态主动吸纳的开放意识,其中源于内部的反省和来自外部的启蒙彼此促进,相得益彰;二是经由中西比较,在现实与历史的对望中,确立并建设本国、本民族摄影文化精神内核的主体意识;三是基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与变化的大背景,对中西摄影文化中的思想资源予以重新审视、择拣取舍、创新改造的批判意识。
觉醒在当代
1970年代末以来的30余年间,中国摄影置身于全球化、景观社会和新技术、消费时代等背景下,经历着政治、经济、科学与技术、观念和文化、现实与传统的力量交织,呈现出繁复多样的形态。从“四五纪事”1到“四月影会”2,及其以“自然·社会·人”之名举办的三届摄影展,摄影不仅提出了在图像语言上实施新探索的可能性,也开始触碰尖锐的社会问题;随后出现的北京“裂变”、上海“北河盟”等以地域为特征的摄影群体,则从新闻摄影与现代主义摄影这两个方向,表现出可贵的自觉与独立意识。
思想启蒙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1980年代国门打开后,西方摄影文化在华交流传播的密集和深入。从“北京国际摄影周”3的举办,到“荷赛”作品的亮相,以及《世界新闻摄影展览》等一批高水准影展的引进,包括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编著的西方摄影大师的书籍在大陆的出版,掀起久久不能平息的涟漪。视界打开引爆的直接效果是观念的突破与更新,一大批资深的中国摄影人开始走出井底,重新审视过往十余年乃至数十年业界前辈引以为圭臬的宣传摄影模式及其价值观。那种讲求唯美、高调和积极向上,报喜不报忧,以及将忠于摄影的“艺术性”与忠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巧妙结合,图像来源于现实却高于甚或远离现实、貌似美化其实已经异化的摄影图像,开始受到反省;弃旧图新的激情与勇气,也随之释放。
而纪实摄影,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缓步登场的新潮运动。它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苏醒,又经过了整个1980年代的萌芽、生长,终于在1990年代中后期形成规模,成为中国当代摄影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既是对1949年之后新闻与摄影规范中一系列禁忌的突破,更是摄影的本质属性在中国的回归。围绕着这一“运动”从理论到实践、从影像形态到传播方式的变革,以及各种观点的表达、观念的流布,其中既有国家政治日渐清朗、社会生活日益正常化这一时代背景所提供的探索土壤,又有国外摄影机构、团体和摄影师群体施加于中国摄影的示范性影响—自觉,其实也是多种条件契合下的省悟。摄影评论家李楠对这一代摄影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的精神之旅和影像实践,以“影响”的角度做了一一对应的研究。尤金·史密斯的《母亲为智子洗浴》让杨延康意识到苦难之于人类的普遍性,而他的《藏传佛教》和《中国乡村天主教》等系列,又无不由此理念出发。邂逅了奥古斯都·桑德的《时代的面孔》后,姜健获得了《主人》的启示。秦军校以《中国妇女缠足考》《婚俗与丧俗》“为后人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的信念,来源于文献摄影的鼻主爱德华·S·柯蒂斯的《北美印第安人》。影响所及又并非简单的直接对应,许多摄影师是在消化、吸纳西方和前辈摄影大师风格理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现实而进行的自然转化。尤金·史密斯的《走向光明》和罗丹的《艺术论》让王瑶从中获得了关于摄影的持久激励。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对美国社会风俗化历史的细致描绘,激发了张新民对《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标本—流坑》等专题的灵感,为中国社会存留了一份可贵的视觉样本。4与1949年后开始从业摄影的老一辈同行所不同的是,体制的严苛束缚松了,他们比前辈获得了更多在艺术思想、摄影实践上的相对自由。
摄影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身份、艺术角色和传媒特征的回归,无异于一场影像观念的革命。
在1990年代,超越于现实或者说表象现实之上,着重于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影像批判,以实验摄影这一新的摄影形态,在中国出现。它借助于美术的经验与方法,与当年郎静山等先驱的美术摄影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然而在图像旨趣和核心价值追求上,二者又有天壤之别—求美与求真之别。其特征“一是实验摄影与中国社会转型及艺术家不断变化的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二是中国实验摄影与后现代理论、概念艺术以及行为、装置艺术等当代艺术形式间的互动。”5刘铮将模特、蜡像和演出场景之类真假场景与对象的故意混淆,实现历史叙事与现实表现的融合,塑造出在时间上贯通记忆的艺术形象。海波的系列集体照片,通过时空的新旧对比,将个人的伤痕巧妙放置于国家命运的宏大波澜里,体现了图像的细节诠释和对于大众整体命运的沉思。这种真,显然比客观新闻的真,更接近于本质意义上的图像之真。
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当代中国摄影家在立足本土精神资源上所作的又一种开拓性实践—从文学、美术等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中探寻影像艺术的精髓,从历史遗存的视觉元素中搜索摄影在当代的意见表达,从家族式的影像遗存中追求可以印刻进国人灵魂的图像文本及其特征,或者只是从中获得其对于当代中国摄影在表达方式和价值铸造上的艺术灵感。塔可的《诗山河考》,则完全以影像的方式,在相隔3000余年的时空中再现了《诗经》的魅力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针对性。
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观念启蒙,在当代中国的正面影响力还在于:摄影师的自由意志激发了摄影主体意识的萌生,禁忌的放宽也使摄影的本质功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释放。作为图像阅读者的公众,人们看到了突破地理空间限制的丰富世界,人们可以走进更多陌生人的心灵并与之共同感受苦乐爱恨;人们见证了国家的巨变与挫折,荣光和艰辛;在不知不觉中,中国人通过照片,已经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与国家命运的休戚相关—视觉关乎心灵。国人的常识,在视野的开阔和视觉的震撼中得到恢复。
觉醒之后
政治和社会空气的逐渐宽松,激发了摄影从艺术载体到传播媒介这两种身份的先天活力;在当代,中国摄影因内在的本性诉求和外在的观念触动,渐渐呈现出独立的民间意识和公众立场。极端年代里那种非左即右、极度贬损或极度拔高甚至舆论一律的摄影图像生产与传播的理念,渐渐遭致排斥;拍摄人的情感和不同群体生存处境的照片,不再只是专业人士和媒体记者的职责,许多以艺术家或者平民身份出现的摄影师,开始运用相机记录现实的中国—摄影在当代中国发生的这种变革,根源于传播理念与摄影价值观之变。1986年4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十年一瞬间》摄影展,可谓于自我批判中体现自信的典型案例。它将摄影记录的功能诉求明朗化,全面展示了文革后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李晓斌的《上访者》、潘科与侯登科的《出征》等作品成为中国摄影观念转折的导火索,在很长时期里影响了中国摄影人的题材选择和技法更新;而1988年举办的《艰巨历程》大型摄影展,则“标志着中国的摄影终于规模性的以一种自觉的人文意识与历史和社会对话了。”6
摄影者在职业、身份和更大程度的思想意志上,以思想自觉的自由人姿态介入公共空间、公众事务,尤其是针对一些社会矛盾、重大的国计民生问题作深入的摄影采访,或作长期的、有计划和系统的图像记录,直观的看是摄影技术革命带来的摄影民主,内在却与国家政治对信息与传媒渐趋开放、包容的姿态密切相关。雍和的上海,陈锦的成都,吴正中的青岛,赵利文的西安,一个个专注于某一地域或城市作“打井式”深入作业而形成个人摄影风格与特色的杰出摄影师,纷纷涌现;关注动荡和变革中的国家以及普通人身置其中的处境与状态,成为这些作品的要旨所在。变化明显的,还有媒体中的摄影;虽然程式化、模型化和符号化的新闻摄影在诸多党报中依然存在,但经由拍摄者、传播者重新思索并以新的视角予以阐释的报道摄影,正普遍地见诸于那些有追求的报刊版面之中。
值得关注的是媒体的市场化生存所催生的一批新锐媒体,通过对视觉语言的重新阐释,使其在诸多公共性主题的报道中,逐步摆脱了原先的“规定动作”,在大方向准确的前提下,遵循着摄影图像传播的规律,以“全球化视野、个性化彰显和人性化的观念”,体现出摄影的公众立场。人性化观念的体现,使新闻摄影“不再是政治观念为标准的判断,而是基于最共通的人类情感所作的选择。”“视觉语言上不断脱离宣传化和模式化,回归了新闻摄影的本质。”7令人瞩目的还有体制内一部分具有自觉意识和历史担当的新一代摄影记者群体,他们在前辈的传承与自身长期的摄影实践中,已经谙熟“新华体”、“党报模式”的规律,但已不甘于这种单一手法的运用。他们的摄影既有严格遵循明确的政治要求和宣传规范的部分,又有自我意识与摄影智慧充分彰显的另一部分;可敬的进步还在于:后一种风格的摄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坚持政治路线正确但不愿始终板着面孔的党报媒体中。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摄影民主,深层的影响,即为公众立场的产生。公众立场是一个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话语概念,与只是对一个国家、特定政党和一定时期的权力意志负责的政治立场相区别,公众立场以对最大多数人和社会公众以及历史负责为己任,它要求摄影者首先以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身份,在正视现实社会民众处境的基础上,从历史和人性的角度发现题材、提炼主题、营造图像,其作品含有深切的民间特质和大众情怀。公众图像在摄影层面的含义,是指建立在公众意志和公众利益基础上的摄影。以国际视角观察中国并向世界报道中国,起源于1990年代;曾璜在《报道摄影》中认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新华社就和美联社签订了新闻图片交换协议,《中国日报》和中新社向国外媒体供稿也有多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新华社、中新社和《中国日报》供稿的中国摄影记者也早已是国外新闻机构的供稿人了,这些摄影师拍摄的图片早已进入了国际图片市场。”8显然,在这些早已为国外图片机构供稿的摄影师的摄影理念中,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立场已不再是唯一的要求,而是一条底线,他们还需考虑国外图片机构的规约和要求;或者说,即便表达某一合乎本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也必须遵循供稿的国外摄影图片机构所制定的规范与标准—也可以说是世界新闻摄影界所共同尊崇的普遍标准。
在只能秉持政治立场的特定年代,享有拍摄权和拍摄机会的体制内摄影师,只能记录那些“应该”记录的景象,表达政治意志“希望”表达的思想;而公众立场是专注于现实世界本身、记录一切“可以”记录的现象,表达一切“能够”表达的思想—它较少受到自身智力和情感之外的力量以及各种利益组织的干扰,它依据拥有独立精神的个人营造一个自由自在的文化区域,它甚至具有修复政治破败的功能。但在国家意志上,批判意识和公众立场,正是一个国家的摄影在获得自我觉醒后,文化自信的表现。
随着中国摄影囿于自我设定的价值系统内部、自足自恋的漫长时期的结束,中西的交流日渐深入。杨绍明的《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在三十一届“荷赛”中获得新闻人物类三等奖,由此启动了中国摄影在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后对世界的重新向往。中国摄影开始深度融入世界,“荷赛”上的中国获奖者逐年增多,世界纪实摄影的“奥斯卡”大奖—尤金·史密斯奖,也被中国自由摄影师卢广获得;中国摄影在世界的影响力,日渐增强。
中国摄影的尊严与自信,在中西间的交流与融通中缓缓建立。
摄影文化与图像话语权
图像话语权的强弱,乃摄影文化兴衰中最显著的标志。
摄影价值观的创立是图像话语权获取的基础,只有建立起世人都能接受并自觉遵从的价值观,才能享有足够的图像话语权。而普世价值观的建立,首先必须建立起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图像价值评价体系。亦即:植根于多元文化以及历史传统中的摄影价值评价标准、评价体系以及价值生成的原则、规范等。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摒除自卑心理,兼容并包;唯其如此,中西方摄影在文化上的对话,才有可能。
中国摄影的实力增强,当从建设自己的摄影文化入手,让摄影术和摄影,切实地服务于国人的生活、教养以及个体人格的塑造、社会群体公民意识的培养—中国摄影应在有效传播本国文化的基础上,着力于构筑其自身独特的摄影文化系统。
文化,应是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行为和思想表达方式、审美情趣以及价值观的一种意识形态;偏重于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文化应当具备三个层次,“一为一个文化中成员的思考的方式;二为一个文化中成员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方式与形态;三为一个文化中成员对自然环境采取的解释与态度。”9钱穆先生认为,“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0承袭前贤思想,窃以为文化还包含着:个体的思考方式及其与所在群体的密切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及形态,群体对自然与社会环境采取的解释与态度。基于这样的认识,摄影文化的概念确定,理应偏重于摄影所依赖的固有文化土壤、社会习俗和政治制度,以及摄影意义的生产方式、传播特点和它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构建中的社会学分析。而摄影文化的涵义,至少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