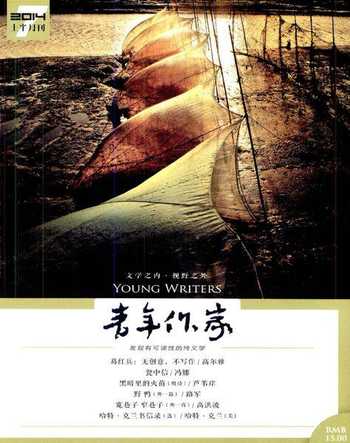野鸭(外一篇)
故乡那时候的水还真是不少,不说门前那条清冽的小溪,在沟沟叉叉间,拦了三座土坝,修了三座水库。西沟里的水库从来就没有干涸过,在我童年的波痕上始终清澈平静,荡漾着如美女眉宇之间的波痕,轻柔而优雅地依偎在小山的怀抱里。
野鸭子喜欢有水的地方,灵气因为水的滋润而鲜活。水有着聪明的大脑与神经,她喜欢绿色就像喜欢自己的生命一样。我不知道童年的雨水为何喜欢我的家乡,除了春天的干旱是一条解不开的死结,我童年的整个夏天都在溪水里洗濯。水润万物,万物膜拜水的灵秀。山鸡、野兔、狐狸、獾子等等来了,行走于山林与草木间。野鸭子也来了,徜徉于绿水行波之上。只是,最初的浪漫很快被贪婪所取代,一双双眼睛的美丽神色如天边的彩霞在太阳落山后立刻变得暗淡起来,像《西游记》里面的变脸妖怪。
最初我知道野鸭子始于野鸭蛋,未看到野鸭子之前。这有些滑稽,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混乱逻辑于我变得简单。一位叔叔来我家串门,在与我父亲东拉西扯后,语言贫乏感如荒漠忽然浮现了,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之后,忽然转过头笑眯眯望了我一眼,伸进裤兜旋即伸出,右手心里卧着一枚淡青色的跟鸡蛋个头差不多的蛋,在我的面前晃了晃,那是一枚鸭蛋带给我的美好印象。时间的车轮总要碾死掉在路途上的一些蚂蚁,在我的脑细胞死掉了一批后,对于这枚鸭蛋走向何处渐渐产生了疑问,我想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不知道是被我吃掉了,还是遗失在山岭之间的荒草丛中,因为我常常丢下书包跑到那里捉蚂蚱、逮蜻蜓、玩草编。
很快,我有了机会,敢于偷偷地背着母亲穿过一片诱人的果树地边际的大沟,大沟里的白杨树东一棵西一棵,歪着脑袋的,枝桠横生的,黑黑的喜鹊窝好像一摊牛拉屎摊成的圆鼓鼓的样子,在挺拔的杨树上来回摇晃。大孩子跟我说,沟里的水库有野鸭子,我想看一看它伏在草丛中下蛋的情景,草窝中的鸭蛋是不是淡青色,有没有好看的水纹,它到底啥模样?跟街巷中昂首挺胸像个作威作福将军派头的家鸭是不是一样。我装了一肚子的问题踩着林中的曲折小径朝前走,爬上一面斜斜的土坡,眼前忽然一亮,波光粼粼的水面如一面轻柔的面纱落在我的神情里。
我喘着粗气,和大孩子坐在水库护坡的一块石头上,眼神一次次在水面、沟塘的草丛中扫来扫去,还没有到中午,太阳不算毒,来凫水的孩子还在等待太阳爬上中天。水面上静悄悄的,只有沟塘中的风轻轻地拂过,一道道跳跃的波痕划过来、跳过去。焦急也被拉长了,平静被掏空。
就在我失望的情绪弥漫全身时,我和大孩子躺在树荫下的石头上凉爽一下滚烫的神经,天空中扑棱棱的声音划过,还有几声不算大的嘎嘎声。我忽地坐起,在天空中找寻,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鸟儿,然而,那枚野鸭蛋启动了我的思维,我一下子就知道这种鸟是野鸭子。我不敢乱动,大孩子也没有动,野鸭子贴着水面低飞,灰色的翅膀拉长了时空,它们平稳地落在水面上,挺拔的白杨遮挡了太阳,那一片树荫洒在野鸭子身上,野鸭子伸着脖子,荡起层层的波痕,朝不远处的水草里游去。留给我的只有瞬间的影像。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家乡的水面上见到野鸭子,后来,三个水库接连干涸,缺少了水的滋润,野鸭子就没有来过,不知道去哪儿了。
山上的草木越来越葱茏繁茂,只是雨水就像一位受了伤的乖戾孩子,脾气阴晴不定,有些年,雨水像勤于赶集的人,说来就来,堂堂不落,还有一些年,它躲在远远的地方不肯露面。家乡的最后一块湿地只残存在南沟里几家人合力修筑的一条坝塘,巴掌大的水面,数得清数目的水草,很显然,野鸭子不会来这里,连腿都伸不开的地方,思想的火花燃不起来。
我一直以为再见到它们只能有机会去湿地赶上运气好,或许能够见到。然而,在前年夏日的一个阴天上午,我来到居住的小城的橡胶坝散步,竟见到了两只野鸭子。我是无意中看到的,两只好像热恋中的样子,一只在前面用脚蹼使劲儿划水,双翅展开,昂首挺胸,另一只欢快地在后面跟着跑,好像我见过的一部电影中女孩在草地上跑,男孩子在后面潇洒地追着一样。跑了一会,他们安静下来,卧在水面上,挨在一起。
他们从哪里来的?秋天又将飞到哪里?种种疑惑困惑着我,我还想到了他们与我多年前在家乡水库中见到的野鸭子的关联,亲戚还是邻里?或者根本不相识,明年还会不会来到这里?
我希望他们不久后能够到我的家乡去,我相信,草木是繁衍湿地的母亲,一年年地积蓄能量,终会在某一个日子,山涧中会流淌出欢快的溪水,汇聚成碧波荡漾的水面,那时候,远在天边的野鸭子就会回来了。
[大黄蜂]
雾霾扩散似乎闲庭信步,昨天,我听说它已经穿越了大洋,来到了法兰西的国土,地球村显得臃肿而又狭小。粉尘颗粒很容易随一阵风四处飘摇。大黄蜂害怕雾霾吗?我不知道此时在山村的夜幕里,它是否能安静地沉睡下去,在风中轻易地醒来。
大黄蜂比蜜蜂心眼多是显而易见的,童年时,我们没少挨大黄蜂的毒刺蜇,蜜蜂很少蜇我们,它也常常在我们的眼前摇晃,可就是下不了手,一阵风似地飞向了远方的花丛中寻找花粉去了。大黄蜂不能,它的出身决定了它在这个世界上要比蜜蜂警觉得多、凶狠得多,丛林能繁衍出凶悍的种群,驯化和改良膨胀了不应该膨胀的组织,它只适合人的胃口,倘若解下它们身上的绳索,砸掉狭窄的各式各样的笼子,走向自然也就意味着走向死亡。大黄蜂从一降生就敏感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周围既是明朗的、纯净的,也是充满风雨和波折的。每一种自然界的生灵自省的速度不亚于飞行的速度与距离。
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挨大黄蜂蜇的情景。天儿空旷悠远,幽蓝幽蓝地放射出光,好像一早晨就用村庄前的潺潺溪流濯洗过一样。这是雨后不久的晴天。林子中蔓延着望不到尽头的野花,散乱如天空中眨眼睛的星星。在一丛丛的如女孩子刘海一样的蔓草丛里,蘑菇悄悄地长着个儿。远在几里外的孩子们已经嗅到了蘑菇的味道,最初跟在母亲身后去山里捡蘑菇的感觉不怎么优美,我曾不停地用小脚丫子追赶清晨的奔跑,还是没能撵上她的身影。
当我看到有一堆蘑菇隐藏在幽深的毛榛柴丛里,也就不顾及里面是否有三角脑袋的毒蛇还是潜伏在草丛里的马蛇子(蜥蜴之类的动物),就在我高兴地捧着蘑菇开心地想象,然后使劲儿地折着身边妨碍我通行的毛榛柴,一根根毛榛柴倒下去,如倒下的箭矢。忽然,我的头顶传来嗡嗡的声音,仿佛遥远的地方一架架飞机离开跑道跃上天空的声音,是蚊子吗?我还在想,一根毒刺已经狠狠地扎进我的脖子,瞬间的疼痛感好像水塘中忽然飞落的石头激起的水波,一圈圈飘漾开。我努力搜寻,看清头顶上一只只大黄蜂在盘旋飞舞,复仇的情绪如升腾的火焰,也顾不上自己的疼痛,拿起手中的镰刀乱砍。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愤怒的大黄蜂似乎不回避你的幼稚和凶狠,我的脸上蜇了一针。就在我即将陷入凶险的境地,有路过的大孩子朝我呼喊,”快蹲下,快蹲下,你找死呀!”我猛然醒悟,慌忙蹲伏在毛榛柴丛中,塑像一般一动也不敢动。我用余光瞄了瞄头上,大黄蜂在我的头上盘旋,像失去了目标似的嗡嗡叫着。安静反而成了最好的保护方式。
此后,我在大黄蜂的面前没有因此变得谦卑而小心,疮疤好了就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刺入心扉的疼痛,去野外,遇到它们建在树枝上、树洞里、山崖避雨处等等的大小不一的圆形蜂巢和飞舞的黄蜂,仍然敢动手,像其他孩子那样戳起一只木杆子或者燃起一捆不知谁家镰刀割下散乱摆在堤坝上的枯黄的山草,对着蜂巢和大黄蜂“围剿”。蜂巢掉下了,像滚翻落崖的圆车轮,在有限的空中翻滚。六棱形的蜂格内贮满了蜜。有几只大黄蜂在乱战中折断了翅膀,拖着身躯在沙地上打转,有人捏住肥胖的肚子拾起来,在阳光中,我看清了奇异的现象:它们的脖子后面竟清晰地印着横躺在地的“8”字。这符号到底什么意思不得而知,就像走到了一处迷宫,任我百思不得其解,问旁人,谁也不知道,还有人白了我一眼:问着有啥用?老祖宗就是这么种的呗!
而我已经陷入了这神奇的符号之中久久不能忘记。后来,我看见过“12”号山蜂子,比大黄蜂个头小而瘦,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山蜂子了,然而,那清晰的横躺着的数字之谜一直在叩问我的魂灵。或许,大黄蜂与自然界的种种生灵一样,在万千变化的世界中总有自己的隐秘,自己像风车随风转动的定律,从远古到现在,沿着一条路径行走,即使横亘在前面的有残杀和凶暴的戕害,只要不违背山林、草原、河流、野兽等等之间的平衡,那都没有什么关系。
可惜的是,我,许多小伙伴,我的长辈们,当贫困像瘟疫一样传染时,也就顾不了那么多,大黄蜂的毒刺再长,也阻挡不住一双双饥饿的眼神的掠夺。
[作者简介]路军,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作品在《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散文选刊》《延河》《山东文学》《北方作家》《岁月》《青海湖》《椰城》《华夏散文》《当代小说》《辽河》等刊发表。 作品曾获河北省第七届散文名作奖一等奖等多项奖励。散文集《光影流韵》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