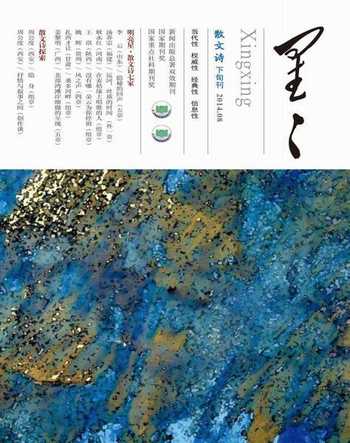月光干草(三章)
许岚
锄 头
锄头,和大地,黎明,黄昏一个颜色。和主人一条心。
锄头,不望天,只低头。在泥土里汲水,淬火,磨砺锋芒,韧性。春天华不华,秋天实不实,生活甜不甜,取决于锄头对土地爱得深不深。
庄稼面前,锄头比母亲柔,像伺候怀里的婴儿。野草面前,锄头比父亲狠,像铲除身上的毒瘤。
庄稼专说锄头的好话。野草专说锄头的坏话。
锄头从不在意。自个自弹唱一曲锄禾歌。
锄把再笔挺。在锄头面前,也得微微躬腰。锄头不喜欢假把式,一个萝卜一个坑。
使用锄头,得用巧力。手不能握得太紧,还要随时在掌心,吐一口唾沫。
大地一沉默。锄头,就陷入生活的僵局。
它靠锈迹斑斑的孤独,勉强在墙角站着,等着慢慢老去。
人死不能复生。锄头比人强。
如果幸运,被收废品的人回收,回一次炉,来生还可以做一个锄头。
秸 秆
五谷成熟前,秸秆是五谷的腰杆。五谷成熟后,秸秆被五谷彻底分家。五谷颗粒归仓,秸秆被放进土灶膛。
秸秆是位地道的乡村厨师,懂得如何把握火候,如何将五谷烹饪成舌尖上的美食。
秸秆最朴素的梦想是化作春泥,或做一粒饲料。秸秆也想做一张纸,画乡村的丰收。做一顶斗笠草帽,为人遮风挡雨。或借艺人的一双巧手,编织秸秆的梦想。
土灶膛一天天冰冷,秸秆也一天天矮下去。农人嫌它累赘,城市嫌它出身低下。秸秆无家可归。委屈与怨恨终于爆发了,它把天空烧成粥了,把人们的诅咒烧成灰了。
秸秆不会死,春风吹又生。
月光干草
月光。怕弄疼我的饥饿,打开每一只白皙之手,轻轻抚摸我呐喊的腹部。
干草。躺在干草中,眼巴巴地看着饥饿和孤独,啃噬我的饥饿和孤独。
它像一位即将枯萎的产妇。嘴唇嗑出血来,也挤不出一滴米浆了。躺在它的怀里,至少有一团温暖裹着我。
我并不怨恨干草,就像月光并不怨恨我。
月光是我牵着,从故乡从春天一路啜着青草来的。
这是1996年的一个深秋。在广州郊外的大朗砖厂,从大地上升起的夜,像个巨大的馒头,收容了我和月光。
还有一片漫无边际的干草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