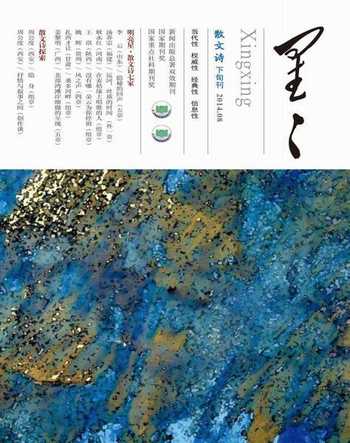新疆之书(三章)
支禄
骆 驼
多少荒凉灌进眼睛,才能成一峰骆驼。
多少寂寞灌进血肉,才能成一峰骆驼。
多少风沙灌进骨头,才能成一峰骆驼。
在夕阳烧红的天空下,一座座在燃烧的火焰中迁徙的城堡。
当雪崩和黑风暴一蹄又一蹄被死死地踏在脚下,骆驼才从风沙中扬起头。此刻,绵延起伏的群山在驼峰上颠簸苍凉和悲壮。
风起,一把羌笛在驼背上吹起塞上的云烟。
风落,一颗流星从骆驼的瞳孔飞快地滑向天边。
背着口粮和柴垛的骆驼;背着高高雪山和茫茫大漠的骆驼;背过传说和神话的骆驼……
让风的缰绳牵着,一步又一步丈量时光堆在脚下的千万里的黄沙。
骆驼的胃里把滚滚黄沙咀嚼成盐、草料。
骆驼的眼里是辽阔的地平线。
就是天下刀子,对于骆驼来说一旦踏上迢迢征途就不再回头。
一棵树
一棵树不仅装满了花朵和果实,还装满了风云和雷电。
一棵树不仅装满了命运和沧桑,还装满了泥土和河流。
正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当龙卷风如一匹马从沙丘上翻过去,带动电闪雷鸣,尖利的叫声如一把锋利的刀子,只听见“哗”地一声惨烈的吼叫。
龙卷风走后,我过去看到树梢像镰刀收割一样,横七竖八躺在沙地上,树皮爆破,渗出一绺一绺的白。
如刀劈开的裂缝间,我目睹了这一切。
从此,修改了一个人对树的简单看法。
当黑夜合上困倦的眼皮,我知道这棵树还没能合上爆裂的伤口。
屋漏偏逢连夜雨。
一场风沙又起来了,颗颗沙子钻入裂缝,对一棵树来说无疑伤口上撒了盐。
猛地,爬在窗口倾听的时候,我听到那棵树抽肠曳肚的呻吟。
在塔格拉玛干沙漠,还不知道有谁能抚慰一棵树的伤口。
鹰
鹰,长长的尖叫一声。
一把黑色的刀子,扔向天空。
一道长长的口子,顿时,雷鸣电闪,暴雨砸向那拉提河的两岸。
车行草原。雨雾连天。
鹰站立过的石头,如一只只白羊让浪涛赶进了河水;鹰站立过的树木,让风雨连根拔起,纷纷下水;鹰站立的山头,让雨雾死死地裹着。
而鹰,在哪?
在电光鞭子一样劈开云朵的那刻,我看清:
鹰,在风雨中,把翅膀练成剪刀。
鹰,在狂风中,把骨头飞成刀子。
鹰,在黑夜中,血肉河流样哗响。
一场暴风雨,就是天赐给鹰的磨刀石。
世间万物,雷电才配做鹰的磨刀石。
多少枯骨,锯末一样纷纷而下。
多少坏了的翎羽,麦草一样纷纷而下。
多少衰老的血肉,如水而去。
暴风雨中,鹰在提炼生命的精华,鹰用电闪雷鸣在不断完整自己。
鹰要用翅膀,飞出另一座灵魂的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