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
——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解读
★文/王 晶
生存还是毁灭?
——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解读
★文/王 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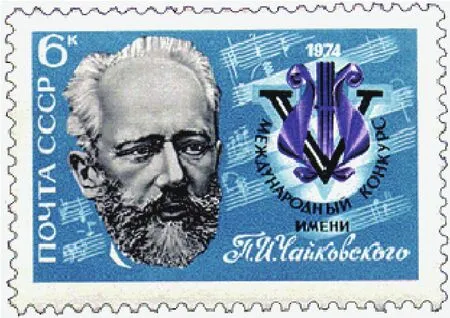
一
1877至1887年是柴科夫斯基“沉寂”的十年。自1878年构思并完成了《第四交响曲》之后,作曲家在十年内唯一的大型交响体裁作品只有标题交响曲《曼弗雷德》。十年时光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段不短的生命历程。从而立到不惑,十年光阴给柴科夫斯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1877年那场婚姻风波早已过去,那个无法定位自己,刚刚而立的作曲家早已消失了。十年间,柴科夫斯基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他似乎已经在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保持一段足够安全的距离。
然而,那阴森的精神危机依旧存在。这种危机一方面来自发疯的前妻米留科娃对他的骚扰,这会令他想起十年前的痛苦事件。更令他困扰的是,“死亡”之影开始浮现在他的生命之中:1881年穆索尔斯基去世,这位强力集团最具才华的作曲家只比柴科夫斯基年长一岁,却因酗酒过早丢掉了性命。接着是挚交维利诺夫斯基突然自杀身亡。然后在1887年,柴科夫斯基的外甥女达维多娃在一场舞会上突然暴毙,随后是好朋友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的病危……种种事件刺激着作曲家的神经,死亡的气氛在身边蔓延。在他写给梅克夫人的信中,柴科夫斯基沮丧地说道:“一种厌世的疲惫、沮丧和淡漠的情绪向我袭来,好像我就要死去……” 这种对“死亡”的感知影响着柴科夫斯基。1888年,已近“天命之年”的柴科夫斯基开始构思一部新的交响曲:《第五交响曲》——一部关于“生存”抑或“死亡”的交响曲。
二
《第五交响曲》的构思与另一部作品幻想序曲《哈姆雷特》基本同期。或许是受到了莎翁剧作中关于“命数”主题的影响。在《第五交响曲》中同样充满了关于“宿命”的诘问与思考。1888年8月14日写作完成, 随后于11月5日由作曲家本人指挥,在彼得堡进行了首演,一周后在莫斯科首演。
但这部作品的演出效果却未达到作曲家的预期,观众与乐团的反应都不甚积极,而最令作曲家感到难堪的则是来自居伊的评论。居伊撰文称:“柴科夫斯基在他的新交响曲里不是把音响当做手段,而是当做目的。”“圆舞曲这种形式总归还是狭隘的、轻佻的,把它放在交响曲里简直是大不敬……”居伊的评论在今天来看显然毫无理据,而且略显保守。然而敏感的柴科夫斯基还是受到了这种反面论调的干扰,他开始质疑自己的这部作品,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而自己已经江郎才尽。并随之陷入十足的沮丧。直到1889年在汉堡演出后,作曲家才开始重新正确评价这部作品。不过在作曲家生前,这部作品始终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尼基什在19世纪90年代将其重新诠释后,这部作品才获得世界的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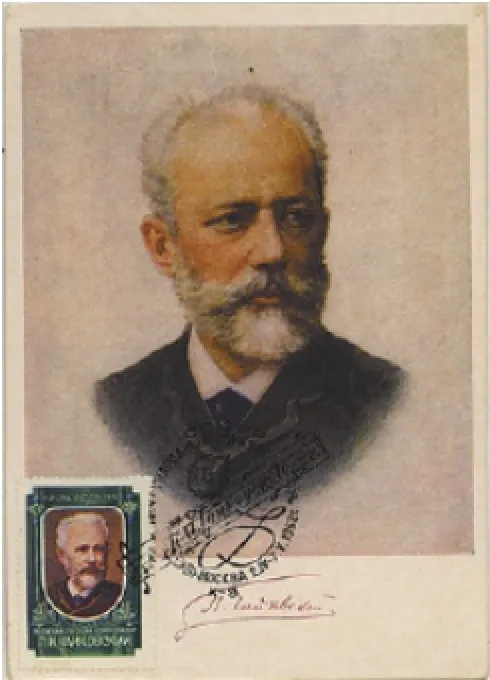
三
因为在《第五交响曲》创作期间,柴科夫斯基同时构思了幻想序曲《哈姆雷特》。因此关于两部作品之间关系的讨论也一直未曾停歇。在当时的笔记本中,研究者发现柴科夫斯基曾记录下一个为《哈姆雷特》构思的主题,这个主题后来成为《第五交响曲》贯穿全曲的引子主题。《哈姆雷特》因为篇幅限制,并未对戏剧本身的内容进行过多的描述,而是着力通过序曲描述哈姆雷特性格上的忧郁特性。因此,在《第五交响曲》这样一种更为宏大的体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曲家对莎翁戏剧中更深层次悲剧情怀的理解。哈姆雷特那句经典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配合当时作曲家的心境以及对“命数”的思考,幻化成《第五交响曲》的音乐结构和旋律主题展现出来。 《第五交响曲》延续了传统古典四乐章交响套曲结构。第一乐章采用带序奏引子的奏鸣曲式写作而成。其中引子主题是《第四交响曲》中引子“命运主题”的延续。这一主题的最明显特性在于其“葬礼进行曲”特质。自从贝多芬将“葬礼进行曲”引入大型套曲之后,这一体裁的标题性含义即变得十分明确。如果《第四交响曲》开篇的号角之音是一种外在的威胁之力,那么这一送葬主题显然“低调”、“内在”了许多。更类似一种“潜在的威胁”。同时在主题结构方面同样模仿了《第四交响曲》。这一动机可以分解成三个不同的截段,每个截段都成为后面各乐章主题形成的种子。因此全曲是对“死亡”的思考,首先在送葬的死亡音调中展开,随后死亡转化为各种形象呈现,并最终在第四乐章完整复现。“死亡”成为整部作品的贯穿性要素。”

按照柴科夫斯基的最初的构思,他曾为《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拟定了一些标题,其中序奏用于表现“对命运或上帝铁律的无上崇敬”。而第一乐章的两个主题分别是“怀疑、怨诉、谴责”、“能否投身到理想的怀抱?”主部主题明显与引子主题存在性格上的联系。主题内部借由细小连线营造出的旋律细碎感则赋予这一旋律惊慌、敏感的个性。因此,这一主题与《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题类似,并不具备典型主部主题那种明确意义的特性。同时这种写法也与《哈姆雷特》中的主部主题相仿,着力刻画一种忧郁与矛盾。这一主题的核心内容正是对引子主题中那“威严命数”的质疑与逃离。

呈示部主部主题在逃离与质疑的过程中不断被单音重复的命运锤击插入。不过这种压力在连接部中逐渐消散,副部主题以一种相对缓和的圆舞曲音调呈现出来,音调同样来自于引子主题。副部和缓的音乐形态符合最初构思中对“理想的怀抱”的描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副部主题的规模相对较小,同时副部主题的后继发展中同样出现一种紧张的张力。弦乐与木管组半音化旋律的不断拔高伴随铜管乐死亡主题的侵入使副部主题那种抒情性格无法获得充分展开,这也为随后的几个乐章形成铺垫。在随后展开部中,主部材料的分裂展示逐渐被厚重的三连音音型同化,而进入再现后,主部的材料变得更为阴沉。直至尾声,主部材料已经失去了乐章开始时的机动性,变得迟滞无比,终至消散,而第一乐章由此完成了意义的陈述,不过在死亡阴影的干扰下,怀疑与逃避都是无用的。
第一乐章是对永恒死亡的质疑与逃离,而第二、三乐章则是从更为具象的角度来阐释生与死的关系。第二乐章是柴科夫斯基交响曲中规模最大的慢板乐章,乐章结构为中部为插部的复三部曲式,其主题同样来自第一乐章引子材料。第二乐章是对第一乐章副部形象“理想的怀抱”的延伸性描述。在第一乐章,这种形象因规模太短小并未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在第二乐章中,这一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衍生出两种不同的主题性格:第一主题沉稳内敛,第二主题激动雀跃。这是对“生存”力量的思考,然而这种思考在曲中两次被引子主题的粗暴插入打断。这是“上帝无上铁律”的威严干涉,是死亡阴影的步步紧逼。与第一乐章的结尾类似,第二主题在引子主题的干涉下变成碎片最终消散。这是先前乐章的进一步陈述:并不存在所谓“理想的怀抱”,在“死亡”、“命数”面前,一切都是无效的。
于是在第三乐章中,视角开始发生转换,这一乐章转而以一种平静的方式呈现生活的本质。作为复三部结构乐章,两端的圆舞曲与中间的托卡塔音调形成对比。圆舞曲主题同样来自第一乐章引子材料,但是在这一乐章中已经完全看不到之前两个乐章呈现出的“怀疑”或“热情”。即便是中段的托卡塔插入段也是以一种“外在化”的音乐描写进行陈述。乐章结束时,命运的动机悄悄进入,与主题融合在一起,以十分平静的姿态结束这一乐章。第三乐章是整部作品的转换点。若前两个乐章以一种诘问姿态问询命运,抗拒死亡。第三乐章转向对死亡的接纳,这种改变延续到第四乐章,完成对这一永恒问题的回答。
第四乐章开头是“葬礼进行曲”为核心的庞大序奏,第一乐章引子主题在此复现,但调性由小调改换为大调。这种调性变化使主题失去了原本的阴郁性格而变得庄重起来,同时,在音乐的进行中,还不断地插入由铜管大管组成的类似圣咏音乐的片段。这种音乐性格的转变使得人们对这一乐章的音乐意义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阿萨菲耶夫将这一庄严的命运序奏形容为“披着节日盛装的骷髅”。他认为这一乐章是表现命运的最终胜利,基调是悲观的。而与他观点相左的克里姆辽夫则认为,这一乐章的基调是乐观的,因为原本阴郁的命运失去了它不祥的性质,仿佛被人民的,不可遏制地改变了。所以终曲应该是个节庆的乐章。
这两种说法都有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即在于并未将其放置于全曲结构中进行观察。单独观察一段序奏显然无法对整部作品的走向加以把握。在经过第三乐章的平静叙述后,死亡已经不再处在人生的对立面,而是被接纳融合,因此第四乐章命运主题的变化实际是一种观念的变化:“死亡”已经不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当“死亡”无处可避,就唯有接纳它,投入它的怀抱才是解脱之道。而当做出这种选择之后,必然会获得救赎。这也是序奏中圣咏主题不断插入的象征意义。作曲家之所以得出如此的结论,或许与之前的《曼弗雷德》末乐章中曼弗雷德灵魂飞升的景象有关。在“接纳”、“救赎”的大背景下,第四乐章的主部主题由《末日经》的原型幻化而成,而随后的副部主题则呈现出一种“狂喜”姿态。在展开部的最后,两主题融合形成一段极纯净的宗教式音响(270-295小节)。随后的尾声也宝相庄严,原本可怕的死亡主题变为一种宗教式的庄严仪式,死亡成为唯一救赎之道,唯在死亡之后,灵魂才可得以飞升。
四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 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生存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莎翁剧作中这段著名的独白成为解读这部交响曲最有效的注脚。整部作品以一种哲学诘问的方式不断质询。如果说在第一、二乐章作曲家还抱着对死亡的恐惧,自第三乐章起这种恐惧已经不存在了。 《第五交响曲》全曲呈现出了一种转化,这是自《第四交响曲》完成后对命运的态度转化。这种转化仍旧是悲观的,但却是勇敢的。在个人与外部世界的裂痕无法弥合之后,作曲家在这部交响曲中找到了另外一种弥合方式,一种自身与毁灭融合以获取救赎的方式。
经过漫长的十年思索,在身边蔓延的死亡氛围催化之后,柴科夫斯基终于找到了解脱之道。于是在音乐中,对命数的畏惧转变为对救赎的歌颂,对世情的留恋转化为迎接死亡的狂喜。这种狂喜将进一步延伸至其最后一部交响曲中,同时将他的痛苦,他的生命引向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