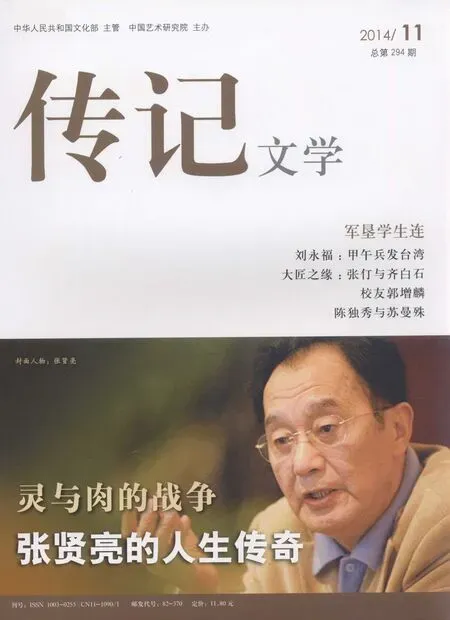我们四个人的故事
叶胜萍
我们四个人的故事
叶胜萍

四个援藏女学生
中秋前夕,相约在上海的同学聚会。自从1978年毕业分手各奔东西以后,有的36年后才第一次见面,岁月的痕迹挂在了每个人的脸上。看着两鬓斑白的你我,大家喜笑颜开,嘘寒问暖,吟诗歌唱,似乎回到了年轻的时代。因为我是毕业分配进藏了,大家不免多了些关心,多了些询问。
话题将我引回到了36年前的夏天,记忆是那样的清晰,就如昨天的故事。
南昌的8月真热,在母校穿着凉鞋从宿舍走到301教室,脚底板烫得踩不下去,走路一跳一跳的,晚上睡觉每隔一小时泼一次凉水到席子上睡下去还是烫背。
这是1978年的暑假,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75级的毕业生在这酷热而空荡的大校园里焦急地等待毕业分配。这一年,是“文革”后国家对大学应届毕业生第一次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当年,国家教育部给江西师范学院下达了四名支援西藏教育工作的指标,这四名去西藏的毕业生名单定不下来,分配工作就无法进行。面临关系到一生前途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我们班102位同学在焦急地等待,心情如烈日般焦躁。每天枯燥的内容就是分组学习讨论。号召去西藏工作的报告会开过多次了,一个多月下来,没有人报名去西藏,也没有人经动员劝说同意去西藏。
8月底,母校请来了我们中文系73级毕业、自愿要求进藏、当时在西藏那曲地区工作的吴雨初给我们做动员报告。在说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西藏见闻和西藏如何需要建设人才的话题之后,吴雨初唱了一首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歌:
红太阳照耀新西藏,
雅鲁藏布江水在歌唱。
高原修起愚公渠,
雪域大地青稞香。
啊,
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
可爱的家乡,美丽的西藏。
就在这第二天,时任院党委副书记兼中文系书记的郑光荣和系主任钟义伟把我叫到了系办公室,夸奖我表现好,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动员我带头报名,服从组织安排,同意去西藏工作。
母校艰难的毕业分配动员工作已经把大家拖得很疲惫。我虽然说不上有什么雄心壮志,但我入学前就入了党,懂得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该如何做。于是,在我们第四组的讨论会上,我作出了“服从组织分配,如果分配我去西藏我也在所不辞”的表态。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是在男生宿舍开会,记得当时陈方根、易中生、彭林槐、周育奎等都用很惊讶的表情看着我,半天没人发言。
我和郭岩是好友,我俩经过商量,由她起草,向系里递交了一份同意去西藏的《决心书》。那天,我的心很痛,在图书馆给父母写了一封信, 我知道,这个决定已让我们没有回头路。
当时,母校正门进入的大道两旁的板报栏、墙面,贴满了红红的要求进藏的申请书和决心书。
于是,曾凡超、罗超群、郭岩和我,还有化学系的曾祥琦,一行5人,跟着护送我们的胡治生老师,被敲锣打鼓的队伍送上了西行的火车。
那年我们去西藏,同学中有传言,认为我们班去西藏四个人是两对恋人。20多年来,也经常有人向我询问过。郭岩和罗超群,在我看来,是不存在这回事的,可以说,他们俩在学校、在西藏,都没有涉及过这个话题,我和曾凡超,也没有涉及婚姻话题。
曾凡超是我们班上的党支部书记,入学前是赣州地区上犹县的村干部。我对他的进一步认识,是母校1977年的秋季运动会,我们没有参加比赛的女同学被叫去当拉拉队。我目睹了曾凡超得了母校的五项全能冠军。在整个比赛过程中,他表现得敏捷、矫健和坚忍的毅力,我很欣赏。那年11月,我们全班赴宁都县实习。刚到宁都时,曾凡超、杨剑龙、李浩川、李美英、卢国荣和我等几位相约一起到翠微峰爬山游玩,我们带来干粮、照相机,玩得很快乐。我不会走山路,下坡和爬山时,曾凡超会轻声叮嘱我“小心点”,让我心存感激,记住他的好。
那时我已经24岁了,但我不能谈恋爱,父母在我上大学之前就替我看好了对象,只等我毕业后回去结婚。我心悦于谁,不敢表露,一点侥幸心理都不敢有。
学校要我去西藏,我能否摆脱父母的安排呢?这时我感觉到了可能有的希望。我和郭岩的《决心书》交出去以后,一种胆怯心理涌上我的心头而不敢与人见面。一天,班上有通知去301教室开会,在教学楼后面的小路上,凡超打招呼和我说话:
“我申请了去西藏,我们一起去吧。”
我很意外,当然也很高兴。我知道,西藏生活很艰苦,高原缺氧,身体会不适应,有一位志同道合的男同学一起去,相互可以关照,也就有了依靠。我们此时有了共同的语言,相约一起谈心,可是我不敢做任何的承诺。我们的心襟都很坦诚,谈前途、理想,不谈个人问题。我相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互相支持帮助。
分配去西藏的通知下来后,回到萍乡做了半个月的停留,前10天是抗婚,母亲以死相逼,不结婚不准走。学校催10月3号要出发,派了刘方元老师来萍乡做工作,无济于事。第11天(1978年国庆前一天)我扛不住了,答应结婚。母亲已经三天未进水米,此时从床上跳下来为我操办婚事。我知道,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祖国需要、母校的安排、父母的旨意都要服从。我10月3号结婚,10月6号离家到母校,10月7号出发进藏。
这是我的真实处境,在这之后的30多年里,总是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西藏,我如此回答,却总有人心存疑问,但郭岩知情,凡超相信。
我无以报答曾凡超对我行为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在西藏再行分配时,我被分配在教育厅机关,曾凡超、郭岩分在西藏师范学院,罗超群分配在拉萨师范学校。由于教育厅环境和条件都比师范学院好,我以很多理由与西藏教育厅人事处、分管副厅长交涉,要求与凡超更换,让他留教育厅,但没有得到同意。
非常欣慰的是,曾凡超在西藏师院找到了一位很优秀的爱人,陕西民院毕业,长相端庄清秀,他们生活很美满。1991年他内调到江西省出版局,历任版权处副处长、处长。2002年春节后正月十一日,我在北京出差,一个噩耗传来:曾凡超被派出到赣西片发行教材辅助读本,汽车在驶近安福县的途中遭遇车祸,为工作献出了年仅48岁的生命。那年他女儿在西安上大学一年级,却没有能赶回来送一程。
曾凡超和郭岩所在的西藏师范学院在拉萨东面,离教育厅很近,走路不到十分钟。而罗超群所在的拉萨市师范学校则在拉萨西郊,骑车要半个小时。当时几位同学和几位江西老乡经常在我这里聚会,做点小菜,改善伙食。罗超群路远,他骑车过来,我们经常会为他的安全担心。
现在回想起来,罗超群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在母校的时候就很瘦。到了西藏,伙食很差,一天只能吃一顿米饭,冬天没有蔬菜,只有牛羊肉。超群一直胃不好,加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到西藏以后,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感觉越来越瘦。但他很顽强,默默无言,勤勤恳恳待人做事。
超群有一副非常善良、乐于助人的侠肠义胆。记得1980年11月,我已经怀孕8个月,要回内地休产假。超群千方百计要求学校批他休假,要送我回萍乡生孩子。那时天气很冷,我穿着大衣,挺着大肚子,带着两个大包。从自治区教育厅出门到贡嘎机场,坐飞机经成都转机到长沙,两个人的行李超群一个人扛,一路还要照顾我。在长沙分手,他把我送上去萍乡的火车,反复叮嘱车上的人照顾我,火车开动时,我感激得哭了。

本文作者在拉萨(1979年夏天)
最后一次见到超群,是1996年8月,我在萍乡市广电局任局长,月中旬随萍乡市领导一行到拉萨出差,那时他已经调整在拉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担任副主任。我打电话找到了他,电话里我们欣喜若狂。那天下午,他和妻子小陈接我和我另外两位同事去他家吃晚饭。
超群早早地站在办公大院门口接我们,走进他家,我的心又沉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夫妻俩衣着非常朴素,超群又黑又瘦,小陈和超群一样消瘦。这时才得知,超群妻子小陈也是赣南人,结婚后随超群到西藏,没有找到正式工作,在一家工厂做大集体工,收入甚低。两个孩子都还小,一个放在赣南老家带。超群的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喝着他一定劝喝的啤酒,我的心在流泪,为他的身体和处境担心,我暗下决心要帮他一把。
回来后,我走了几个地方,请人帮忙调他回江西,没多久,赣南地委同意他调入赣州地委办公室。没想到,超群那边的手续不好办,单位迟迟不肯放。
1998年底,超群夫妇休假坐火车途径萍乡,打电话给我,希望能去车站见一面。我因开会去不成叫同事代我去见面,想挽留他们下车住几天,他们推辞了。没想到,超群回到老家后竟一病不起。次年上半年,我准备去赣南看他,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才得知他一病不起,已于早几日辞世,年仅43岁。
当年我们四个人同伴走进西藏,却没能携手同回。1980年中央在西藏落实民族自治政策,我因在行政机关工作,1981年6月随大批行政人员内调队伍回到了萍乡。
郭岩于1982年随丈夫调回上海,一直在上海浦东洋泾中学任教,担任语文教研室主任直到退休。郭岩为人质朴善良,性情平和温柔,我们进藏后,她在西藏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她先生冯钧国是上海人,当时是上海华东师大的援藏教师,也在中文系。“有情千里来相会”,他们相助相知相爱,成了一对幸福的伴侣。在上海,虽然工作奔波辛苦,夫妻俩却是夫唱妇随,恩恩爱爱。

本文作者(左)与郭岩在拉萨/2004年重返拉萨时本文作者与大昭寺主持、全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尼玛次仁合影
我在西藏工作还不到三年,但对西藏的感觉一直如梦魂般缠绕。在那里,我感受了孤独,只身来到一个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地方,以前的任性和骄气荡然无存。记得1979年春节除夕,我的室友、河北姑娘王惠玲被亲戚接走过年,我一个人守着食堂分配的摆满一办公桌的菜和一瓶汾酒,大喝起来,一个人把一瓶60度的白酒喝个精光,喝着唱着睡着了。初一醒来,一脸的鼻血。走到门外,教育厅院子里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影。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的孤独和无助,跑到拉萨大桥上,对着滚滚的江水撕心裂肺地大哭。在那里,我学会了吃苦。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边境县下乡,经常是一星期吃不到一粒米饭,上餐喝了酥油茶、吃了烤牛肉吐了,下餐还得接着吃,带的烤饼硬得咬不动。晚上睡觉犹如躺在稻草堆尖上,浑身没有着落,激烈的心跳感觉就像断了气。在那里,我经受了磨练。在教育厅政治部,大大小小的情况汇报、会议文件、工作总结、调研材料、领导报告,大多落在我的头上。特别是下牧区搞调研,一走就是半个月,白天进机关、学校、家庭走访,晚上整理,回来就要有几十页稿纸的调研报告上交。 在那里,我领略了美丽的高原风光和质朴的民族品质。高原上那变幻无穷的白云、湛蓝剔透的蓝天、常年不化的雪山,呈现着无以伦比的美。藏族人拜佛,三步一长叩到拉萨寺庙,可以走上一年而为了奉上一盏酥油。藏族人质朴谦让,一次我骑自行车在一处斜坡拐弯处刹车不灵撞到了一位中年男人,我也摔倒了,他在他妻子的搀扶下爬起来,还要他妻子扶我站起来,我以为他们要找我算账,结果他是以很蹩脚的汉话问我:“朴姆,没事吧?”(朴姆,姑娘的意思)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软弱、自私、或英雄豪气都会被转变,环境由不得你不去顽强地挣扎、拼搏。
回来已经33年了,我把西藏当作我的第二故乡,尽管回忆是那样的沉重。33年里我回过三次拉萨,每次的感觉都很新鲜、很亲切。进藏前朱安群老师送了我一首古体诗,其中一句是:“高山水美育才俊,愿尔长成擎天松。”这是老师的鞭策和嘱托,我不是什么擎天松,但在这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都能吃苦努力,意志坚定,坦荡乐观,真情做事待人。
责任编辑/孙 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