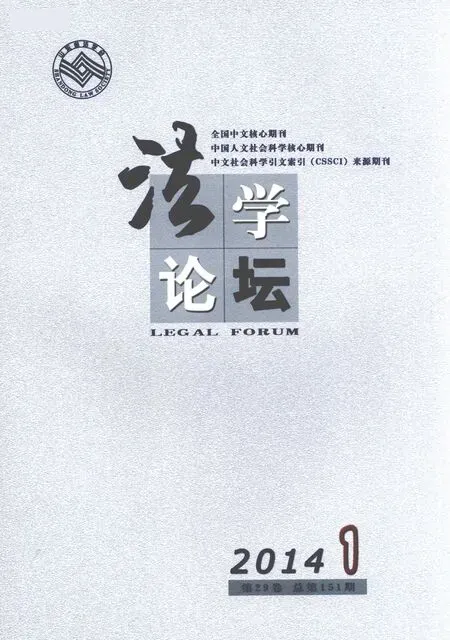论犯罪本质的义务违反说优越于法益说
牛忠志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犯罪是全部刑法的逻辑起点,犯罪的本质问题是刑法学的核心问题,故犯罪本质理论是整个刑法学的逻辑起点。对犯罪本质的不同认识,关系到刑法立法具体规定和刑法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如关系到刑法的任务的确定,关系到刑法目的和功能的定位,关系到犯罪成立条件的筛选,关系到犯罪形态标准的确定等。不仅如此,犯罪本质问题还关系到犯罪的司法认定和刑事判决的执行。因此,目前的我国在犯罪本质问题仍然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继续对其加强研究,深化犯罪本质的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目前的中国,除了不少学者坚持正统的犯罪本质的“社会危害性说”①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以下。之外,相当一部分学者都转向了法益说,法益说将有取代“社会危害性说”而成为通说之势。不过,笔者认为,对犯罪本质问题,首先,站在法学立场,而不是政治学或社会学的立场,犯罪的本质不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次,在法学视野下,犯罪的本质不是法益侵害而应该是义务违反;②笔者曾经主张“义务违反为主,兼采法益侵害折中说”(参见牛忠志:《犯罪内涵新释》,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法学)版》2007年第7期)。现在,笔者彻底秉持义务违反说:犯罪的本质是行为人对其重大的正当义务的违反。最后,基于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定义,犯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因而犯罪的本质是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对其重大的、正当的义务的违反。这一结论的获得和确信,除了需要形而上地为义务违反说正面立论(笔者已另行撰文),还需要将义务违反说与法益说的优劣进行对比,包括阐述法益说的不足、义务违反说的优越性、刑法立法的可贯彻性以及其与当代刑法理论的融洽性,进而坚定大家秉持这一立场的信念。
一、法益说的主要不足
在我国,法益说主张: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合法权益;我国《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犯罪定义指明了犯罪是侵犯合法权益的危害行为;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犯罪都是对合法权益的侵犯,也即“犯罪的法律本质是侵犯法益”。①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但笔者发现,法益说存在重大的缺陷。
1、法益说无法确定和解释行政犯所侵害的法益。对于行政犯所侵害的法益的确定和解释是最令法益说头疼的事情,以至于对行政犯是否侵害法益的问题,有些学者干脆说“行政犯没有侵害法益”。不过,这样的回答显然是动摇了把法益侵害作为犯罪本质的资格。如果“对法益的侵害是犯罪的本质”的命题成立,那么,不可能只有刑事犯才侵害法益,而行政犯却不侵害法益;如果“只有刑事犯才侵害法益,而行政犯却不侵害法益”这一判断成立,则意味着对法益的侵害不应该是犯罪的本质,因为本质是该类事物共同的属性。
正是法益说陷入此等“二难”困境,故该说对实定法所规定的犯罪的解释力大大地被削弱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却需要立法规定行政犯,这就催生了义务违反说,义务违反说作为法益说的掘墓者便应运而生了。
2、法益说容易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效果。法益说强调的“法益”是权利主体的法益。这样,就极易给我们一种错觉: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而由于法益是特定主体的法益,故犯罪是对某一特定主体之法益的侵害。其结果是强调了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犯罪被评价为是对国家整体法律秩序的挑战,犯罪之所以是犯罪,主要的不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事情,而是国家与加害人之间的事情。这是现代刑法不可动摇的信念。法益说不能恰当地说明犯罪行为对国家整体法律秩序的对抗性,因而容易把犯罪视为对某一特定主体法益的侵害,从而导致对犯罪理解和评价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效果。
这种不足,已经导致了对犯罪构成理论的模糊认识。例如,有学者认为,正当防卫行为和紧急避险行为都符合我国犯罪构成——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犯罪客体要件”。②参见王政勋:《定量因素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陈兴良:《四要件犯罪构成的结构性缺失及其颠覆》,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6期。而实际上,这是坚持法益说所导致的不足。如果秉持义务违反说,从国家整体法律秩序的角度考察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存在犯罪客体的余地,否则,就不是正当行为了。
3、法益说不能区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与其他部门法所保护的法益。如果说这一缺陷在德日国家由于其不严格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③在德日,犯罪的成立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以日本刑法为例,按照日本刑法,行为人盗窃一分钱的行为也可能构成盗窃罪,至于是否最终作为犯罪来处理并追究刑事责任,则需要有检察官、法官根据其职业经验、考察全案情况、案发当时社会环境条件等因素,自由斟酌之。还不是重大缺陷的话,那么,在我国,由于犯罪与一般违法的严格区分,因而刑法理论必须着力解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与其他法律所保护的法益的划界问题,从而法益说的固有缺陷在我国就被进一步地放大。界定犯罪就必须把刑法法益与其他法益作严格的区分,但法益说难以完成这一使命。有学者试图区分刑法保护的法益与一般部门法保护的法益,在坚持法益说的同时,认为“‘国外可罚的违法性’概念,就是为了把刑法上的违法在量上限定为一定严重程度,在质上值得科处刑罚的违法性;在我国,只要坚持对犯罪构成的实质解释,就不会得出‘只要行为侵害了法益就成立犯罪’的结论”。④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335页。请注意,论者一方面把犯罪的本质理解为法益侵害,另一方面又主张并非“只要行为侵害了法益就成立犯罪”,这里显然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是法益说所固有的。
4、对法益说不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照搬并不适当。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明楷教授最先介绍法益说到国内。“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这是法益的一般概念,其中有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则是刑法上的法益。”⑤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稍后,也即至世纪之交,何秉松教授由最初主张利益说转而接受法益说;⑥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2000年修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以下。陈兴良教授撰文主张将犯罪客体还原为刑法法益,并认为法益概念在“规范性”、“实体性”、“专属性”等方面优越于“社会危害性”。①不过,作者只是把法益说与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简单对比而没有对法益说的本体内容展开论证。参见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在刑法学界这些权威人物的影响下,国内许多刑法学人逐渐接受法益说。但是,在中国,缺乏的是进一步对法益说的深入研究,以及法益说与其他犯罪本质观的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灯不拨不亮、理不辨不明”,如果不深入研究,不作比较分析,便人云亦云地搬用法益说,则有盲目跟风、赶时髦之嫌。
5、法益说在其发源国的衰弱。法益说发源于德国,并一度盛行于德国。但是,随着对法益说研究的逐步深入,德国的不同学者对法益概念产生了不同认识:关于什么是刑法中的法益,却有很大分歧。李斯特、如鲁道夫(Hans-JoaehimRudolphi)、奥托(Otto)、马克斯(M i haelMarx)、汉瑟莫尔(winfriedHassemer)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如有的认为,刑法所保护的对象就是法益,作为法所保护的生活关系被固定化、规范化的东西就是法益;有的认为,法益是刑法分则条文所认可的立法目的;还有的认为,法益是刑法解释与概念构成的目标等。其分歧的焦点在于,这里的“法益”是实定法所确立的法益,还是前实定法的法益。对此,德国学者至今也没有就法益的实在含义作出一致性的回答。持法益说的学派内部关于法益的不同见解和学说自身的问题导致了该学说在德国的衰弱。
二、义务违反说较之法益说的优越性
义务违反说主张犯罪的本质不是法益侵害,而是义务违反。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定义,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触犯刑法和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由此,犯罪的本质应该是对重大的、正当的义务的违反。笔者认为,义务违反说较之法益说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1、义务违犯说有助于从国家整体法律秩序的立场来把握犯罪行为。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虽然广泛,但是却具有“片段性”或者“不完整性”②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只有在立法者看来如果适用其他法律制裁便不足以控制该类危害行为而必须用刑罚的方法才能制裁和预防该类危害行为时,才把这类危害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换言之,刑法只是调整“违反国家整体法律秩序的行为”。这说明了“犯罪是违反国家整体法律秩序的行为”。③参见牛忠志:《刑法目的新论》,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5期。这一判断的要害在于“犯罪是对特定法律义务的严重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具有国家强制性。如果义务主体不履行法律义务,则国家动用执法或者司法机关强制其履行该义务。法律义务的国家强制性使我们很容易且顺畅地理解犯罪的反社会性质以及犯罪人与国家整体法律秩序的对抗性。于是,义务违犯说从国家整体法律秩序的立场来把握犯罪行为的本质,就能有效地克服法益说对犯罪本质解读的局限。
2、为什么危害行为侵害相同法益却构成不同犯罪并设置了不同的法定刑?法益说对此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盗窃罪、抢夺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它们所侵害的法益是相同的——所有权,但为什么它们是五个不同的犯罪,且对它们处罚也有很大的差异。再如,背叛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等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但其法定刑设置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有的犯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有的却为有期徒刑。义务违法说则能够很容易地提供合理的解释:危害行为所违反的具体的法定义务不同,当然就会导致相应不同的法律后果——不同的刑事制裁及其强度。
3、法益说不能解释对真正的身份犯处罚的合理性和对不真正的身份犯的处罚轻或重问题。真正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无此特殊身份时该犯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犯罪;不真正的身份犯是指特殊的身份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的犯罪。④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前者如贪污罪,其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后者如诬告陷害罪,任何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该罪,但若是国家工作人员犯此罪时,则从重处罚。在身份犯的场合,行为人侵害的是相同的法益,但为什么只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构成犯罪,而不具有该身份便不构成犯罪或者构成其他犯罪?在不真正的身份犯的场合,虽然都构成犯罪,但为什么对于有特定身份的人的法定刑设置与没有此等身份的人较轻或者较重呢?法益说对此难以做出恰当的解释。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以至于坚持法益说的学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犯罪的“义务违反”实质性。其中,“犯罪的本质既包含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同时也包括对一定的义务的违反”的犯罪本质这种观点,是日本学者团藤重光首倡,并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①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如日本学者大冢仁教授就指出,“犯罪的本质,一方面基本上是对各类法益的侵害,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的义务违反可以作为本源。”②[日]大冢仁:《注释刑法》,青林书院1978年版,第122页。转引于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笔者认为,坚持义务违反说,对身份犯问题解决就用不着拐弯抹角,身份犯问题的解释就很简单:身份不同,社会地位就不同,其肩负的义务也就不同;无论是真正的身份犯,还是不真正的身份犯,对其行为的犯罪化与否、处罚的轻或者重,当然是各当其理。
4、法益说在解释对未遂犯、危险犯和预备犯处罚的合理性时,背离了其最初所倡导的“刑法谦抑”之旨趣。法益说原本主张:“犯罪的本质是对作为权利对象的、国家所保护的利益造成的侵害”,之所以提出法益说,其初衷是为了实现刑法的谦抑性:限缩刑法对社会生活介入的深度与广度——依法益之侵害为标准来限缩刑法对社会的介入深度和广度。但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的客观现实却不能囿于法益说的初衷,现实的需要是:立法必须处罚未遂犯、危险犯,甚至某些犯罪的预备行为。但是,在未遂犯、危险犯,犯罪预备行为的场合,法益的侵害不具有实害性。
为了说明处罚未遂犯、危险犯和某些预备行为的合理性,不得不对法益说进行修正:在法益被侵害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法益的威胁”的内容。这样,刑法的调整范围的划定上就不再基于已然的、作为法律后果的法益之侵害,而把一种可能的趋势,即对法益的“危险”情形也包括进来。其结果就背离了法益说最初的旨趣。
然而,如我们若立足于犯罪本质的义务违反说,则危险犯、未遂犯、预备犯等的处罚根据就能够直接地、顺畅地予以说明:在上述诸种情况下,行为人都违反了相应的法律义务,因之,其义务违反行为;如果该义务违反行为是严重的,当然就可能获得“应受刑罚惩罚性”,从而避免了法益说拐弯抹角的说明或者强词夺理的论证。
5、对不作为的行为性问题和处罚根据、对于疏忽大意犯罪的处罚根据,等等,这些世界性刑法理论难题,法益说同样束手无策而不得不转弯抹角去进行苍白无力的论证。
首先,法益说为了证成对不作为犯处罚的合理性,在不作为的行为构成上,不得不设定先在的“积极作为义务”,而后再把这一积极的作为义务作为不作为的构成条件之一。法益说在这里,实际是明一套暗一套:名义上持法益说,暗中却转而求助于义务违反说。
其次,对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处罚的合理性的论证,法益说也陷入窘境。本来,犯罪与一般违法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反社会的主观意志性。但是,疏忽大意情况下行为人对法益的侵害,既无认识,也无意志,谈何主观恶性!这时,法益说为摆脱窘境又不得不转“暗渡陈仓”:求助于义务违反——行为人有义务预见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却不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于疏忽大意而不能预见,于是,对疏忽大意的处罚是合理的。这解释是多么的拐弯抹角呀!如果直接采用义务违反说,则能够直接地、顺畅地予以说明:在不作为、疏忽大意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违反了相应的法律义务,因而其义务违反行为在严重到必须用刑罚加以制裁时,就获得了应受刑罚惩罚性,即构成犯罪。这种解释也同样避免了法益说的拐弯抹角和强词夺理。
无需再多举例,已经可以看到:法益说在犯罪和刑罚具体问题的解释时,每逢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就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义务违反说,从行为人的义务违反角度,拐弯抹角来做出曲折的解释或者牵强的说明。这也反衬出义务违反说优越于法益说。
三、义务违反说与现行刑法和刑法理论的相容性
如果一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或者必须做重大的修正才能贯彻,那么,这一理论要么就会是镜中花、水中月,或者是难以开花结果的枯树,其结局就是不得不将其束之高阁或者干脆将其抛弃。笔者认为,这种不能产生实际效益的理论,无论被说得是多么的天花乱坠、极其动听,也无论是多么的权威,都注定没有生命力而难以苟活。然而,义务违反说不仅理论上能够自恰,在实践层面也容易贯彻:既无需彻底推翻现行的立法,也不颠覆当代的刑法理论体系。
1、我国现行《刑法》所设立的罪刑规范绝大多数都直接表明了犯罪的义务违反性。从条文表述上看,大多数犯罪的罪状都无例外地表述为:“违反法规,非法……的”,这是义务违反说在刑法分则中贯彻的直接体现。例如,“故意杀人的,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致人死亡的,处……”。我们能十分清楚地看到现行立法对义务违反说的贯彻。
相反,在个罪基本罪状的表述上,刑法分则中很少有以被害人的法益被害性质和量度作为犯罪的反社会性的衡量标准。换言之,法律没有规定“被害人因他人故意杀害而死亡的,对行为人处……”,法律也不是规定“被害人的财物因他人的盗窃行为而损失且数额较大的,对行为人处……”。可以说,从整体上看,目前的立法现状所贯彻的是义务违反说,而不是法益侵害说。
2、对刑法条文的修改更加亲近义务违反说。我国对刑法的修改体现出贯彻义务违反说的立法例很多。兹举几例:第一,1997年《刑法》对于许多犯罪的犯罪数额的标准由“违法所得”改为“非法销售金额”。①例如,对1997年《刑法》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重大修改之一便是把本节犯罪的数额标准由过去的“违法所得”改为“销售金额”。这种修改实际上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贯彻了犯罪本质的义务违反说。因为与“违法所得”相比,“非法销售金额”更能直接地表明犯罪人的对其法定义务违反之程度。这一立法趋势,表明了义务违反说的生命力。第二,《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通过)第1条:“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薄财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这一表述清楚地体现了特定义务主体违反法定义务时,构成该犯罪。第三,《刑法修正案(七)》第1条:“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第四,《刑法修正案(八)》第35条:“明知是伪造的发票而持有,数量较大的,处……”。如果不是盲目轻信法益说,而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刑法的修改是在贯彻义务违反说而不是法益侵害说。
3、义务违反说与当代刑法理论的融合性。犯罪本质问题是刑法的基本问题,对于犯罪本质的不同观点会关涉到刑法理论的诸多方面。那么,犯罪本质的义务违反说能不能与现行的刑法理论相融合?或者说如果秉持义务违反说,要不要对现有的刑法理论进行彻底的颠覆?回答是:不会,绝对不会的!
义务违反说在前述关于对真正的身份犯处罚的合理性和不真正的身份犯的处罚轻重问题;在解释对未遂犯、危险犯和预备犯处罚的合理性,以及不作为的行为性问题和处罚根据、对于疏忽大意犯罪的处罚根据等刑法理论难题时,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穿透力和柔韧性。如果以上是从微观层面证明了义务违反说与当代刑法理论一致性,那么,下面将从宏观层面进一步阐释义务违反说能很好地与当代刑法理论的融合生长。也就是说,主张犯罪的本质是行为人违反了重大正当的义务,这绝不意味着彻底颠覆和全盘否定当代刑法学的所有理论。
首先,“犯罪的本质是什么”,与“犯罪的认定标准”是两个问题,而学界一直混淆这两个问题。犯罪本质是犯罪的本体论问题;认定犯罪的标准是对犯罪(本质)的衡量标准,是认识论问题。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正如“飞行中的子弹”是本体论问题(仍然是子弹),“测量飞行的子弹之速度(或者能量)”是认识论问题: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度量衡工具来测定的子弹的飞行速度——我们可以通过弹痕、子弹击中的靶子,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财物的毁坏、人的伤亡等)来检测子弹的速度或者能量。但是,我们却不能把“飞行中子弹”与“检测子弹的速度的工具”相等同,把“飞行的子弹”混同于“弹痕或者子弹所击中的靶子”同样也是错误的。再如,“树的高度”是本体,测量树高的尺子是喻体,显然我们不能说“树高”就是“尺子”。同样的道理,犯罪本质与对犯罪的测量(法益的被害)是不同的。所以,坚持犯罪的本质是义务违反,也绝不会颠覆现行的以“法益为犯罪本质考察标准”所建立的刑法理论。
其次,区分犯罪本质与对犯罪的衡量标准有助于拓宽设置犯罪成立条件的思路。犯罪的本质与犯罪的测量手段(实际是犯罪的成立条件),虽然明显区别,但又不是截然无关的。犯罪本质是本体论问题;对犯罪的测量是实践层面的认识问题。正如我们要测量青岛距北京的距离时,有多种方案:可以直接地测量青岛与北京之间的距离,也可以先分别测出青岛至济南和济南至北京的距离,再使二者相加得出青岛至北京的距离,还可以先分别测出青岛至哈尔滨的距离和北京至哈尔滨的距离,再使二者相减得出青岛至北京的距离。不过,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哪一种方法是更准确呢?显然是前者。法益说与义务违反说的优劣,与此相同:衡量犯罪,首先作为上策的是直接确定行为人的义务违反之质和量。既然“刑法中的行为是行为人控制或应该控制的客观条件作用于具体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过程”,①此为陈忠林教授语,参见刘霜:《论我国刑法中行为结构层次理论的构建》,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那么,转而去根据被害人法益所受的侵害来测定行为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是舍本取末。只有从行为人(加害人)本身来考量犯罪行为的反社会性及其程度,才是直接和精确的;相反,通过考察被害人法益的被侵害及其程度,并以此作为测量犯罪人犯罪性质和程度的标准,是间接的,也是不精确的。
那么,如何测量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对行为人犯罪行为的衡量就是要确定行为人的义务违反性质及其程度。所以,考察犯罪的反社会性及其程度,从行为人的义务违反的质和量来进行就具有直接性和精确性,从而具有首选性。反过来,借助于被害人一端来设计,通过测量被害的法益受损的性质与程度来推测、映衬行为人犯罪(即犯罪性——义务违反的性质和程度),就是间接的也同时是相对不精确的。其次,当“直接确定行为人的义务违反之质和量”困难时,衡量被害人的法益侵害性质及其程度就是次等途径。也就是说,法益之侵害可以用来从外部、间接地量定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只不过这是一条是次选的途径罢了。总之,对犯罪本体衡量的首选应该是对行为人的行为所承载的义务违反之性质和量度的考察;次之,才选择以对被害人的被害法益的危害及其程度作为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