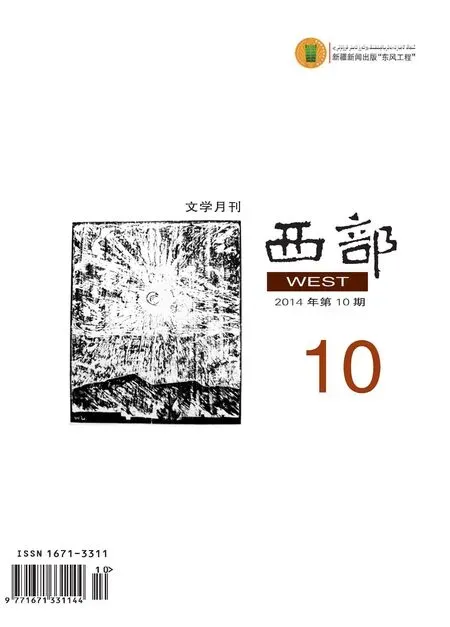西部头题·2014特克斯笔会仲夏伊犁走笔,或黑走马
汗漫
西部头题·2014特克斯笔会仲夏伊犁走笔,或黑走马
汗漫
向西
2014年6月末,我应《西部》杂志邀请,在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特克斯县城、喀拉峻草原、伊宁市等地,与若干友人盘桓数天。我,一个本名“向东”的中年人掉头向西而行,向东流淌的一江秋水掉头,向西,追溯源头。路上,一个伊犁人问我:“朋友,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我说:“初次进疆像初恋。”他笑:“初恋都是要抛弃的。”我嘀咕:“我被初恋抛弃了?”
是的,我和伊犁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初恋,而非婚姻,伊犁不会接受一个中年人虚脱的身体和心灵。她属于这个州、这个区域内生长着的哈、汉、维、回、蒙、图瓦等等民族的人们,彼此有着平淡而隐秘的深情,持久,恒定。一路上,欢呼、拍照、恋恋不舍的人,都是我们这些内地来的初恋般的人,有着即将失恋般的感伤。而那些眼睛微闭、嘴角含着嘲讽的人,像伊犁的丈夫,从容,平静——他们对自己的魅力很有信心,知道我们这些内地人、这些内向的小地方人,带不走伊犁的大美,至多怀揣一些馕、无花果、绣花披肩、薰衣草、冬不拉、伊犁特、星光、马嘶……等等事物,作为“初恋”的信物以供长期回忆而已。
短短数天,影响一生,像初恋。我写下这短短几页文字,像情书、情诗,给伊犁——笔尖像跳“黑走马舞”的哈萨克人的脚尖、像马儿的蹄尖,在纸上移动,按照一只手鼓击打出的节奏,移动。
土陶奖杯
在特克斯获得一个硕大的土陶奖杯,其上镌刻“喀拉峻杯·第三届西部文学奖散文奖——汗漫”字样。诗人、《西部》杂志总编沈苇说,这个土陶奖杯是由维吾尔族老艺人制作的,做得这样大是因为新疆天大地大。中亚的泥土和火焰,使这个奖杯微微泛红。接过这个奖杯和证书,我随口说了一句感想:“这个像酒坛一样大的奖杯,像结婚证一样的证书,证明我是一个能喝酒的喀拉峻草原上的新人了!”朋友们笑。
我的获奖散文《小叙事》,以近于小说的笔法叙述了故乡中原村镇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若干乡村小人物的命运。他们困顿、绝望、挣扎、失败,像切片,可能由此透视出一个转型中的时代病象。一篇似乎与新疆无关的散漫文字,却获得了西部文学奖,使我确信:写中原就是写新疆,写中国就是写世界,因为所有的文字不论从哪一个地域、哪一个年代出发,都必须直指人性、归于灵魂,像希尼的爱尔兰沼泽地、福克纳的美国南方、沈从文的湘西长河、索尔·贝娄的芝加哥。
所以,我对自己获得西部文学奖感到光荣和坦然。那是喀拉峻草原的光,繁荣和坦然。
从此,我的写作有了以天山雪峰为远景的支撑、示范和召唤。
喀拉峻草原
终于站在面积约两千八百五十平方公里、海拔约两千七百米的喀拉峻草原上了。喀拉峻,哈萨克语意为“莽原”。绿草从眼前一棵棵奔向天边山顶——天山峰顶,转化成了白雪,这也是一种从绿到白的“跨文体写作”吧?
试探着走到一匹黑马身边。想起布罗茨基的诗《黑马》:“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这匹黑马能够显影出我的青春和暮年吗?我是不是它要寻找的骑手?“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它也与白昼格格不入。我在这匹黑马巨大而淡远的眼神前感到了自卑。
小心翼翼地在一个哈萨克族牧人的帮助下爬上马背。我的海拔又提升了一匹马的高度。美国诗人斯奈德在苏窦山望站写下过诗句:“向下远眺,数英里在目/大气高旷而静止。”他应该也骑过马。我第一次有了马背上的世界观:大气高旷而静止。
一个喀拉峻草原的牧人,如果走在内地,比如上海的外滩,罗圈腿、眼神都与一匹马及其海拔有关——他显得“高旷而静止”。在他的视野里,我大约只是一张轻浮而微弱的广告纸,写满了价格和错别字。一匹马支持他的高和静。
现在,一匹马帮助我与轻浮和微弱拉开大约两米高的距离了。双腿紧贴马腹,感受到了马体的热度,有一些紧张。哈萨克族牧人用不太流利的汉语指导我:放松,呼吸与马步节奏保持一致,与草地起伏保持一致。像是老师在指导我写作:放松,呼吸与叙述的节奏保持一致,与生活起伏保持一致。黑走马像在走笔。
渐渐适应马步的节奏和草地的起伏。马偶尔止步,低下漫长的头颅咀嚼绿草,我随之向前低下身子,好像也满口草汁了。与马的身体渐渐融合为一,就像与爱人的身体在拥抱中渐渐混淆了归属。我们向草地深处走去,草越来越深,深到马的腰部了。星星点点的花朵像草原的优点——我像喀拉峻的一个缺点?
朝着天山雪峰的方向一马步一马步地移动。我、一匹马,与天山雪峰之间充满库尔代森林大峡谷、库什台草原、包扎墩儿草原、阔克苏大峡谷……
有些绝望。只能眺望而不可亲近,像梦中面对已经去世了的父亲。一种榜样般的存在。只能目送绿草涌上大约一百公里外的峰顶,成为白雪。草色在奔涌的过程中不断转化:从近处的深绿,到远处的浅绿,再到更远处——天山腰部耀眼得近于白的明绿,到最终的雪光、天蓝……
突然,马站了下来。哗哗啦啦的声音。我低头观察——马在尿,像我在尿,冲洗着大约四、五十棵左右的草。我笑了,像一个因失恋丧父而长期抑郁的人,在寻找到某种独特的释放形式后重新树立起生活下去的信心。哗哗啦啦。
一个失恋丧父的人有可能成为诗人——用笔作为某个女子眉笔的纪念碑,用墨水瓶作为祭奠父亲的酒瓶。
一首诗
内心默诵出一首短诗,《在喀拉峻草原眺望天山》:
你头颅高大,才能思路漫长、丝绸之路漫长——
从桑叶、蚕、织工
到飞天、金桃、《古兰经》
你冰峰入云,启示:在晚年
双肩之上堆雪,一个人才能真正拥有怀抱中的
江南、中原、西域这三个少女和少年
在喀拉峻草原眺望你的北麓
这背影或者面影,让我对日益降温的生活
有了依归和尺度——
两鬓渐白,不必染发
身体佝偻出弧度,就与草原的坡度保持一致
内心缺陷,让草、蜜蜂、流水抓紧修补成为峡谷
晚安,天山。在喀拉峻草原向晚年致敬
我怀抱一卷诗、一匹马、一个夏天
这三种事物,让双臂逐渐打开、延伸、返青……
夜色里
喀拉峻的夜色,大约在北京时间二十二点开始,从草根里渐渐向上升起。青草渐渐成为了黑草。天山之上,最后一抹晚霞在微白的雪峰上吻别出了一缕淡淡的红。吻。别。淡淡的红最后也消失了,但雪峰的微白始终存在,像一匹黑走马唇部的微白——
夜晚的喀拉峻,一匹黑走马?峡谷里的流水声像马蹄、马嘶。远远近近牧民毡房里的灯已经亮了,像黑走马马鞍上刺绣出了红花。哈萨克女子绣出的花朵都针脚很大,因为她们天大地大。这几个灯火通红的毡房很大,点缀在喀拉峻夜晚的腰部,点缀黑走马。
毡房里的朋友们正围坐在地毯上,面对馓子、手抓饭、羊肉、奶茶、西瓜、酒、揪片子、葡萄干、酥油、拉条子,敞开胃口、歌喉、手风琴。毡房外有一只雄鹰卧在树枝上,头部被牧人戴了一个小皮帽,围堵视线,使它产生倦意、睡意而不至于在夜色里冲天而起。它等待白昼。“那夜间全是平安的,直到黎明显著的时候”(《古兰经》)。
我也戴了一个帽子,但像那只雄鹰吗?它梦境里一定充满了对野兔的轻蔑和进攻。我属兔。坐在远离那只雄鹰的草丛里,稍稍有了安全感。据说,此地早年频频发现草原石人——石头,直立,粗线条浮雕出人的轮廓。这些石人如今都被珍藏在博物馆里了。其功能据说有三:守候墓地,指明方向,证实边界。我坐在这里,像一个草原石人吗?为自己逝去的岁月守墓;为草丛里的一只蜥蜴、蚱蜢指明方向;为自己今夜以前、明晨以后的生活,证实一条边界的存在……
最早知道新疆是少年时代读《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和妻子在河边洗衣服,乌鸦飞来把肥皂叼走了。妻子着急:“快追呀!”阿凡提望着飞远的乌鸦,一动不动,说:“咳,别跟它争了,你看它那肮脏的样子,比我们更需要肥皂呢。”一个语言天才,依靠舌头的运动就可以赢得声名。我读着那本《阿凡提的故事》,笑得难以自持。新疆是有阿凡提的地方,是让人欢笑得难以自持的地方,是输出肥皂给异乡的事物洗去肮脏样子的地方。
最早看见一个与新疆有关的人,是二舅。他在天山那边的阿克苏当医生。回到中原,到我家走亲戚,礼物是一张羊皮、一袋葡萄干。羊皮很大,可以铺满一张床作为床垫御寒。那袋葡萄干是我至今没有再遇到过的美味。二舅说话已经不是纯正的中原土语,带有陌生的音调和节奏。他是从远方回来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无形中鼓舞着一个幼小的孩子想象远方。
最早爱上诗歌,是因为李瑛1963年出版的一本诗集《红柳集》。木刻封面上的赛里木湖、小舟,插图中的月亮、骑马的人、哨所、天山,让我神往。“风沙很早就醒来,/ 像群蛇贴紧地面,/ 一边滑动,一边嘶叫。”这些句子与我七十年代课本中充斥的“打倒”、“斗争”一类政治词语多么不同啊!与当时报纸上批林批孔的诗歌多么不同啊!《红柳集》纠正了我对诗的认识。我喜欢上这种竟然把“风沙“和”蛇“联系在一起的句子了,喜欢这些句子所联系的西域了,幻想自己也成为一个边防线上巡逻的哨兵,业余写诗,像李瑛。多年以后,在北京,认识了这个老人。我说到了《红柳集》,他眼睛有些湿润,说:“你到新疆、甘肃一带走走,有必要。”
现在,喀拉峻的夜色里,我坐着。周围草地里随处都要踩到的一团风干或新鲜的牛粪马粪,像我一样,怀着燃烧的隐秘欲望和重新转化为草绿的可能性。有必要这样坐着,没有人知道,像坐在自我的尽头、尘世的尽头了。在尽头,一个人反而有可能获得转化的契机,像唐代诗人王维所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云起,草枯羊鸣。
此地属于夏牧场,处于海拔比较高的位置,牛羊可在这里逗留半年左右。当寒流渐渐从天山方向来临,牛羊就随着牧人转场到低海拔的冬牧场,那里有最后一片草地以及干草垛可供过冬。
在中年,我的生命时区,正处于类似夏牧场的位置吧?离领取退休金一类“干草”还有若干年的距离。我将逐步降低海拔,转场,到低处度过冬牧场一般的晚年生活。我需要天山、喀拉峻、伊犁、新疆乃至更广大的美、温存和感动,来构筑“干草垛”的重要部分,以供自己在晚年里回味、御寒——最初的草,影响最终的炊火和力量。
在天山下的夜色里预感晚年,渐渐安详、沉着。
我朝着草原深处的点燃的一堆篝火走去。
歌
逗留伊犁的几天,贯穿歌声。我们在餐桌上唱,在毡房里唱,在卧室里唱,在路上唱。用汉语、维语、哈语、蒙古语等等语言来唱。不唱的时候内心也回荡着某支歌的旋律。内心始终回荡着一支新疆民歌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恶棍?我唱着,听朋友们唱着,像被歌声洗涤后的树枝随风摇动——一路随处可见的白杨树枝,白杨树叶随风摇摆。我的双手练习随着歌声摇摆。
歌和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一路上,我看到十岁左右的男孩骑着马从身边掠过,听到孩子的歌。他们将骑到老、唱到老。父兄们骑着马、唱着歌在旁边引导这些孩子。在平均每平方公里十一个人的新疆,不唱歌、不骑马该怎样生活?在平均每平方公里两万六千人的上海中心城区,开车人如果一齐鸣笛将怎能生活?
在伊犁,多年沉默的我唱了或者听了以下民歌:《玛依拉》、《牡丹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伊犁河》、《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一杯美酒》、《奶茶歌》、《送我一朵玫瑰花》、《达坂城的姑娘》、《劝嫁歌》、《别离歌》、《你不要害我》、《美丽的姑娘》、《黑眉毛》、《撒阿黛》、《在银色的月光下》……“一首歌能够把非常散乱的光芒集中起来,把自然界互相隔离或区分开来的东西统一起来。”(里尔克)
围着酒桌,沈苇唱了《两只小山羊》,我唱了《燕子》。在新疆,在伊犁,这两首歌都具有兴发爱情的功能。“两只小山羊爬山着呢,两个姑娘招手着呢,我想过去呀狗咬着呢,我不过去吧心痒着呢。”沈苇在两只小山羊的掩护下心痒着哪。“燕子啊,听我唱歌我心爱的燕子歌,亲爱的听我对你说一说燕子啊。燕子啊,你的心情愉快亲切又活泼,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眉毛弯弯眼睛亮,脖子匀匀头发长,是我的姑娘燕子啊……”我在燕子的翅膀下心爱着呀。
1997年,与沈苇在苏州参加《诗歌报》第二届金秋诗会时相识。他带着两瓶伊犁特曲从新疆来,我从中原来,十多位诗人欢聚寒山寺。他当时就唱了新疆的酒歌,伊犁特曲就像伊犁河一样特别曲折地流过韩东、庞培、黑陶、长岛、叶辉、森子等等诗人们的肠胃了。再次相见,十七年后的当下,我们人到中年到伊犁。他的诗篇充满了西域木卡姆、刀郎、吴越小调混血而成的音乐性。
在新疆,一个人不唱歌是可疑的、可怕的。歌也都是情歌。唱歌的人都像是情人、有情在身的人。我多年不唱歌了,在内地的竞争理论、成功学的引导下,假装自己是一个可怕的人、无情的人,让周围竞争对手且疑且惧且回避。
在新疆,我暴露了自己脆弱、不安的本相——唱吧,爱吧。“在如此卑微的生活中,我能说些什么/ 最多说我爱我自己”,沈苇在《回忆》一诗中写下这句子的时候,一定没有看到两只小山羊后面存在两个招手的姑娘。而我在没有燕子飞过的生活里,连爱自己的能力,也早已丧失。
需要“山羊”,需要“燕子”,来帮助我们克服虚妄、恐惧、狭隘、阴郁。
需要“山羊”,需要“燕子”,尤其是人到中年,看见暮年。
特克斯
在特克斯县街头,询问“特克斯”的含义。一个卖奶茶的人说是“野山羊很多”,一个赶驴车的人说是“野山羊出没”。解释各有差异,前者强调了山羊的规模,后者强调了山羊时隐时现、往来不定的动感,但只有浩荡的山羊群才能对应于充满动感的“出没”一词,所以两种解释相通无碍。我,一个矮小的人,在周围群山里或者在上海的楼群间走动,根本不敢用“出没”一词。
抄录《特克斯县简介》:“特克斯位于亚欧大陆中部,处于中国古丝绸之路最西端的乌孙山以南、天山以北的特昭盆地,隶属于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全县总面积八千三百五十二平方公里,总人口十七万人,分属三十三个民族。境内四面环山,平均气温5℃,自古以来皆为避暑之夏都。有天山马鹿、雪豹、棕熊、天山羚、北山羊、雪鸡、松鸡、石鸡等国家一、二级珍稀保护动物。人工饲养的动物主要有新疆细毛羊、哈萨克羊、新疆褐牛、西门塔尔牛、荷斯坦牛、伊犁马及鸡鸭鹅等家禽;有遍及山区草原的天然雪岭云杉,分布于沟壑小溪旁的野生胡杨、白桦树;有野生珍贵菌种阿魏菇、羊肚菌等;有天山雪莲、石莲、野生贝母、党参、甘草、沙棘、黑加仑、麻黄草、野蔷薇果等珍贵野生药材。特克斯河作为伊犁河的支流贯穿全境,河源在汗腾格里峰北侧,由西至东流向喀德明山,与巩乃斯河汇合后再折向西流,与喀什河汇合,进入哈萨克斯坦。”
我在特克斯河边住了两个晚上。河水在向东流还是向西流?我无法辨别。这片土地上的事物都具有转化、转向、转折的能力,随物赋形。一个作家应该也具有转化、转向、转折的能力,持续给阅读者带来意外和震惊,让稿纸不断隆起、倾斜、覆没,建立起使文字奔流、跌宕、跨越边界的无限势能——天山、乌孙山像书房的南墙和北墙,文字应该像野山羊一样,出没不可胜数。
特克斯县城就是闻名中外的八卦城。民国初期,根据《周易》八卦“后天图”方位设计,从八个方向进入县城中心的主干道,衍生出六十四条支路,路路相通,形若迷宫。全城没有红绿灯和交通警察,开车的人只需要向前、右转就可以抵达任何一个目的地。《易经》的“易”由“日”、“月”二字组合而成。《易经》就是阴阳变化、日月流转之经,反对凝滞、僵化——所以,八卦城或者说特克斯县城没有交通堵塞现象。
一个作家从八个方向开始的语流,都必须穿越各种感官细节,最终抵达人的心灵,而不能在叙述的中途迷失方位感,或抛锚、爆胎于下半身附近某条小街旁边的隐秘花园。
八个方向的人流车流进入的特克斯县城中心,正在建造一个心脏般的太极坛。沿着盘旋的楼梯,站在尚未完成装修的坛顶,乌孙山、天山、特克斯河的光芒就一涌而来——我就成了特克斯的几声心跳、一馨心香?却闻到了自身的汗味和脚臭。我赶紧沿着楼梯下来,到特克斯河边冲洗自己。西域三十六国,此地属乌孙。乌孙的国王当年迎娶汉家女子之前,大约也是这样跑到特克斯河边冲洗自己。
西域三十六国的名字都很美,乌孙之外,还有楼兰、大宛、疏勒、西夜……
我的同乡岑参在唐朝骑马穿越这里,用河南南阳话吟诵:“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寒冷造就了一个诗人。”(奥登)而目前,仲夏,雪和梨花尚在天山峰顶以上囤积、蓄力,特克斯河里的水,依然暖和。
喀赞其的两个院落
在伊宁喀赞其街区游荡半天,看了两个院落。
其一,吐达洪巴依旧居。这是一个在俄罗斯做生意、十月革命时期逃回伊宁的塔塔尔族巴依(富人)的旧居。吐达洪巴依本身也是建筑师,他邀来全疆各地的好木匠、好泥瓦匠,历时三年建成了自己的家。院子阔达,融合了塔塔尔、俄罗斯、维吾尔、汉等多个民族的建筑风格,混血、跨界。俄罗斯铁皮屋顶在蓝天下发出反光。院子一角的露天小舞台上,有几个维吾尔族少年少女在为游客歌唱舞蹈。俄罗斯手工地毯、壁毯环抱了三十多间卧室、书房、会客室、餐厅。留声机寂静。壁炉里的大列巴(俄语“大面包”)寂静。一个富人的旧居成为景区,沙发和床空虚着,没有一个后人、亲人。吐达洪巴依在伊宁建立起了第一个面粉厂、第一个肥皂厂,成为了拥有良好声望的伊犁行政公署副行政长。这个院子后来成为了当地政府的办公室、印刷厂、四个画家的画室和住宅。哈萨克女导游对吐达洪巴依的几个妻子的卧室做了重点指引,她对这些女子所属族裔说不清楚:“肯定很漂亮的!我们新疆各族的女子都很漂亮的!”
其二,主人不知其名的一个当代院落。比吐达洪巴依旧居小许多。院子里停着一辆奔驰牌轿车。小菜园里有白菜、辣椒、西红柿、蒜苗在生长,蜜蜂嗡嗡着赞美其中的甜意,像诗人、阿肯(哈萨克语“歌手”之意)嗡嗡赞美着女子身体里的甜意。这个院落主人家的女子、孩子在午睡,在十一间有前檐的高大房子中的某些床榻午睡。屋门都很信任地开着,漫长的纱帐随风摇摆。我和朋友们放轻脚步。前檐下的走廊墙壁、门窗分别涂着蓝色、粉色。我在一扇门前止步,试探着挑开纱帐,屋内无人,地毯一角摆满了皮质的小鞋子、大鞋子、高腰长靴,甚至还有皮制的袜子!我问导游,主人为什么将自己的院落开放给游客?导游说:“院子的主人是个维吾尔族商人,经常在北京、上海做生意,想让客人们都来看看新疆人日常生活的样子,他不拍打扰,他的车也在这里不怕打扰,呵呵。”
在上述两个院落之间,我们乘马车看街景:哈依古丽刺绣店,依扎提酸奶店,三个维吾尔族孩子向我们的马车招手,天山服装店,墙壁、门窗涂满蓝、黄、绿、粉各色的若干民居,一个穿长裙怀抱西瓜的美丽女子慢慢走向喀赞其街道办事处,墙壁、门窗涂满蓝、黄、绿、粉各色的若干民居,六个老人坐在街头闲谈并与赶马车的人打招呼,内心火热的馕坑,吉尔格朗学校,金雕民族工艺品店,墙壁、门窗涂满蓝、黄、绿、粉各色的若干民居……
我问一个维吾尔族姑娘,这些五彩的墙壁寓意着什么?她说:“蓝色代表天空,黄色代表阳光,绿色代表生命,粉色代表……爱情吧?”我俩都笑了。在内地,墙壁大多都是一致的灰色、晦涩,像墙内人的心境也很灰色、晦涩一样。五颜六色的墙壁,至多在幼儿园内能够看到。所以,在喀赞其街区里与这些幼儿园一样的景象相逢,就看到了天真和爱意——同行的重庆诗人冉冉有名句:“这欣悦的相逢,是今天的大事,也是今生的大事。”
相逢,欣悦,在喀赞其的两个院落和婉转回旋的七彩街道上,我做着一件大事。
他们
与他们相逢也是大事。
高兴,作家、翻译家、出版人、前外交官。他的名字使一个抑郁的人都不好意思与他握手、拥抱、干杯。他大约也防止自己在悲伤的地方和时刻出现。他相逢的人群、辰光都应该很高兴。伊犁很高兴。但一个把本名掩盖起来的人,内心又有多少积郁、暗伤需要借助于“高兴”这一笔名来消解?此前,我和他只相互通过电话、发过短信,在伊犁初见如故交。他也属兔,我们在草原上相逢比较合适。兔子以狡猾著称——狡兔三窟。但它实际是在依靠忧患意识和迅疾的速度,在老虎一类属性的庞大、强悍者中间,活下去。两个兔子在草原上相逢,完全不需要智商。从众声喧哗的宴会上悄悄撤出,我们两人在星空下散步——星辰密集硕大如同葡萄在天空中的反光。散漫谈论着共同喜欢的东欧诗人米沃什、索雷斯库,以及当下各自的境况。我俩像两只兔子告诉对方自己挖掘的三个洞窟的位置在哪里,以便在不安的时候可以到那里碰头。
刘亮程,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这个在黄沙梁闲逛着用铁锹改变一条小水沟命运、用一根绳子纠正小树姿势的农民,如今在乌鲁木齐闲逛着,用笔改变内心的地貌。他在餐桌上鼓励我吃大蒜:“伊犁紫蒜,配羊肉,好!”我礼貌性地吃一点点,赶紧喝茶悄悄漱口咽下。我怕自己发出蒜味影响周围人。他不怕,大口咀嚼羊肉、紫蒜——他有力量影响别人,用掺杂着羊肉、紫蒜气息的文字影响文坛。一个人是他吃下去的东西。这几天,刘亮程总在路边寻找蒲公英,摘下几棵就直接吃起来,“嗓子有些发炎”,他对我解释。他文字里又将会出现蒲公英的气息了。在伊宁街头,他用八百元买了一个壮大粗野的石臼,上刻“自力更生”四字。他握着石臼棰,嘀咕:“这阴阳和谐的小世界啊。”大家笑。他发愁如何把石臼带回家去。我建议他把石臼摆在书桌上,激励笔杆像石臼棰一样深入生活的秘境。
王雁翎,作家、出版人。她背着硕大的专业照相机,捏着手机,与我一样繁忙地拍风景、自拍、互拍,在马上、路上、车上,拍。我们一边拍一边篡改卞之琳的《断章》:“你在草原上看风景,看风景的鹰在天上看你。照相机、手机装饰了你的眼睛,你装饰了一匹伊犁马的梦。”以哈萨克马为基础、与顿河马等杂交而成的伊犁马,繁殖能力、抗病能力、长途奔走能力都很强,高大,长鬃飞扬,像帅气的长发男子,使王雁翎动心。她反复与伊犁马合影,像与心爱者分手留影。她试探着抚摸马头的样子像即将失恋的人。摄影术的产生就源自于对告别的感伤。在伊犁,我发现镜头的密度约略大于人头的密度。依靠照片来回忆往事、辨认西部,是内地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王雁翎又独自去了喀纳斯,为今后回到海南岛后保持感伤的气质而积累素材。
阿苏,锡伯族诗人。他是1764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开始奉清廷之命自东北迁移伊犁屯垦戍边的锡伯族移民的后代。阿苏讲了西迁的历史:历时一年半;牛车向西,三千余名锡伯族官兵及眷属一路风雪;诞生或者死;如今在新疆繁衍生根的锡伯族人约四万人。“东北我还有五万多锡伯族兄弟姐妹。我回去过三次。”阿苏的汉语说得九曲十八弯,比我只有四声的汉语要婉转生动。他会说四种语言:“我们锡伯族人都会多种语言,舌头都柔软得像蜜糖,但灵魂像天山和长白山一样硬朗。”他唱锡伯族民歌《招魂曲》,我们安静,像树上空了的鸟巢一样安静,招引鸟儿归来。他被沈苇称为“麻袋歌手”,有一麻袋的歌藏在他的喉咙里、胸腔里。他写诗,认为“写诗就是唱歌”。他写了许多牛车向西、马头朝东的乡愁诗,再唱出来,像马叫一样直着嗓子唱出来。我喜欢这个人。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维吾尔族青年诗人。九十年代出生在新疆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间的绿洲。孤岛一般的绿洲,宁静、自足而又渺小。一个维吾尔族孩子独自走出绿洲和沙漠,到北京上高中,在江南读大学,用维、汉两种语言写诗,书写忧伤和孤独,但这忧伤、孤独明亮而有热力,是西域的忧伤和孤独。我在日常生活和写作中已经不敢触及这两个词汇。一个芜杂、晦暗、颓败的中年人,对这两个词汇应该保持谨慎和敬意。在伊犁分别的早晨,他与同时代的两个小朋友拥抱、依依惜别,顺便拥抱了我这样一个老前辈。我说:“好好写,好好生活。”他点点头,大眼睛里是单纯和明亮,像绿洲……
与他们在新疆相逢,比在内地相逢多了光照和热度——在新疆结果的情感,应该比内地的瓜果甜蜜?
另一首诗
借着喀拉峻草原毡房房顶倾泻而入的月光和桌上的烛光,写出《拟伊犁民谣:黑走马》,抄录于此,结束本篇:
白昼漫长的伊犁,黑走马那么黑,像夜的孩子
白杨树集聚的伊犁,黑走马那么黑,像夜的父亲
黑色的伊犁马在走,学习伊犁河九曲的姿势
黑色的笔尖在走,汲取伊犁河多语种的水声
诗歌给黑走马,马儿摇头,姑娘用歌声来安慰诗人
干草给黑走马,马儿埋头,姑娘用怀抱来收留牧人
马上的人呵,你看到伊犁就成了伊犁马下的人呵,你回到内地就改变了内心——
天山提高了心尖,雪一般干净了,有明月涌出更好
喀拉峻繁荣了心地,草一般吐绿了,有马粪滋育也好
黑走马那么黑,像孩子,在歌谣般短促的时光里,走
黑走马那么黑,像父亲,在流水般四散别离的尘世上,走

空中草原喀拉峻 黄永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