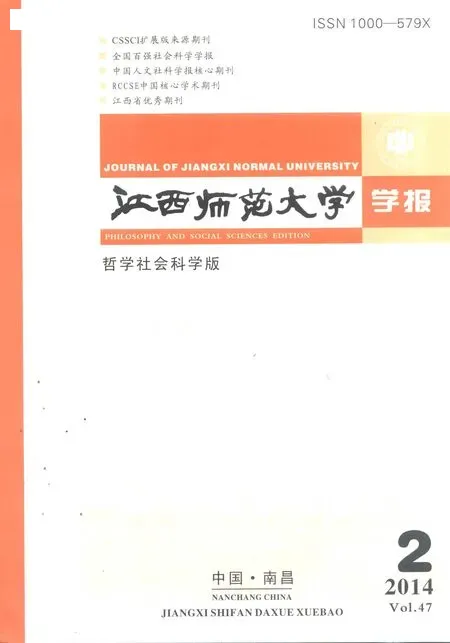明清通俗文学中医者形象的文化阐释
王 立,秦 鑫
(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大连116622)
古今通俗文学的题材范围十分广泛,然而,从通俗文学题材表现特征及其延续的角度,审视明清医者叙事所表现出的文化内蕴及其通俗文学特征,却少有人关注。借助于对《聊斋志异·医术》为代表的文言小说医术叙事特别是庸医形象文化意蕴的梳理,考察该母题与明清通俗文化中“通俗文学”的关系。
一、关于通俗文学、通俗性的界定
民国语境下的“通俗”包括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通俗’云者,应当是形式则‘妇孺能解’,内容则为大众的情绪与思想。”[1](p729)郑振铎先生解释“俗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通俗文学应来自民间,且为民众而作,为民众而生:“其内容,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的谈穷诉苦的心绪,不讲论国制朝章,她所讲的是民间的英雄,是民间少男少女的恋情,是民众所喜听的故事,是民间的大多数人的心情所寄托的。”他认为“俗文学”里的小说专指“话本”而言,诸如谈因果的《幽冥录》、记琐事的《因话录》等,所谓“传奇”、“笔记小说”等,均不包括在内。[2](p7)袁良骏先生强调:“‘通俗文学’一语来自‘俗文学’,而‘俗文学’本来泛指民间文学,是相对文人创作而言的。”他认为“通俗小说”是俗文学到通俗文学的桥梁。[3]范伯群先生指出:“我认为俗文学与通俗文学是属同一范畴的大小并不等同的两个概念。……我认为俗文学这个大家族中有两个分支:一支是当前称之为‘通俗文学’的分支,是指不属于纯文学范畴的叙事作品,主要是长、中、短篇通俗小说。而当前研究者通常提及的近现代‘通俗文学’流派,就是指继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模式的通俗作家群体。……一支是当前称之为民间文学的分支,指民众集体口头创作,经口头流传,并不断地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分支。”[4]后者情况与本文的论题较为接近,明清许多笔记小说如《聊斋志异》众多篇章,即属于“集体口头创作,经口头流传,并不断地集体修改、加工的”,不过由蒲松龄斟酌定稿。按一般观点,通俗文学的形式首先要易懂,如柳词般凡有井水处,皆能歌之。且其内容一定是关乎大众生活情感的,也就是其世俗性、社会性。简之,一要与世俗沟通;二要浅显易懂;三要有娱乐消遣功能。[5]据此,文人创作的文言性质的传奇、笔记小说等,往往不被认为是通俗文学。通俗性既有形式上的限制,又有内容上的要求,可是后者因范围广泛却往往被忽视。
号称“短篇小说之王”的《聊斋志异》,清初面世时也大半属通俗文学:“文言小说自然是由文人搜集、记录、整理的,或者是文人利用民间传说素材进行再创作的。无论是魏晋时的志人、志怪,还是唐传奇,亦或是文言小说的典范《聊斋志异》,其作品虽难免学一学太史公笔法,卖弄一下才情,用一些典故,却终究是供文人雅士茶余饭后消遣解闷的‘闲书’,书中又大量运用俗语俚词,算不得‘雅文学’之列。”[6]文言小说其实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被排除在通俗小说之外,而《聊斋志异·医术》二则故事讲述的正是蒲松龄不愿割舍的一个通俗文学、大众文化关心的重要题材。
可见,究竟应该如何界定“通俗文学”,其实可看成是相对而言的。通俗文学中的通俗之相对性未必非要体现在语言。明代袁宏道说:“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7](p882-883)意为表面文字不一定都通,而作品体现的世俗倾向可让普通读者理解明白。陈继儒《唐书演义序》也称:“演义,以通俗为义者。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迁)、班(固)、陈(寿)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为耳。演义固喻俗书哉!意义远矣。”[8](p1)界定通俗文学,应以总体文学格局参照。如相对于《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俗的。又像清代中期的《红楼梦》,时因以文人诗文为正统主流,小说戏曲上不了大雅之堂,其就是通俗文学,正所谓“开口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而伴随着文学创作中戏曲小说比重的增大,《红楼梦》有个经典化的过程,变得愈来愈雅,在当代无疑成为高雅文学的一个代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张赣生先生认为:“中国的小说,自‘小说’这一概念确立时起,它就与‘通俗’牢牢拴在一起。”“中国小说之通俗,最初是指‘通晓风俗’意义上的通俗,这种观念一直传到唐代……由‘通晓风俗’意义上之通俗小说。转化为‘与世俗沟通’意义上之通俗小说,这中间有个过程。”该过程主要指唐代变文兴起。“通俗小说”一词在汉语中的出现“是由于一次误会”,由“通俗演义”一词的仿词性误用而来:“中国小说自其确立时起就与通俗拴在一起,但直至明代中叶,却从来不用‘通俗小说’一词,其原因当然是明显的,按自由相沿的看法,小说必然与通俗相连,正如吃饭必然用嘴,只须说吃饭就够了,无须再说什么用嘴吃饭,画蛇添足,多此一举。”[9](p1-9)因而,小说(文学)的通俗与否,古代是与诗文(别集)相对而言的。研究时既要考虑到时代背景的因素,又要对文学文本深入挖掘,似不能只看到其语言形式,还更应看到其内容题材上的通俗性,医者形象及涉医题材即如此。
二、明清文言小说医者形象题材表现的通俗性
医者形象遍布许多明清小说中,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雅文学文本或俗文学作品。生病是无分贤愚贵贱的,与各种角色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深入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生老病死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有病求医成为世人必不可少要务的一部分,因而,医者形象常常构成了小说叙事母题,其形象本身就带有通俗性。这些医者或是作为单独的形象被抽象出来,或作为小说情节的重要一环而不容忽视。似不能因医者题材出现在文言小说中而将其排除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外,医者题材的通俗性亦不受到语言形式的限制。
无论寻常百姓还是大户人家,在遭遇病痛折磨时都希冀得到良医救治,而良医之所以为良医,多自有家传良方。然而,能治愈疾病者却未必都是良医。清初《娱目醒心编》有论:“更有一种医家,传得秘方,实能手到病除,起死回生,而所用药物,奇奇怪怪,暗里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说出来,可广见闻所未及。”[10](p223)《聊斋志异·医术》载两则医者故事,其一称贫民张氏遇道士相之,言当以医术致富,街市行医他碰巧根据自身经历,治愈了青州太守的咳嗽;又因醉误诊,反治愈了伤寒患者,益以声价自重。另一则写益都名医韩翁本是卖药的,碰巧投宿一家,其子伤寒,他无奈就搓体垢捻之如丸,不料病者服下汗出而愈。[11](p1547-1548)治病求医,通常百姓首先要找到有名气的医者,还希望他医术高明,用药入神。然而文中这两位医者,一个非科班出身,只因偶遇一道信其言,自以为医;一个胡乱下药,均误打误撞,侥幸成功。百姓将这类事件传播开来,自然进入文人笔下。同样的类化题材叙述,也出现在其他文言笔记如钮琇《觚剩·白蕈散》中的林茂、袁枚《子不语·摸龙阿太》的少宰之祖、慵讷居士《咫闻录·菜叶治病》的杨五、同书《医者》的徐某故事,医者角色均于偶然经历中获治病良方。然而作者在叙述这类事件时却是带着某种褒贬意识的。他们将此类故事诉诸书卷,将百姓关注的治病求医事展现在小说中,并有意为小说,把自己的感情融入之中,或褒或贬地表达对于医者行医的看法。虽为文言表述,但其所述故事却通俗易懂。
共同的民俗文化心理,更减轻了此类喜闻乐见故事的接受难度。对医德的重视,每多冲破了当事人文化层次的差别,生活难题变成了文言白话共同的故事母题。医术好坏直接干系着患者生死,不识字的百姓也明白。清代名医叶天士云:“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事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兼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12](p4)医德越高,求医者亦越多;反之,则会使医者被世人遗忘和恶名久播。然而,医至明清两代,其医德更是屡遭非议,诸如唯利是图、不恤病苦等字眼都被高频率地加之于医者头上。从明代《金瓶梅》中为官哥治病的任太医,到乾嘉时《阅微草堂笔记》,众多医者常常被描述为医德沦丧的化身。《阅微》卷八写某医见病人有姿色,非要此妇荐枕才答应救治其子。起初“妇与姑皆怒谇,既而病将殆,妇姑皆牵于溺爱,私议者彻夜,竟饮泣曲从”,却不曾想爱子已死,妇因悔恨亦投缳而殒,而贪色的某医也遭到家破人亡的恶报。[13](p162)同样,《萤窗异草》中的刘医,某日醉酒后看到隔江楼上一女色“不禁喜而长啸”,上楼为女诊治;[14](p233)该书三编卷一《沈阳女子》主人公赵三公因沈阳女子貌美而为其诊治,剪除狐祟,又因此女貌美想让其子娶之,终遭狐祟报复家破人亡。诸如此类的叙事带有实录性和新闻性,流露出憎医、惧怕恶医的民俗心理。
与大众感受贴近,世上医者的确贪色者有,贪利者更比比皆是。《夜谭随录》写某太医嗜钱如命,为人傲慢:“延者日积于门,非日晡不到病家,不顾病者之望眼穿也。每视一病,写一方,不论效不效,例奉千钱,否则不至也。日暮归,从人马后,囊橐尽满,人或怪其来迟,则色然曰:‘甫从某王、某公主、某大老爷府宅中来。’盖非一时势位炫赫者,不肯流诸齿颊也。人无如之何,任之而已。”太医较之平常医者,请之亦难。到底是“庸医杀人,当获此报”,结果被新鬼旧怨索命。[15](p257-258)《续子不语》卷十写名医汤劳光“凡求医者,非先送十金不治”。[16](p700-701)《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则写某医谨守理学不计后果,拒不出售堕胎药,梦被冥司拘仍无悔意:“药医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于我何有?”连冥司都不禁感叹:“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独此人也哉!”
清代小说中出现的医者的种种恶劣行径,均发生在百姓身边,对医者之庸良的关注实际上是普通百姓最为关心的普适性社会问题。而作者关注的这类生活事件及文学题材母题本身就极具普遍性、通俗性,他们将目光深入到寻常人的日常生活中去,洞悉他们何所悲,何所求,将他们的生活和情感渗入到创作中来。所以,就医者题材而言,它是最为通俗的题材之一,它叙写的是百姓身边事,言说的是百姓身边人,表达的是百姓(也包括载录者、传播者、创作者自身)最为通俗熟悉的情感。因而,我们应该抛开作品形式的限制,把眼光转入到题材上来,更加全面地关注医者形象的通俗因素。
三、由杂剧入小说:元明清医者形象的通俗化进程
文学名著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由于曲艺、戏剧、白话小说(续书)等艺术形式对它们的阐释延伸,但文言小说的阐释传播却未受到足够重视。诸元明杂剧、传奇中,通过通俗的艺术形式将医者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反映着当时大众对医者的看法和见解。根据臧晋叔《元曲选》、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统计,元杂剧中医生形象出现在十一部剧作中,姚大怀《再探元杂剧中的医生形象》将医者分成四类:“庸医”七位——《降桑葚》宋太医和胡突虫、《西厢记》“双斗医”、《张天师》的太医、《东墙记》的李郎中及《碧桃花》的赛卢医;“恶医”三位——《窦娥冤》、《救孝子》和《魔合罗》中的赛卢医;“良医”两位——关汉卿《拜月亭》中的大夫和《燕青博鱼》中的燕二;“义医”一位即《赵氏孤儿》中的程婴。[17]这十三个医者形象中,十个庸医。《窦娥冤》中的“赛卢医”其实就是个既开药店又行医的江湖骗子,内心歹毒又胆小怕事:“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王仲文《救孝子》的“赛卢医”,自我定位实为类化式的恶医群体:“我是赛卢医,行止十分低,常拐人家妇,冷铺里做夫妻。”[18](p188-200)孟汉卿《魔合罗》中“赛卢医”李文道,为了女色杀兄霸嫂,竟至灭伦。而良医形象元杂剧却仅有三位,如此三比十,大于“三七开”,足见元代民众对医者阶层的评价之低。元杂剧题材广泛、作品众多,均与其具有的通俗性有关:“与当时广泛的观众市场分不开。元杂剧扎根于群众之中,坚持其平民立场是得以繁荣的关键。……功能上也以娱乐为主的通俗戏剧转变为以批判为主的严肃作品了。”[19](p280)而《金瓶梅》第六十一回赵太医上场自道:“我做太医姓赵,门前常有人叫。只会卖仗摇铃,那有真材实料。行医不看良方,看脉全凭嘴调……”直接就是元杂剧庸医上场诗的延续。高小康延伸了夏志清的观点,认为对其“讽刺庸医……对社会风气的一种批判”从具体语境看却不能太当真,不过是取悦听众的老套路:“很难说是在严肃地批判什么东西。……叙事意图的矛盾性固然表明作品在艺术风格上的不成熟,但更重要的是表明一种新的叙事意图正在从民间叙事艺术传统中蜕变出来。”[20](p120-121)那么,针对文言小说为主的清代小说来说,这类批判的“严肃”与否,是否能作为其判定通俗性的标准?明清文言小说医者形象与元杂剧医者形象比较,大致有以下母题共通之处,题材内部叙事构成了母题史前后的互补。
首先,通俗文学代表的大众审美积习稳定而顽强,共有题材母题是其具有跨文体传播的文化能量源。医者、庸医成为上述元杂剧到明清文言小说描写的共同人物,以模式化、类型化手法引起受众兴趣则一。特别是庸医形形色色都逃不脱如是特征:粗通文字,略识药性;弄虚作假,草菅人命;坑蒙拐骗,麻木不仁。元杂剧中十位庸医医德败坏,而文言小说中医者则更变本加厉,更带实录性与概括性,时时有着载录者的“叙事干预”来强化。《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写业医的蒋紫垣有解砒毒良方:“然必邀取重赀,不满所欲,则坐视其死。”偏偏置患者的性命于不顾。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六《庸医》写其先外祖卧病时,众医互相标榜,商立医案,迁延月余导致病重,陈某遍视旧方,则叹“皆此等庸医所误”,患者过世不逾年,此数庸医亦相继死。而某名医之子,术本不精,每诊妇女脉,“必揭帐熟观”,后为一少妇治病,“竟以目成私合”,被其丈夫引妖鬼捉魂发疯而死。载录者感慨:
家大人曰:“昔人有言,士君子无以刀杀人之事,惟庸医杀人,其惨即无殊手刃,若复包孕邪心,乱人闺阃,则其孽愈重,某之暴卒,非妖鬼之能作祟,实其人之自犯冥诛。”纪文达公尝戏为集句以赠医者,有“医来寇至”之对,其言不为苛矣。[21](p251-252)
状写庸医之行事如此。可见无论杂剧还是明清小说,涉医叙事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言说庸医种种恶行,反映一种让人关切的社会状况,即医者素质普遍低下,大众对庸医的痛恨和无奈,带有揭露的力度和控诉的情感色彩,虽较少戏谑诙谐的娱乐之笔,岂不带有通俗性才构成传播?
其次,比起杂剧,文言小说写医者形象,虽追求娱众性的程度、风格情调有所不同,用情节新奇或插科打诨手法的比重有差别,但创作动机、采取叙事干预的意图颇为类似。据研究,明清统治者对行医者政策大不如前,医者地位下降:“清代康乾时期名医徐大椿,出身名门望族,家道殷实,又是一方名流,与社会上层人士有着广泛交往,其社会地位与一般医生不同,他本人并无轻视医学的念头,但他仍不愿视医为职业,而总强调自己的儒者身份。”[22]医者自己对行医职业本就看不起,何况识文断字者,因而医者尤其是庸医出现在小说家视野时,其滑稽可笑之态,愚昧懵懂情状便跃然纸上,成为野史笔记之首选的转述传播话题。酉阳野史云:“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23](p1)而相比“娱人”为主的白话通俗小说,文言笔记更成为文人(往往兼官员)自娱情怀和博物炫学之笔,若非大众认同的,恐怕也难于进入笔端和流传,故而文言笔记也无刻不追求叙事之新颖奇特。《聊斋志异·酒虫》就将一位僧医治嗜酒怪疾过程言说得新奇有加。说番僧看出体肥嗜饮的刘氏不醉,因有“酒虫”,运用燥渴法诱出了其腹中游鱼状的“酒之精”,可加水制成佳酿,而刘居然自此体渐瘦,家日贫。故事本身的新奇性契合了大众审美趣味,而实际上这是一个中古佛经以降持久不衰的惯常母题,如同其他众多类似母题一样,有着深刻的讽喻性和持久的母题延展力,[24]并不违背通俗性的审美取向,只是语言简约典雅而已。
其三,通俗文学母题的模式化、复制重组性质,在医者故事、庸医叙事中表现得较为突出。明清文言小说总试图在旧有题材中引人入胜,《聊斋志异·医术》即为代表。蒲松龄对于前代戏曲小说医者医术题材的沿袭重构,倒是颇为类似欧洲通俗文学大师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作品之伟大,其事实上并不表现在严格意义上的独创,美国学者不无夸张地强调:“实际上,莎士比亚从未创造过自己的故事情节。故事的讲述是一个长期采集的过程,相较于艺术审美性来说,故事原始材料的传承方式更具探讨价值。学者们追溯莎士比亚的材料来源时,发现其素材都可在此前的记录中得以还原。……莎士比亚能够得心应手、收放自如地驾驭作品的素材,娴熟地将其编织于更新颖、更具独创性的结构之中。”[25]只是中国的文言小说描述医者及其行医过程,更为简洁,思想容量更大,叙事干预体现得也往往较为隐蔽,且偏好强调得之于见闻的实录。
其四,明清医者形象的通俗性不仅体现在文言小说题材上,也体现在其他艺术形式对其传播上,因而是一种重要的世俗文化现象。可以说,许多文类都少不了。如汤显祖《牡丹亭》第四出《腐叹》介绍陈最良的出场,在读者的潜意识里陈最良是迂腐老儒生的代表,殊不知他还是医者出身,因仕途不畅改行医,继承祖父的药店维持生计,可谓“儒变医,荣变韲”,在作品中他是亦儒亦医的形象。冯惟敏《归田小令·朝天子》将医、卜、相、巫四种人的手段概括得十分贴切,说医:“把腕儿绰筋,掏杖儿下针。无倒段差分寸,处心医富不医贫。惯用巴霜信,利膈宽胸,单方吊引,几文钱堪做本。泻杀了好人,治活了歹人,趁我十年运。”[26](p92)将医者的从医心态和行医心理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清代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刘高手治病》开篇就讽刺了“名医”徒有虚名:“论时医自我观来如狼虎,病者遭之似夺命星。他哪知名医如名相有关生死,他只晓趁我十年运且博虚名。……”蒋世隆患病请来了名医刘弘景,后者一进屋便要给蒋妻王瑞兰看病,连病者是谁都辨不清,提醒后又急忙称自己年高眼花。“猜病法”浪费不少时间后,从他人口中了解病情,又急着开药方,亲自试药,但药入口就呕吐了,原来忙中有错:“这原来是我家婆擦脚的矾。”[27](p329-332)无法对症下药就以多开、苛求煎药之水和相关配料取胜。这些,都会引起有着类似经验的大众文化受众深切的共鸣。
总之,“通俗性”是一个超文体的文化概念,[28]许多大众关心的、持久传播的故事母题,如医者形象及其行医叙述之类,无论白话小说还是文言笔记,抑或戏剧,都带有十分浓重的通俗文学特质。虽然也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多半是伦理叙事方面的探讨,却罕有注意到医者题材史的通俗性动因,以及对于社会不平现象关注的责任感。应当说,就其题材选择而言,通俗文学,言说的是大众生活最为关心之事,不断重复着唠叨着的,基本上都是真实的社会问题、需要疗救的世俗顽症,其本身就具有通俗文学的性质与特征,足证“通俗”的判定应与社会流通的频率范围相关,具有相对性。谈文学作品的通俗性需要将其置于时代、社会、人类多民族文化共通性的大背景中来,[29]关注母题的丛集性和持续性,以及诸如相关的技术表现手法的跨题材、跨国性传播,[30]从而有利于更全面深刻地认识通俗文学的通俗性。
[1]茅 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下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2]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袁良骏.走出“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误区[N].人民政协报,2004-04-05.
[4]范伯群.通俗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1).
[5]刘安海.通俗文学的美学特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6]罗立群.中国小说雅俗论[J].社会科学战线,1993,(4).
[7]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9]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10]草亭老人.娱目醒心编(卷十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1]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M].济南:齐鲁书社,2000.
[12]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13]纪 昀.阅微草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4]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
[15]和邦额.夜谭随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6]袁 枚.子不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7]姚大怀.再探元杂剧中的医生形象[J].语文学刊,2009,(19).
[18]臧懋循: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0]高小康.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1]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九册)[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
[22]刘理想.我国古代医生社会地位变化及对医学发展的影响[J].中华医史杂志,2003,(2).
[23]酉阳野史.续三国演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4]王 立.《聊斋志异》中印溯源研究的学理依据及意义[J].求是学刊,2012,(2).
[25]〔美〕哈利·列文.莎士比亚作品主题的多样性[J].王立,铁志怡译,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26]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7]张寿崇主编.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28]王 立,秦 鑫.明清小说中的医者形象研究综述[J].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29]王 立,刘卫英.明清雹灾与雹神崇拜的民俗叙事[J].晋阳学刊,2011,(5).
[30]王 立,郝 哲.韩国古代汉文小说“预叙”与中韩文化融合[J].东疆学刊,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