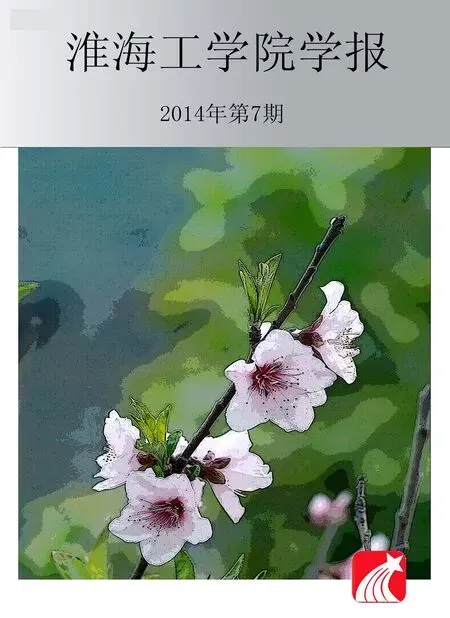历史与现实的艰难苦渡
——评方方的《闲聊宦子塌》*
李 苗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连云港财经分院 语文教研室,江苏 连云港 222006)
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闲聊宦子塌》是方方唯一的一部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她“像一位淘气大胆睿智张狂的精神漫游者,在迷雾般的洪湖水乡宦子塌”,“‘淘’取出相当意义的‘历史内容’和人性蕴藏”[1]32。这篇小说既有历史文化意味,又饱含了一个心怀理想的作家无法摆脱的精神痛苦。
一、冷静睿智的平实抒写
“当小说重在客观事件的描述的时候,它是发扬故事的传统,小说成为再现社会生活的艺术化了的历史。”[2]135《闲聊宦子塌》正是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审视当代宦子塌人的生活。方方把眼光投向了当代宦子塌人商品意识的萌动:胡幺爹爹的满腔仁义感化不了钻在钱眼里的儿子儿媳;高中毕业的天壮原先的理想是不种田,能赚钱,干什么都行;靠贩卖野鸭发起来的田享生,在胡家危难时想趁火打劫低价买房,这些鸡毛蒜皮、恩恩怨怨的小事构成了他们一生中重要的事。作者立足于宦子塌人的生存现状,以冷眼旁观的姿态,真实地揭露人们不敢正视、不愿正视却真实存在的生存欲望,将这种残忍、冷酷的人生世相写得细致入微,动人心魄。正如费振中所说,生活的真实就是它本身的真实,没有生活的真实就没有本质的真实。方方揭示出人性自身的弱点和周遭环境的不足,她采用的是针砭法,而不是急火煎熬和矛盾冲突的剧烈激化,作者透过历史的尘埃,冷静谛视人性欲望的变异。
方方描写人物,不是从“价值”层面去做是非善恶的评判,而是从“存在”的意义作“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复原,作者以精神守望者和人性阐释者的身份,展示多样复杂的人生和人性,形成多维广阔的舞台,尽显人生世相。宦子塌闭塞的生存环境、大富的投机和自私心理,由此而衍生的愚昧和贪欲,这都是以基本的物质层次和人的本能要求为出发点的。由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需要,继而延伸描写欲望满足而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展示人生挣扎过程中产生的利用、反叛与伤害的冷酷形态。原本和蔼可亲的老红军,一旦遇到切己利益的事,立即翻转人生镜相,露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即使他后来试图用毫无价值的金钱来赎罪,却永远无法弥补人格戕害造成田七爹爹的命运错位。现实人性的匮乏与异化,人生价值的缺席与虚空,造成一种历史与现实的陌生感与荒谬感。
面对人世的残酷无情,作家不是表现出迎起抗击的姿态,而是以温和的解构粉碎现世的不合理与虚妄性。田七爹爹日日看河,想从清澈流动的河水中寻找人生的答案,但老红军斩钉截铁的回答“您认错人了”,使他一生的期待付诸东流,他在默默中到另一个世界中继续他的守望。作者以冷静演绎的方式,从容叙述人生存在意义的荒诞,咏叹人生命运的荒漠性和无希望感。方方以“身份还原”的方式,将文学还原为作家个性化的创作,忠实于自我感受,体验并阐释生命与人的存在形式。
现实主义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写实性、批判性、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以及那种虽然难以测定但可以在阅读的接受体验中获得相应印证的‘真实性’”[3]65,这种卷入现实的手法,增强了作品的共鸣性与艺术生命力。《闲聊宦子塌》描写了人类生存状态中的一种群体类型,是民族背景、民族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人格观念的再现,作者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在对人生世相的解剖中透出几分冷峻,她要求环境改观和人性改善的愿望与“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一致的。同时,方方对凡俗人物生存景况和生活状态的还原是以本真的状态出现的,这又使她的创作具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外观,如行云流水般自然顺畅。“对生活的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形态,而对生活的还原,则是现实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带着某种自然主义外观的现实主义形态。方方小说的现实主义,同时具备了这样两种形态。”[4]同时,对久远的民族传统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反思,又使这篇小说具有寻根色彩,显现出超越性眼光和审美态度。
二、无奈悲婉的命运主题
田七爹爹以沉默的方式执着坚守命运转机的虚妄,胡幺爹爹与秦家麽麽疯狂热恋而又中道崩溃的性格悲剧,天壮与喜鹊相爱却终不能结合的命运劫数……方方以每一代人的当下观念为基点,以三家三代人的命运回响呼应主题,书写出历史宿命与人世无常的尴尬。
悲剧“产生于那种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在世人面前的形象被剥夺而不可避免地引起的灾难中”,这是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的观点,也是田七爹爹一生悲剧命运的写照。命运“实在太奇怪太玄妙太变化莫测了”[5],由于偶然间的误认,原本是革命功臣的田七爹爹一直被历史遗忘,甚至背着反面角色的黑锅。偶然形成的人生命运的歪曲轨迹,成为人物命运的强力制导因素。这种人物命运的无序状态,是混乱年代价值错乱的直接后果,是凭个人力量无力控制的命运玩弄,显示了历史的残酷和命运的脆弱,这是对人的生存状态无法把握与预定的无奈,也是对历史与现实复杂多变的清醒认识。
面对现实的随意性、偶然性和机会性,方方“为生活规定了那种悬而未决的态度,表现了我们置身的世界间的事物之意义和关系的一种根本易变性的宽睿”[6],这种“类戏剧式”的生存状态,使虚假的价值在历史的沉淀中遭到嘲弄与轰毁。田七爹爹日日等待契机的出现,长期的沉默是以内心的挣扎与分裂为代价的,它随生命的存在而永不停滞;金枝用青春的等待来回报意外的事故,作者将生命存放在偶然与良知领域、生命情感的基点上平衡轻重,结果生命在孤寂中耗损,激情在岁月中流逝,这种理想主义的毁灭是对命运主题的无奈体认。
《闲聊宦子塌》打破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将过去与现在的悲欢离合放在一个命运之网中审视,营造出无出逃遁的复合命运空间。在直接显示与间接暗示中,方方进行“代际轮回”的命运设置。胡幺爹爹与秦家麽麽的激情野合,燃烧的欲望一直延续到隔代遗传的孙辈中,缠绵疯狂的热恋使他们几乎成为乱伦的牺牲品,在自然遗传的壁障上演出了一幕情欲宿命的悲剧。在这里,“社会—历史性的因素滤除得更加干净,蛮荒的自然和狂野的生命直接合一,显出一种亘古的神秘,关于人物和行为的价值判断也渐渐隐退,力图展现一种非道德伦理所能评价的神秘欲望的原生形态”[7]139,这体现出“浪漫主义”的生命冲动。情爱绝望与价值虚无,是命运的荒诞游戏,任何的挣扎与呐喊在它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定数。
对人的生存的某种不可捉摸的虚幻感觉,遭遇生命伦常的强大支配与压制,形成这篇小说温婉哀伤的情感色调。方方对这些历史与现实处境中的边缘化群体进行逼真的再现,不是疯狂的自毁与报复,而是制造出一种富有诗意的“间离效果”,在时间的搅拌机中粉碎命运的石块。田七爹爹的默默忍受与喜鹊的安命乐道,使巨大的命运悲剧在历史中被遗忘与超越,形成另一道人生风景。“劫难,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悲剧,也以不同形式代代相续”[1]98,不同于希腊悲剧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方方展示的是普通人对命运的无奈天问。
三、互汇交叠的叙述语态
《闲聊宦子塌》是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互汇交融的文本结构,形成历时与共时交错的关联域。方方的历史叙事进行了大量的横断面处理,移步换形,采用类似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逐一叙述,在一个横截面展开一系列情节,这些碎片式的场面,构成共时性艺术,又符合历时发展的逻辑,既粘合又顺连,形成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小说叙述了平原凹地宦子塌的历史,介绍了它的形成地貌,巧妙打破时间链条,在同一时间里展开不同层次上的行动和情节,来回切断同时发生的若干故事,中止历时叙述的时间流动,并对时间进行分排组合,形成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的统一。作者将胡幺爹爹、田七爹爹、秦家麽麽的过去史拉到现在时进行叙述,形成“现在”与“历史”的互文对照,打破历史的迷障,容纳高度浓缩的信息量,形成强有力的张力场效应。
“人物身份的倒置,愿望与效果的倒置,以及倒置的反向重复,便成为方方结构小说的重要艺术手段。”[8]方方将田七爹爹年轻时的贡献与老年的凄凉、天壮与喜鹊的情爱宿命对老辈的轮回,在逻辑与价值中展开历史时间,进行精神反思。作者跨越时间限度,将它扩展到价值与命运之谜中,通过这一“时间的召唤”,达成对人格、人性的透析。大富以投机坑骗赚钱来审视胡幺爹爹的忠直穷酸,用新的价值意识“审父”,而天壮又在上两辈的压力下重新审视他们的选择,这种双向的相互审视,是一种精神交流,是过去与现实的对话。历史是割不断的,既有时间的链结,又有精神的延流。
方方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自由间接引语,即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叙述人物的语言、思想感情,以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形成某种潜在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寓言内涵。荆河水生生不息的流淌、木瓜的先知先觉,借这些意象或悬念解读故事,同时它们的存在又大大造成情节的模糊性、多种可能性或某种象征性,使故事的意蕴丰富,结果一个平面的故事形式扩充为一个立体的氛围。木瓜坚守在别人看来荒诞的看河行为,识破胡秦两家的微妙关系、预言尚未发生的事情,这些具有符号化的倾向和象征色彩的情节,增强了写实性小说的陌生化效果,使小说的题旨具有多意的内涵。象征性艺术经由写实描写,并使它具有象征指向,超越具象而形成深刻的寓意目的,这种表现手法和叙述角度的变换,使方方的小说具有现代主义的色彩,形成交融着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小说叙述方式。
语言是艺术本体的一部分,也是有价值和意义的符号系统。方方对语言刻意翻新,使其具有多层意蕴,由个性化层面上升到文化功能层面,形成智性精巧的多味语言风格。《闲聊宦子塌》以优雅的语态使文本富有历史文化的诗性美。宦子塌的自然景观,富有民族色彩的孝歌和小调,传达出宁静古远之气,悠悠地传出了宦子塌这块远离都市土地上的生民们对相对稳定而又古朴的文化心理。另外,写实语言和象征性话语交相渗透,人物性格被方方描写得逼真而精细。富有方方特色的语言,灌注的是历史文化的深度内蕴,对当下人性的透析和对生命存在的独到的理解。
方方的探索从意蕴到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尝试,显示了一个作家应有的敏锐力和判断力,也为当代文坛的创作开创了一条有意义的新路。
参考文献:
[1] 李俊国.在绝望中涅磐——方方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2] 王先霈.徘徊在历史与诗之间[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3] 周政保.精神的出场——现实主义与今日中国小说[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4] 陈骏涛.在凡俗人生的背后——方方小说(从《风景》到《一唱三叹》)阅读笔记[J].小说评论,1992(5):9-14.
[5] 方方.何处是我家园[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6] 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J].文学评论,1993(2):88-100.
[7] 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 王绯,华威.方方:超越与品位——重读方方兼谈超性别意识和女性隐含作者[J].当代作家评论,1996(5):6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