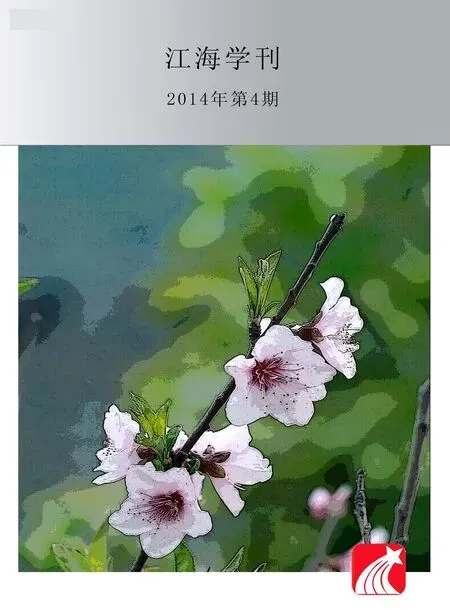从乡村社会变迁反观熟人社会的性质
陈柏峰
“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目前已经成为人们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描述。这一描述最早来自费孝通先生,但他并没有明确将“熟人社会”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熟人社会”概念是伴随着“半熟人社会”概念的建构而逐渐丰满起来的。这两个概念的建构,是在对乡村社会巨变的深入观察的基础上完成的。如果深入观察乡村社会,就会发现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既有表面上的社会形态的变化,更有深层次的村庄社会性质和内生秩序机制的变化。这些剧烈变迁,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理解,因此需要对社会巨变过程中及之前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和秩序机制有着深刻的把握。“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概念的建构正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中。
“熟悉”和“亲密”
最早人们是从“熟悉”这一层面来理解乡土社会的,这也是将乡土社会理解为“熟人社会”的基础。费孝通对乡土社会的理解非常多面,“熟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他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
苏力在对基层法治的研究中,沿用了“乡土社会是熟悉的社会”这一论断,将法治在乡土社会的实践过程与后果的考量和分析建立在乡土社会成员“熟悉”这一基础上。例如,在对一起强奸“私了”案件的分析中,苏力从“熟悉”出发论证了当事人的“理性”。因为社会成员熟悉,信息传播和交换非常快,提交司法程序不利于强奸案件中受害人的名誉保护,相反“私了”可能更有利于受害人的未来生活。在对基层司法的分析中,苏力也将“熟悉”、信息等要素纳入考量因素中来分析司法制度的具体运转。例如,在分析“送法下乡”实践时,强调村干部作为地方性知识载体的重要性。因为村干部熟悉村民,掌握着司法权力影响的对象的具体知识和信息,包括当事人的个性、品行、脾气、家境等,法官在送法下乡的法治实践中需要却不掌握这些地方性知识,因此必须依赖作为其载体的村干部。
贺雪峰最早用“半熟人社会”来描述行政村范围的村庄社会性质,其着眼点在于行政村内人际关系的“熟悉”程度相对村民小组而言较低。行政村的范围在人民公社时期相当于生产大队,村民小组则相当于生产小队。生产小队的规模一般有200口人、30户左右。生产小队在人民公社时期是日常生活劳动和会计计算的基本单位,是高度熟悉的熟人共同体,也正因为这种熟悉和信息透明,互相之间的劳动监督变得简单易行,因此才可能在半个世纪中成为较为稳定的劳动与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则超出了所有村民都非常熟悉的范围。在生产大队范围内,往往只有大队干部才对所有村民较为熟悉,村民之间的熟识范围较为有限,往往只是“面熟”而不知根底。改革开放以后,生产队变成了村民小组,虽然村民小组的生产功能在制度上日趋淡化,但农民的生产合作往往还在这一范围内进行,生活方面的很多功能还是在这一范围内实现,比如人情往来、生活价值实现。因此,从熟悉和信息透明的角度来看,村民小组仍然构成熟人社会,行政村范围内则是一个半熟人社会。
贺雪峰的上述描述主要建立在人民公社后乡村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社会变迁的基础上。而随着改革的深入,乡村社会发生了更为剧烈的变迁。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农民外出和流动增加,就业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非农收入成为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村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村庄社会日趋多元化、异质化、去熟悉化。村民们的观念不再划一整齐,而是有了多元观念,不同人群、阶层、家庭和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人们的隐私观念越来越强,对喧闹的容忍程度也逐渐变低。村庄内的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模式都在不断变化,家庭生活私密化程度越来越高,串门聊天大为减少,尤其是过去那种如入无人之境进入他人房间的现象逐渐变得不可理喻。如此,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就需要新的模式和公共场所,村庄生活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村庄发生了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有熟悉程度降低的原因,更有“亲密”程度降低的原因。
因此,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乡村社会变迁来看,从“熟悉”去理解熟人社会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从信息透明去理解“熟悉”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至少还需要从“亲密”这一维度去理解“熟人社会”。正如费孝通所说:“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
地方性共识
如果仅仅从“熟悉”去理解熟人社会,荆门农村农田灌溉合作中“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怕饿死的就会饿死”的奇怪现象,就可以被理解为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在农田灌溉合作中,由于村庄是一个熟悉、信息透明的社会,村民们对彼此的性格非常了解,因此公益心高的农户或对利益算计特别敏感的农户,就会成为每次公益行动中其他村民期待的对象,其他村民什么也不做,却期待公益心高的村民为公益性行动支付成本但不得好处或只得较少好处。这些公益心高的村民因为在每次公益行动中都付出较大成本,得到较少好处,从而在经济上被边缘化,不但没有因公益行动获得赞誉,相反却因经济边缘化而成为村中说不起话也办不起事的贫困户;而那些总想搭便车也总是搭上便车的村民则成为他人公益行动的最大受益者,并逐渐成为村中中心人物。“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怕饿死的就会饿死”现象,导致热衷村庄公益的村民受到嘲笑,反受其害,必然导致村庄社会的不可持续。
因此,熟人社会并非仅仅是信息透明、知根知底,在费孝通那里,熟人社会不仅熟悉,而且“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这种规矩可以称之为“地方性共识”。地方性共识是村庄熟人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共享的具体知识,这种知识可能也不局限于村庄之内,而为某一区域内人们所共享。地方性共识是人们从日常生活中“习”出来的,以“从心”的方式“从之”。地方性共识是人们生活和行动中的理所当然。因此,通常情况下,遵守地方性共识是内在的,感受不到外在的压力。地方性共识是熟人社会的人们在行动中的政治正确和身体无意识,按照地方性共识行动是无需思考的,更无需论证,它甚至可能成为其基本情感的一部分,违反共识可能导致情绪性反应和焦虑不安。在熟人社会中,人们有着许多不容置疑的地方性共识,村民个体往往缺乏质疑地方性共识的能力,地方性共识构成了一种判定何为正确,何为应当的个体行为标准。
地方性共识是村庄熟人社会秩序的维系基础,而缺乏地方性共识,信息透明、知根知底可能导致村庄熟人社会的瓦解。丧失了地方性共识的村庄社会,人们也许仍是熟悉的,信息也是透明的,但这种熟悉反而成为大家互相算计的基础,结果是人人利益受损,村庄社会基本秩序无法维系。在当前中国一些地区的村庄,村庄信息仍然透明,但地方性共识却已经瓦解,新的共识尚未定型。这种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变迁,正是熟人社会瓦解的表征。而正是经由这种变迁的观察,才能更深刻体味熟人社会的性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流动的增加,乡村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农民就业多元化,收入发生分化,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庄结构解体,村庄边界日渐模糊,村庄社会出现了多元化和异质性的增加,过去习以为常甚至无需语言沟通的地方性共识解体,村民的就业、收入、交往、兴趣、品味、秉性、需求都出现了差异,地方性共识因此不断瓦解,甚至在信息沟通上,村庄也出现了与之前熟人社会有所不同的逻辑。伴随着村庄边界的模糊,现代性的各种因素向乡村社会全方位渗透,例如,以广告和时尚为工具且带有强烈消费主义特征的现代传媒进入农村,现代的个人主义观念进村,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进村等。相对封闭的村庄开始解体,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被挤压,传统的地方性共识越来越边缘化。乡村社会中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歧义纷争,社会秩序出现了“语言混乱”,甚至于种种因素导致熟人社会趋于瓦解,村庄社会面临着社会解组的“结构混乱”状态。
乡土逻辑
地方性共识包含价值与规范,是农民行为的意义系统和规范系统,由其形塑的农民的行为逻辑,则是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它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熟人之间的“情面原则”,二是情面原则衍生的“不走极端原则”,三是情面原则衍生的对待陌生人的“歧视原则”,四是情面原则衍生的“乡情原则”。伴随着地方性共识的瓦解,农民价值系统越来越动摇,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和地方信仰,逐步与迷信、愚昧、落后、不理性等负面价值画上等号,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及时行乐”,村庄中不断出现各种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荒唐事情。
从笔者研究的与乡村混混有关的实践来看,乡土逻辑的变异显而易见。由于乡村混混的生长和介入,熟人社会内部出现了对待外人和陌生人的歧视原则和暴力化处理方法。在本该讲人情和面子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却越来越倚仗于暴力,人们正在以传统社会中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父老乡亲,对待那些从前被认为类似于自己的父母兄弟的“熟人”。生长于本乡本土的乡村混混,正在以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对待本乡本土的村民,他们不遵守熟人社会的情面原则,对于村民而言,他们本来是熟人,却正在变成陌生人;而那些外来的乡村混混,他们本就是熟人社会的陌生人,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气焰嚣张,在村庄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中肆无忌惮地“撒野”。因此,乡村混混是老实本分的村民眼中的“陌生人”,这种“陌生”并非交往关系上的陌生,而是乡村混混用对待陌生人的歧视原则来处理原本熟悉的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完全不按传统的情面原则行事,是一群行为无法预期的陌生人。人们遇到摩擦和冲突时,不再按照原有的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处理相互间的关系,而是动辄倚仗于暴力。
乡村混混对待熟人社会内的村民肆无忌惮,强者不惮于将村外的混混引入村内,他们日益残忍地对待弱者,这背后就是不走极端原则的衰落。“忍让”不再是村庄社会的公共性价值,也不再是可欲的生活方式,而越来越成为弱者避免强者赤裸裸的暴力的自我保护方式。村民的生活预期越来越短,人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仅仅看重物质的好处,而置道义于不顾,面子等表达性收益不再是人们追求的对象,人情再也无法将现实的利益裹挟到长远的村庄生活中去。他们不再珍惜因世代在一起生活而积累起来的感情,更加不会为了未来和后代的生活去积累感情,日常行为不断走极端,互让伦理不断衰落。
同时,乡情原则也在衰落,村庄越来越只是村民暂时的聚居地,而丧失了魂之所寄的重要意义。当村庄精英离开村庄后,不再那么关心村庄的发展,那些做混混发迹的“村庄精英”更是如此。他们不再在乎自己在村庄中的名声,他们的生活目光是向外的,生活价值和意义也在外面的市场经济中获取,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样,当一个村民朝着乡村混混的道路发展时,村庄舆论对他几乎构不成压力。因为在他们心中,村庄并不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固定生活空间,而是一心要摆脱且轻易就可摆脱的暂时落脚点。当村民将外来的乡村混混引入村庄时,他也不会受到指责;当外来混混进入村庄时,村庄也难以组织起来进行应对。
传统熟人社会中,地方性共识和乡土逻辑能够保障乡村秩序的良性生产,维系乡村生活的道德秩序。伴随着地方性共识的瓦解和乡土逻辑的日趋变异,乡村良性秩序的维系日益艰难,道德秩序日趋瓦解。正是在这种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深刻理解熟人社会的性质才更有可能;而更深刻理解熟人社会的性质,才可能更深入地进行“半熟人社会”的概念建构,以及提出其他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