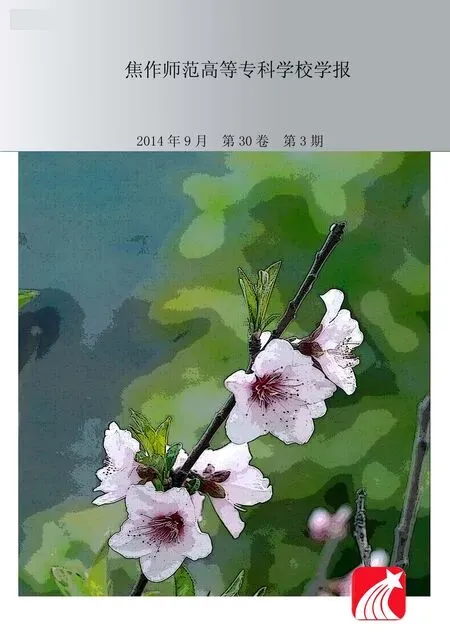北魏中心经济区的营造及其影响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史学界对北魏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对北魏前期社会性质以及迁都前后均田制、三长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诸问题建树颇多,亦对北魏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做出过一定探研*相关研究参见: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岳麓书社2003年;[日]掘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陈玉屏:《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拔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张继昊:《从拓拔到北魏——北魏王朝创建历史的考察》,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孙同勋:《拓拔氏的汉化》,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62年;吕清培:《北魏孝文帝的华化运动》,台北:华明出版社1969年;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相关论文散见文内注。。笔者认为,如果把北魏经济史作为一个整体,把时间角度的从游牧到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化进程,与空间角度的对中心经济区的营造过程结合起来,做一定程度的综合研究,或可有助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并相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必要性。同时,笔者推想,既然均田制,如被目前研究所高度肯定、对北魏生产方式的转型具有决定意义,而与此同时进行的迁都洛阳之举更是拓拔鲜卑汉化的关键步骤,那为何在实施不到五十年后,北魏不仅没有因此走向繁荣并进而发展到盛世,却反而迅速分崩离析直至陷入东西分裂呢?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探讨北魏先后对以平城和洛阳为中心的两个经济区的营造作为国家经济一体化*理论上讲,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东方亚细亚社会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加之受制于交通和地理因素,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论是统一的王朝,还是疆土辽阔囊括多经济地理单元的王朝,在实现政治大一统的同时,无不致力于国家各经济区域的整合,以巩固政治统一的成果。如秦始皇修灵渠以开发岭南,隋炀帝修大运河以沟通南北交通,等等,都是统一王朝致力国家经济整合的时代壮举。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以农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特点,要求王朝统治者必须为该王朝的经济统一体构筑外围屏障,防止草原游牧民族的掳掠。如从秦始皇开始历代之修筑长城。笔者将这一行政努力命名为国家经济区域整合。的基础,同时以上述探讨为基础,对北魏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经济政策力求新解,以期增加学术界对北魏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一、北魏中心经济区的营造
(一)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经济区的营造
北魏建国后,国家经济重心迅速实现从旧都盛乐向代北重镇平城的战略转移。这也是北魏统治集团选择农耕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虽然生产方式的转变非朝夕可就,但是北魏统治者通过对被征服地区民众的强制移民,并将移民以“计口授田”方式安置于代北平城地区,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战略意图。在转变生产方式的同时,北魏逐渐营造起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经济区*相关研究参见:高平:《拓拔魏往京师平城大规模迁徙人口的数字、原因及其影响》,载殷宪、马志强:《北朝研究(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62-81页,等。。
历史的契机发生在西晋末年。本来以盛乐为中心从事游牧经济活动的拓拔鲜卑,“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百姓乂安,财畜富实”。直到昭帝禄官元年,穆帝猗卢“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1]6,开始进入代北地区。猗卢从西晋并州刺史刘琨手中获得大片土地,“乃徙马邑、阴馆、娄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1]7。这片代北土地的获得使猗卢开始对平城产生兴趣。三年后,拓拔鲜卑便“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1]12。由于此时拓拔鲜卑仍然以游牧生产作为主体经济,因此昭成帝什翼犍三年(340),仍然“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1]12。
北魏对代北经济区的营造始于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时期。太祖即代王位后,于登国元年(386)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1]20。登国九年(394),太祖“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1]26。天兴元年(398)二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1]2850。同年,北魏攻占后燕太行山以东疆土,“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1]2850。同年十二月,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1]32。这既有出于防止太行山以东新征服的原后燕统治区死灰复燃的政治考虑,更有充实代北中心经济区的经济动机。同年,太祖“如繁峙宫,给新徙民田及牛”[2]3465。天兴二年(399)七月,太祖因“陈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1]35。之后这一进程不断加快。天赐三年(406)四月,“河东蜀民黄思、郭综等率营部七百余家内属”[1]51。天赐五年(408)七月,“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1]53;八月,“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田,计口授田”[1]54。除了强制移民外,对游牧部落采取离散定居政策,将部落组织强制改造成国家编户,以适应农耕经济生活需要,也是北魏构筑代北经济区的重要政策。太祖“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1]1812。同年,太祖“命有司正封畿,标道里,平权衡,审度量;遣使循行郡国”[2]3476,从而确立平城的国家经济中心的地位。天赐三年(406),太祖营建平城国都,“欲封邺、洛、长安,修广宫室。……穿沟池,广苑园,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2]3591。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经济区初具规模。
继太祖之后,太宗、世祖、高宗、显祖、高祖诸帝继续充实与巩固代北经济区。为此,北魏诸帝力倡劝农,把农业作为官员考绩的主要标准。泰常二年(417),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下诏称:
九州之民,隔远京邑,时有壅滞,守宰至不以闻。今东作方兴,或有贫穷失农务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诸州观民风俗,问民疾苦,察守宰治行。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闻。[1]57
泰常三年(418)正月,太宗“自长川诏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人众北略,至弱水。降者二千余人获马牛羊二万余头”。同月,“河东胡蜀五千余家相率内属”[1]63。同年四月,“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1]58。泰常八年(423)正月,“河东蜀薛定薛辅率五千余家内属”[1]63。这些内附移民均被北魏朝廷以“计口授田”的方式安置在代北。
所谓“计口授田”,即以人口为单位分配土地。而既然是强制迁徙,便更接近曹魏屯田制,是通过国家政权强制把农业劳动力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从事农业生产。当然,“在分土定居后,所有氏族内部的个别集团,也即是各个家长制大家庭的单个家庭包括贵族在内一律变成了编户,显然这是地域性的编制,但家长制并没有被分解”[3]。如以牛为单位分配土地,以及互助合作的社会关系都还带有部落制痕迹。同时,由于“拓拔魏国家的疆土和人民,主要是原来魏晋封建社会的土地和人民,自然不得不承受原来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4]。因此,历史传统和既有中原农耕经济基础使拓拔鲜卑入主中原后必须接受农耕生产方式的洗礼。
但是神瑞二年(415),平城地区发生严重饥荒,朝野上下为是否迁都邺城争执不休,平城的经济中心地位受到挑战。崔浩进言:
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1]808
崔浩虽然以政治地理地位的优越性排除众议,暂时稳定了平城的首都地位,但对于经济基础问题,北魏却也只能“分民诣山东三州食,出仓谷以廪之”[1]808应急解决,无法扭转平城在经济地理方位上地处偏远的现实困境。太宗在度过这次灾荒和迁都危机后,立刻下诏劝农:
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凡庶人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缞。教行三农,生殖丧无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教行园囿,毓长草木;教行虞衡,山泽作材;教行薮牧,养蕃鸟兽;教行百工,饬成器用;教行商贾,阜通货贿;教行嫔妇,化治丝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岁数丰穰,畜牧滋息。[1]2850
斯时畜牧业仍然在北魏国民经济中占有较重要地位,因此太宗劝农必须兼顾农商畜牧。
到世祖太武帝拓拔焘时,这一生产结构大体沿袭。世祖在继承太祖、太宗劝农政策的基础上,十分注重发挥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
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韧膳府。[1]2850
世祖政策的这种灵活性是由于北魏在尊重各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曾经有过失败教训。如:
敕勒新民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洁与左仆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后,不得北遁。世祖曰:不然。此等习俗,放散日久,有似园中之鹿,急则冲突,缓之则定。吾自处之有道不烦徙也。洁等固执,乃听分徙三万余落于河西,西至白盐池。新民骇,皆曰圈我于河西之中,是将杀我也……既而新民数千骑北走,洁追讨之。走者粮绝,相枕而死。[1]687
当然,世祖施政仍然以劝农为主导方向。泰常八年(423)十二月,世祖即位伊始即“除禁锢,释嫌恶,开仓库,赈穷乏,河南流民相率内属者甚众”[1]69。太平真君九年(448)二月,“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1]102。南征后,正平元年(451)三月,世祖“以降人五万余家分置近畿”[5]61。同时,鉴于北魏户籍编制疏漏严重,“禁网疏阔,民多逃逸”,以至出现“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的混乱局面,世祖于“始光三年(426)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1]2851。太平真君四年(443),太子拓拔晃监国,实施课田政策:
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偿以私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小老无牛家,种田七亩,小老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1]108-109
这是在“计口授田”基础上的进一步资源优化政策。所谓有牛户和无牛户之间“以人牛力相贸”和“无牛户偿以锄功”诸细则,旨在克服“计口授田”实施后必然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对代北经济区的社会稳定具有深远影响。
北魏诸帝为稳定农业人口,严令禁止百姓因贫苦卖身为奴。和平四年(463)七月,高宗文成帝拓拔浚下诏称:
前以民遭饥寒,不自存济,有卖鬻男女者,尽仰还其家。或因缘势力,或私行请托,共相通容,不时检校,令良家子息仍为奴婢。今仰精究,不听取赎,有犯加罪。若仍不检还,听其父兄上诉,以掠人论。[1]121
高允也因“时多禁良田,又京师游食者众”,向高宗上表:
古人云: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田三万七千顷。若勤之,则亩益三斗,不勤则亩损三斗。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若公私有储,虽遇饥年,复何忧哉?[1]1068
结果“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1]1068。
北魏统治者甚至强制命令工商业者转行务农。高祖孝文帝元宏延兴二年(472)四月,“诏工商杂伎尽听赴农,诸州郡课民益种菜果”[1]137。孝文帝派使者赴各地督促检籍,“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者,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1]139;同时力促劝农,于太和六年(482)正月下诏称:
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若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1]143
同年三月,又“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1]144。孝文帝此举,其“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不仅继承了拓拔晃京畿课田的成就,强调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给;而且“一夫制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的课田标准,更可视作均田制的先声。
除力促劝农外,北魏统治者开始关注各经济区域之间的物资交流,以求丰荒互赡,贫富相济。高宗于太安五年(459)十二月下诏称:
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有流徙者,谕还桑梓,欲市籴他界,为关傍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职不均,使上恩不达于下,下民不赡于时,加以重罪,无有攸纵。[1]118
世宗宣武帝元恪延昌元年(512)四月,“诏河北民就谷燕恒二州,诏饥民就谷六镇”[1]212。这虽然是灾荒年景的政策,但其“通其交易之路”的精神,想必不会不适行于丰年。此外,促进经济区域的整合需要规范度量衡和货币媒介。北魏朝廷适时统一度量衡,根据“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疋、六十尺为一端,令任服用后仍渐至滥恶,不依尺度,于是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1]2852。代北经济区的不断充实与巩固,不仅有利于促进各经济区域的整合,也为迁都洛阳奠定了经济基础。
同时,在代北经济区的营造过程中,附近地区经济也得到带动与发展。南部的并州是最先被纳入北魏版图的原后燕地区。皇始元年(396),太祖“取并州,初建台省,置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悉用儒生为之”,采用中原汉制管理,“招抚离散,劝课农桑”。[2]3431崔游任河东太守,“郡有盐户,常供州郡为兵。子孙见丁从役,游矜其劳苦,乃表闻请听更代,郡内感之”[1]1276。司马跃任朔州刺史,固请“罢河西苑封,与民垦殖”[1]859,最终得到孝文帝诏准。
(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经济区的初步形成
在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经济区的形成与巩固的同时,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经济区也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河南是传统的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中心区。拓拔鲜卑若要真正实现问鼎中原的政治抱负,就必须要营造河南经济区,并以此为基点实现国家经济一体化。
早在太祖时期,奚斤“既平河南,以(司马)楚之所率户年民分置汝南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以益豫州”[1]855。太宗神瑞元年(414)五月,东晋官员刘研第等“率流民七千余家内属[1]54。神瑞二年(415)四月,“河南流民二千余家内属”;九月,“河南流民前后三千余家内属”[1]55。后秦灭亡后,“秦雍之民来奔河南、荥阳、河内户者至万数,”北魏在洛阳设立南雍州招抚流民,“由是流民襁负自远而至者叁倍于前”[1]947。
但是直到世祖时河南仍处于“南土未实”的状况。世祖“略地至于陈汝。淮北之民诣军降者七千余户,迁之于兖豫之南,置淮阳郡以抚之,拜(李)祥为太守加绥远将军。流民归之者万余家,劝课农桑,百姓安业”[1]1174。李洪之于高宗时任河内太守,“河内北连上党,南接武牢,地险人悍,数为劫害,长吏不能禁。洪之至郡,严设科防,募斩贼者便加重赏,劝农务本,盗贼止息”[1]1918。
孝文帝趁南朝宋齐相交之际掠取大片南部疆土,河南逐渐摆脱了边境的境遇,经济发展更加迅速。韦珍“拥降民七千余户内徙,表置城阳、刚陵、义阳三郡以处之”[1]1013。辛穆任汝阳太守,“值水涝民饥,上表请轻租赋,帝从之,遂敕汝阳郡,听以小绢为调”[1]1028。沈文秀任怀州刺史,“大兴水田,于公私颇有利益”[1]1367。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避奉公之誉,部内患之”[1]1681。宋弁“于豫州都督所部及东荆领叶,皆减戍士营农,水陆兼作”[1]1415。王慧龙任荥阳太守,“在任十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1]876。迁都后,北魏新首都洛阳面临着远比旧都平城更加复杂而严峻的治安形势:
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荫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荫结贵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比之边县,难易不同。[1]1514
对此河南尹甄琛建议:
取武官中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者,进而为之。则督责有所,辇毂可清。[1]1514
世宗采纳此议,诏令“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不必武人”[1]1514。到孝文帝时期,河南经济区已经初具规模。
但是迁都伊始,代北和河南两个经济区的过渡仍然不协调。李平在上书时反映:
嵩京创构,洛邑俶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尽,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运;陵太行之险,越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得达京阙。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兼历岁从戎,不遑启处。自景明已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务。实宜安静新人,劝其稼穑,令国有九年之粮,家有水旱之备。若乘之以羁绁,则所废多矣。[1]1457
此议道出了经济中心转移过程中的高昂经济成本和沉重社会代价,希望通过继续劝农以实现平稳过渡。世宗正始元年(504)十月,北魏又“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1]198,进一步充实河南经济区。延昌二年(513)正月,朝廷再次诏令“以苑牧之地赐代迁无田者”[1]213。另外,在加强主体农业经济基础的同时,北魏并不偏废畜牧业。太和十八年(494),宇文福“表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河凡十里牧地,纵则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横则距河十里”。孝文帝“自代徙杂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无耗失”[2]4369,使其成为河西以东距离平城较近的一块牧区。
由于洛阳是中原王朝传统政治中心,这一政治地理地位决定了北魏优越的国际贸易地位:
自魏德既广,西伐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1]2888
迁都后,洛阳继平城之后成为新的国家经济中心*相关研究参见:王万盈:《北魏时期的周边贸易述论》,载殷宪、马志强:《北朝研究(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64-66页,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北魏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均田制、三长制的影响
太和九年(485),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宣称“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1]156。为贯彻均田令的实施,特别是有效实现国家地租收益的最大化,北魏朝廷同时推行三长制,将行政神经末梢触及到乡村基层。太和十年(486)二月,“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1]161。孝文帝在继续重申劝农精神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国家的社会救济职能,并重申对户口检括的强调。太和十一年(487)九月诏称:“罢北山苑,以其地赐贫民。”同月诏称:“去夏以岁旱民饥,须遣就食,旧籍杂乱,难可分简,故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实,赈贷平均。然乃者以来,犹有饿死衢路,无人收识。良由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廪恤不周,以至于此。朕猥居民上,闻用慨然。可重遣精检,勿令遗漏。”[1]162十一月,诏令“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1]163,以减少宫廷开支。太和十二年(488)八月诏称:“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1]163太和十三年(489)九月,“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鳏无妻者”[1]165。太和十四年(490)十二月,“诏依井丘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弱,罪有常刑”[1]167。任城王元澄也上表请求“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禁造布绢不任衣者”[1]473。北魏朝廷还督促各地兴修水利,“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灌溉,遣匠所在指授”[1]165,由朝廷派出专门匠人帮助水利建设。
均田法令包含三方面的信息。其一,规定授田对象、种类、数量和还田条件: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授。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1]2853-2854
其二,均田制体现宽狭相通原则:
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诸地狭之处,有进丁授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1]2854
其三,关于官员受田。均田令规定: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1]2855
官员所授田,既然明确指出是“各随地给公田”,则说明并非私产;而“卖者坐如律”,则表示官员任内可享有对土地收获物的所有权。这是北魏对官员分配的用于俸禄的禄田。
北魏统治者通过均田制,准确掌握土地与人口信息,一方面通过给予部分世业田以满足农业生产者的私有欲望;另一方面通过掌握大部分土地所有权即必须还田部分,控制土地总量以供调节与配给,从而与农业生产者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在刺激农业生产总量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地租收益的最大化。这是农耕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北魏国家通过限制农产品的种类,以及通过控制地狭地区农业人口的迁徙,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对农业资源即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综合配置和优化配给。与西晋占田制相比较,均田制无疑更加细则化,也更加强调产权与责任的界限。占田制只规定了占田的私有方向而无产权细则,如无还授条件等。但或许是史载缺失,或许是颁布占田令后仅仅有十年的和平发展局面,西晋便陷入内乱,细则恐在酝酿阶段便胎死腹中。而均田制事先即在“计口授田”后经历过拓拔晃在京畿的课田和孝文帝初年的课田,为均田制做了良好的铺垫。当然,与西晋占田法是在屯田制瓦解基础上形成不同,北魏在颁布均田制的同时并不放弃屯田制这一行之有效的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的生产资料配置手段。太和十二年(488),有司甚至建议“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民足矣”[1]2856-2857,设置专门机构并提留专门资金专司屯田。事实证明,屯田对稳定边境地区仍然具有战略意义。均田制如要达到地租最大化目的就必须依赖对人口信息的准确掌握。于是括户成为地方官的重要行政职责。如元晖“出为冀州刺史,检括丁户,听其归首,出调绢五万匹”[1]379。
均田制对后世影响深远,一直是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其实,均田制是北魏经济从游牧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方式转化的必然结果,其历史价值与西晋占田制相当。西晋占田制是曹魏屯田制崩溃后的必然结果。西晋统一后,西晋朝廷通过确立小农土地私有制,辅以户调制的赋税征收办法,以解决屯田制瓦解后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问题。而北魏朝廷立国初期即推行“计口授田”,既为北魏朝廷强制移民后安置新民而推行,也类似屯田制由曹魏政权强制推行的屯田民与土地的结合。因为对于拓拔鲜卑这样一个刚刚摆脱游牧生产方式的民族来说,为解决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问题,“计口授田”是绝对必须的选择。而且面对劳动力短缺的难题,强制移民又成为急需,因此站在土地与劳动力结合这一农耕经济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理解北魏均田制,才能把握北魏统治者推行均田制的直接用意。此举虽然如有论者指出:均田制的目的“是在增加粮食生产,在地荒人少、生产力衰退的情况下,均田能够使劳动者在土地上增加生产,使封建统治的北魏王朝获得经济上的暂时成功,而不是为了直接生产者的农民而调整土地关系”[6],但新制度既然建立在农耕经济传统和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生产关系的调整便无法阻挡,势必超越执政者的初始动机[7]。
为配合均田制,北魏朝廷还推行三长制,通过乡村基层组织的设立以辅助朝廷各级地方官,在尽可能准确掌握人口与土地信息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地租收益最大化。首先,三长制的设立是逐渐强大的皇权,在代北经济区不断充实的基础上,对基层乡村行政的渗透。在这之前,建国百年来,乡村权力始终掌握在宗主督护制的主导者——地方豪强手中。由此造成的人口荫附现象自然不利于国家扩大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和地租收益最大化的获得。“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徵敛,倍于公赋。”对此,给事中李冲上书曰:
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孤独病老笃贫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之。[1]2855
李冲所论欲使三长制为国家承担赋税征收的职能,三长本人因而得以在赋役方面获得政府相应的优惠承诺。孝文帝对李冲上书中的这一功能十分看重,他尤其希望利用三长制实现国家对人口信息的最大限度掌握,同时可以摆脱原宗主督护制下的豪强在国家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角色。他表示:
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馀,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虽建九品之格,而丰角之土未融,虽立均输之楷,而蚕绩之乡无异。致使淳化未树,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怀深慨。今革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1]2856
三长制也被用于洛阳新都的规划。宗室元嘉“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1]428-429。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直接经济目的可以从李安世的上表中得到反映:
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人获资生之利,豪右靡馀地之盈,无私之泽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於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1]1176
李安世规劝朝廷必须尽可能准确掌握土地信息,使土地从强宗豪族的实际控制中简括出来,一方面体现“宜更均量”的原则,另一方面对“事久难明”的田土纠纷采取“悉属今主”的简化处理手段。以冯太后为代表的朝廷决策者看中的也正是均田制和三长制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正如冯太后在肯定三长制时所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1]1180
减少中间环节的盘剥,赋税征收过程更加透明,直接生产者的负担相对减轻,国家地租收入也相应提高。同时,朝廷对佛教寺院经济也大力整肃,尤以括户为重点。由于北魏帝王佞信佛教,佛教寺院经济得以控制大量劳动力。
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洒扫。魏主并许之。于是僧祗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1]3037
因此,佛教寺院经济成为均田制推行前后括户工作的重点。延兴二年(472)四月,朝廷诏令:
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1]3038
世宗也对僧祗粟问题痛加节制。永平四年(511)诏令:
僧祗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翻改倦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已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检括。[1]3041
孝文帝曾向公孙邃垂询均田制与三长制推行后的效果。
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于百姓颇有益否?邃对曰:先者人民离散,主司猥多,至于督察,实难齐整。自方割以来,众赋易办,实有大益。[1]786
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地区的旱灾对均田制和三长制给予严峻考验:
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留业者,皆令主司审核,开仓赈贷。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检集,为粥于术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间甚多喂死者。时承平日久,府藏盈积,诏尽出御府衣服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缯布丝纩诸所供国用者,以其大半班赍百司,下至工商供国用者,以其大半班赍百司,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边戍,畿内鳏寡孤独贫癃者,皆有差。[1]2856
面对空前的饥荒,北魏一方面希望发挥三长制代理官府实现社会救济职能,另一方面则仍然强调发挥国家开仓赈济的主渠道作用。从孝文帝“然主者不明牧察”的指责可看出,三长制的社会救济职能在北魏执政者的行政设计中仍然是辅助性的。
但新制度的推行,虽然雷厉风行,却并非立竿见影。直到太和十二(488)年五月,孝文帝仍在督促,“农惟政首,稷实民先,澍雨丰洽,所宜敦励。其令畿内严加课督,惰业者申以楚挞,力田者具以名闻”[1]179。七月诏称:“京民始业,农桑为本,田稼多少,课督以不,具以状言。”[1]180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更不无忧虑地承认:“京师之民,游食者众,不加督劝,或芸耨失时。可遣明使检察,勤惰以闻。”[1]170均田制在各地的贯彻情况并不理想,如元晖上书肃宗反映河北地区的情况:
国之资储,唯籍河北。饥馑积年,户口逃散,生长奸诈,因生隐藏。出缩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调,割入于己。人困于下,官损于上。自非更立权制,善加检括,损耗之来,方在未已。[1]380
而元遥在任冀州刺史时,拟“以诸胡先无籍贯,奸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诸胡设籍,当欲税之,以充军用”[1]445,也归于失败。均田制更未贯彻到边地:
自比缘边州郡,官至便登疆场统戍,阶当即用。或值秽德凡人,或遇贪家恶子,不识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残忍之法。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资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1]1539
甚至对佛教寺院经济的检括成果也毁于一旦:
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有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3048
三长制的推广也同样需要时间的考验和实际效果的验证。“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富豪并兼者尤弗愿也。”但是“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1]2856。不过,三长制的效果总起来看差强人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设计者的初衷。如任城王元澄便上书胡太后希望解决如下问题:
逃亡代输,去来年久者,若非伎作,任听即住;边兵逃走,或实陷没,皆须精检;三长及近亲,若实隐之,徵其代输,不隐勿论;工商世业之户,复徵租调,无以堪济,今请免之,使专其业;三长禁奸不得隔越相领户不满者随近并合。[1]475
地方官监督不力或者与充任三长的富豪勾结,很容易使人口与土地的准确信息被刻意隐瞒,出现“逃亡代输”,甚至无地商户也被课以赋税的现象。同时,正如有学者所论,“乡里编制虽然普遍存在,但在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村民对村落表现出归属感,而“官方设置在村落被架空”。[7]这说明乡村社会对官府的感受更多体现为对国家行政机构及其经济职能的隔膜与缺乏认同,也恰恰反映出三长制仍然需要在实际操作层面,通过与宗主督护制合流,才能实现地租最大化的目的。
总之,均田制与三长制的推行是北魏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过分追求短期现实经济利益,因而其调整社会生产关系以促进国家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受到限制。
(二)货币政策的影响
随着平城和洛阳中心经济区的形成,北魏开始试图通过货币政策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研究参见:史卫:《北魏货币使用研究》,《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刘玉民:《南北朝货币盗铸问题初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北魏建国后百年,国家经济处于从游牧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方式的艰难转化过程中,同时还必须首先完成对北方疆土的统一,因此战事频繁、政局动荡和农业总量低所导致的商品经济水平低下的状况,直到孝文帝时代才有改观。因此,
魏初至太和初,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495),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1]2865
北魏朝廷通过俸禄的钱币化和规范钱绢比价,试图凭借国家行政强制力推行经济一体化进程。但准许民间私铸,着实欠妥,因为斯时国家对各经济区域的整合努力正举步维艰,农业经济基础尚不足以保证国家硬通货的压倒性优势,这时便放开私铸无疑过早,尽管北魏也在强调铸币成分的纯正。果然,由于流通钱币种类庞杂,货币秩序逐渐混乱:
世宗永平三年(510)冬又铸五铢钱。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1]2865
其实,早在这之前,太和五铢已出现通行障碍问题。熙平年间,尚书令、任城王元澄反映:
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徐今彭城、琅玡郡地。扬今寿春郡地。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徐之域。荆今南阳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鲁郡、东平郡地。致使贫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1]2865
永平三年(510),面对朝臣“断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的倡议,世宗只用“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多行,至年末悉令断之”的模棱两可态度处理[1]2865。各地方借朝廷的优柔寡断纷纷自行其是:
徐州民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镮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1]2865
徐州纳入北魏版图不久,求用土钱情有可原。河北、河南诸州不欢迎官铸五铢,则充分说明北魏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成就并不高。为此,元澄建议采用一个变通的妥协方案:
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1]2865
这个方案其实基调温和,无非是在通货成色上做些文章。但皇帝恐担心骤然实施此法令激起地方不满,态度依旧模棱两可,表示:“钱行已久,今东南有事,且可依旧。”[1]2865元澄坚持己见,上书曰:
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鹅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钱者,罪重常宪。既欲均齐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绳以严法,无以肃兹违犯。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于市也。[1]2865
当然,元澄为得到皇帝支持,也做出些许妥协,表示:“诸方之钱,通用京师”,以期换取地方对官铸五铢的支持,这才获得朝廷的通过。但实际效果仍然差强人意。如“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1]2865。结果,盗铸再起,以至“建义初,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1]2865。这不仅说明民间区域市场的顽强生命力,还说明北魏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一体化的无能为力。朝廷试图通过铸新币重塑经济权威,从而展开与民间盗铸的恶性竞争:
至永安二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二市赏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1]2866
不仅国家金属货币被民间盗铸吞没,而且用于调节比价的货币等价物绢也被民间奸商刁民投机炒作。地方官员更借机通过操纵比价从中渔利:“受调绢匹,度尺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1]1297期间虽有前废帝元恭普泰元年(531)宣布“天下调绢,四百一匹”[1]274,以稳定币值,但为时过晚。
肃宗孝昌年间,高谦之被胡太后委任为铸钱都将长史,上表力主铸造三铢钱,宣称:
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征税既烦,千金日费,资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税之秋,桑、儿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败,民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1]1711-1712
按照高谦之的意思,既然开支浩繁,而各类钱币本已并行不悖,自然可以开铸新币弥补国用不足。国家铸币无法保证足额成色,自然会导致货币信用的跌落。到敬宗孝庄帝元子攸时,“用钱稍薄”现象已十分猖獗。高道穆从铜的市价和官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的角度分析,认为:
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铸薄钱,斤余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复何罪。”[1]1716
他建议:
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也。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1]1716
孝庄帝从其议,遂铸永安五铢。这势必会演变成一场官府与民间争夺铜资源的市场价格战。但是朝廷提高货币成色的行政方向还是值得肯定的。可是杨侃却建议孝庄帝放任民间私铸“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1]1284。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民间盗铸猖獗的现实。
总之,北魏朝廷的货币政策彻底失败,无法实现促进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北魏建国后,拓拔鲜卑统治集团通过对被征服地区民众的强制移民,并以“计口授田”方式安置于代北平城地区,逐渐营造起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经济区。与此同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原河南经济区也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为迁都奠定下经济基础。均田制、三长制与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推出使北魏宏观管理经济的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北魏经济转型缓慢,国家对各经济区域的整合成效并不显著。加之孝文帝迁都的时机并不十分成熟,国家行政意识超前,延误了促进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最佳时机。结果,代北和迁洛鲜卑人之间的族群内战使北魏国家走向解体,经济一体化进程被迫中断。
但迁都和汉化也并非全无成就。北魏灭亡后并非陷入如前秦灭亡后五胡十六国般的混乱局面,北魏时代的经济区域整合努力终于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报。河南、河东及河北经济区以邺和晋阳为中心整合为北齐,以长安为中心的西部整合为北周。他们在北魏灭亡后分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孝文帝因急进汉化而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最终由北周和隋朝完成。
[参考文献]
[1] [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唐长孺.拓拔氏的汉化过程[A].魏晋南北朝史续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93.
[4] 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191.
[5] [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45.
[7]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