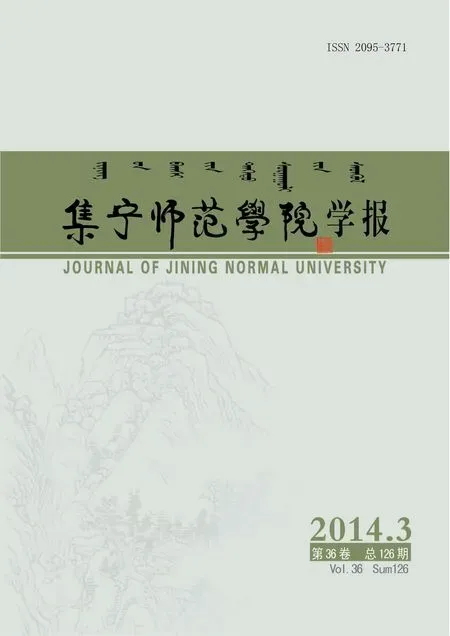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之融合转换——论《第七天》的主题内涵
刘文婷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余华的小说,历来以残酷和怪诞著称,他选择用残酷的语言描述现实,用怪诞的情节讽刺现实。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现实一种》、《兄弟》等为人熟知的作品中,“死亡”是其必不可少的主题元素。通过多种方式的死亡描写,展开情节,揭示主题。但事实上,他的本意并不在于把所有人写死,而是用死亡的残酷性来激励活着的人继续勇敢而坚强的活着,即海德格尔所谓“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以此来追踪活着的意义所在。相比之下,《第七天》则有所不同,余华一反常态,首先将所有主人公写死,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余华笔下,把对生前的追忆与死后的存在交汇融合,其所谓死者,不过是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转化为另一种存在方式。“如吾人以现在所有之存在形式为可喜,则死后吾人所得之新形式,亦未尝不可喜。”①这种突破生死界限的写作,既是余华对于死亡的重新定义,也是他对于以往死亡即是终结的突破所在。
正如余华自己所说:“假如要说出一部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第七天》),因为从我八十年代的的作品一直到现在作品里的因素都包含进去了。”②因此,如果在《第七天》中以死亡为界限,那么作者对于生前的描述,是将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结,与活着相对立的存在,为现实绝望所生、为希望所弃的主人公形象之塑造,是对以往作品中“向死而生”的死亡本体论之延续;而死后虚无世界的情节叙述,则将死亡引申为活着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是对活着本身的突破,亦融合了道家思想“以死为生,向生而死”的智慧。
一 以生为死,向死而生
人为什么活着?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命题并作以回答:“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③在作者看来,应该为“人类的解放”而活着。这种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活着是对生的崇高解读,是一种伟大的生的存在。而在余华作品中,活着得到了重新的诠释,相对而言,这是对于生回归自身的解读,同样伟大。
早在《第七天》问世以前,余华就用《活着》对“向死而生”这一命题进行过最直接的思考。虽然题为《活着》,内容却充斥着死亡的元素,他选择用死亡来回答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本应该幸福美满的家庭,却因种种荒诞的原因相继离去:儿子抽血过多而夭折,女儿难产致死,妻子因病离世,女婿意外死去,仅有的希望外孙苦根吃豆撑死,这种残忍的生命经历并没有让福贵倒下,而是更坚定了他活下去的信念。用残酷的死亡来突显出活着之不易是余华冷漠描写死亡之用意所在。抛开一切外在因素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死亡来结束除福贵外一切有联系的生命存在,将其置于绝望的环境中,以此来揭示活着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④,是余华对于“活着”本身最纯粹的理解。
相比《活着》,《兄弟》并未达到预想的高度,但就其对死亡的叙述来看,亦是一部关于死亡的荒诞集合。亲生父亲在粪坑憋死,宋凡平文革中被活活打死,母亲李兰得尿毒症而死,以及宋刚最后的卧轨自杀,所有亲人的离去,李光头选择同福贵一样坦然接受。其实,余华是想在此基础上对“活着”有所突破的,于是在结尾让李光头学俄语、炼身体、上太空,在绝望中寻找生的意义,但并不能让读者理解与接受,以失败告终。
在《兄弟》饱受争议的七年之后,《第七天》与读者见面。在书中,余华延续了其创作的一贯方式,集合了众多离奇的死亡,与以往不同的是——叙述者已死。暂且抛开这一因素,那么《第七天》无疑是当代版的《活着》。
主人公杨飞从小失去父母,经历了妻子李青先弃他而去,后因公司被查选择自杀;养父杨金彪身患淋巴癌,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离家出走;虽非亲人、胜似亲人的妈妈李月珍车祸丧生,又因地陷未能送她最后一程。相比《活着》中福贵见证一家人的离去,余华将杨飞置于更加绝望的境地,每位亲人的离去,他都未能相送,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这种描写对生者来说是十分残忍的,但在残忍的同时,也给主人公留有一丝希望,如父亲依然活着的希望。
余华用《活着》中的种种死亡让本应美满的家庭变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以此阐释“人为什么活着”的命题,认为生命应该是“向死而生”的存在。死亡的不确定性、荒诞性和死亡的必然性让福贵也让读者理解了生命的珍贵,活着的不易。而《第七天》中亲人的相继离去,是让本就破碎的家庭更加不堪,父亲的存在是主人公杨飞活下去的希望所在,离婚后的杨飞与父亲相依为命,这位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养父为了他放弃了一辈子的幸福,父子感情之深由此可见。所以,当患有淋巴癌的父亲不辞而别时,在作者看似冷漠平静的描述掩盖下,是杨飞绝望的灵魂。“向死而生”的命题在这里得以突破与升华——“向父死而生”,明知父亲的死必然存在,只是不确定何时会发生,是无法挽回的,杨飞仍毫不犹豫的辞掉工作、变卖房产,只为父亲活着。杨飞选择了寻找,为了父亲的存在而寻找,在不断报以希望又不断失望中寻找,在寻找中得以存活。
没有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死亡的事实让福贵选择了接受、隐忍的活着。与福贵所不同的是,父亲的失踪而并非直接死亡,使杨飞在最后因希望破灭而走向了死亡。表面看来,作者让杨飞死于饭店爆炸,但仔细咀嚼,在父亲失踪的一年多后,生的希望已然渺茫,来到和父亲一同吃过的谭家菜馆,坐在同样的角落里,徒增伤感。本就神色黯淡的“我”,看到了前妻李青自杀的新闻这一导火索时,杨飞感受到的是对生的茫然和死亡的召唤。所以,当厨房起火,众人破门而出,跳窗而逃时,杨飞选择了坦然接受死神的来临,以此来承接作者由“向死而生”到“向生而死”的转换。
二 以死为生,向生而死
老子有云:“知其白,守其黑。”黑是先于白的存在,在这里,可以将“黑”理解为虚无的世界,虚无是先于我们的存在。“我们存在的意义应当是虚无赋予的,故此,归于虚无的死并非同生的别离,而是和生的重聚。”⑤
《第七天》中,余华构造了一个死后的世界,并将这个世界一分为二,对死亡进行了两种解读。通过象征着生死之界的殡仪馆,有骨灰盒和墓地的人去了“安息之地”,在那里永远地结束了生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死;而没有骨灰盒和墓地的人到了“死无葬身之地”,在死亡的虚无世界中得到了永生,这种存在超越了死的限制,意味着生的无限与永恒。
“黑夜的恐惧就是害怕永生不朽,害怕存在的悲剧常演不衰,害怕必须永远承担存在的重荷。”⑥余华笔下“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就是列维纳斯描述的这样一种存在,他们害怕生的悲剧重新上演,害怕承担生存的重压,只能选择在死亡的虚无世界中远离现实而永生。
“死无葬身之地”本是存在于生的世界中对人的诅咒,是恶毒的攻击,被认为是对恶人应有的惩罚,在余华这里,又有了新的含义。“死无葬身之地”也就是“死无安息之地”,安息代表着永远的死亡,而“死无安息之地”则代表着另一种永生,以死为生,向生而死。这种永生,不是永远存在于生的空间,而是永生于死的空间,是对生的恐惧,对现实的排斥。相比较之前作品中通过冷漠描写死亡,控诉现实,此时对死的崇尚,对“死无葬身之地”的动人描绘,其讽刺批判意味则力透纸背。
对于这种永生,其存在的原因是多样的,余华对此做了多种阐释,具体来说,在《第七天》中的“向生而死”可以归为两种含义。
(一)因“情”而永生
较之余华以往的小说,《第七天》中的语言描写是更加节制与冷漠的,这符合叙述者的死亡身份,但在主人公追忆往事时,人物语言随情感而升温,则显示出作者对“情”表达的独具匠心。杨飞与杨金彪之间的父子之情,跨越血缘、跨越生死。在现实世界中,杨飞竭尽全力寻找父亲,以父亲的存在作为自身存活的理由,向父死而生。当希望逐渐破灭,死亡临近时,他选择了接受。在死的世界中,他的目的依然是寻找父亲,“我和父亲永别之后竟然重聚,虽然我们没有了体温,没有了气息,可是我们重新在一起了。”⑦与现实世界相比,死亡的虚无世界中依然有父亲热爱的工作,但没有了疾病与苦痛以及死亡的威胁,与其在生的世界中遭受折磨,不如在死的虚无里得到永生,父子二人因此选择了后者,为亲情而永生。相比亲情,爱情之永生以错过告终。世人的冷漠与无情诱发了鼠妹跳楼事件的发生,使鼠妹与伍超在生的世界中错过。得知鼠妹死讯的伍超卖肾为鼠妹买下墓地,却不知此举让两人在死的虚无中再次错过,这一错过便是死的永生。尽管可惜,但不可否认,鼠妹是感受着伍超的爱而安息的,伍超也是为爱而死,因此能为爱在死里得到永生。作为蚁族的代表,两人在死亡的虚无里为爱情永生,是余华出于对现实生活中蚁族的同情。长期蜗居于地下室的蚁族们,处于社会下层,为了生存而拼搏、而牺牲,却常受到社会的压榨与不公,“爱情”对于他们来说是奢侈品,却在《第七天》中得到了永生。
书中,友情的描写最为特殊,若将杨金彪杨飞的父子亲情、鼠妹伍超的爱情看作是生在死中的延续,那张刚与李姓男子的友情则截然不同。跨越生死的界限,在生的世界中本为敌人的两人,在死的虚无中却成为了为彼此而永生的挚友。“他们之间的仇恨没有越过生与死的边境线,仇恨被阻挡在了那个离去的世界里。”⑧此等荒诞友情的用意在于,通过死的虚无远离了现实世界中的地位、阶级、身份、利益等外在因素,人与人之间处于平等的地位,可以充分展示这种较之生命更为珍贵的真与善的价值。余华在此赋予其虚无世界以消灭不平等的特权,以此来否定现实友情的复杂性与虚伪性。
(二)因绝望而永生
余华在以往作品中常描写死亡,但本意在于拒绝死亡。对死亡的不确定性与死亡发生必然性之理解让他选择了“向死而生”,说明他对于生活仍充满希望。《许三观卖血记》中多次卖血的情节,即是主人公对生命执着追求之体现。明知道卖血是在用生命与死亡搏斗,许三观依旧选择卖血,是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也是对“向死而生”的完美阐释。但在《第七天》中,余华制造更多贴近现实问题的荒诞和无法避免的死亡,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余华是在用“向生而死”来对人性罪恶进行绝望地控诉呢?
如果把父亲杨金彪的癌症、杨飞的不逃跑、鼠妹的跳楼、伍超的卖肾、李姓男子的袭击、妻子李青的死亡通通理解为“自杀”,那么李月珍与二十七个死婴,商场火灾中被隐瞒的三十八条人命,以及强拆事件中小敏父母的不幸遇难则无疑应归于“他杀”的行列。
看似遭遇意外车祸的李月珍,在死前三天发现了被当做医疗垃圾丢弃的二十七个死婴,面对医院的否认,媒体的压制,作者选择设置李月珍的车祸。不管是人为还是巧合,对车祸与发现死婴的关系,作者留下了空白。但对于发现丑恶的主人公,作者选择用残忍的方式——先被超速的宝马撞飞,又被卡车和商务车碾压——造成其必死的结局。现实中揭露罪恶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这是作者的无奈揭露与批判。更进一步,拥有丈夫孩子的李月珍本可以去往“安息之地”,但余华并未如此设置,他选择将现实的罪恶,实行仁心仁术的医院人性之泯灭表现到极致,因此设置了“地陷”的情节。现实的掩盖使李月珍与二十七个死婴永远留在了“死无葬身之地”,在死的虚无中远离人性罪恶而永生,这种存在的本身,就是对现实罪恶的绝望控诉。
在睡梦中遭遇强拆的小敏父母,还来不及与女儿告别,就被永远的掩埋在废墟下。这种人为的残忍,是对人性黑暗的无情揭露与嘲讽。相比以往冷漠叙述,对存在于生的世界中的小敏,作者保留了同情,并没有让这位依然懵懂的孩子过早地了解现实的可怕,而选择了掩盖事实,让她在废墟之上孤独地等待掩埋在废墟之下父母的出现。真相对于孩子来说太过残忍,《班主任》中“救救孩子”的呼吁在这里有了新的含义。
庄子云:“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在“向生而死”的两个内涵中,前者的“为情而永生”可以理解为“杀生者不死”,余华笔下的亲情、友情与爱情是跨越生死的存在,彼此的存在让他们没有了对生的留恋,忘生则得不死,是作者对人性中真情的正面赞美与留恋,也是对以往先锋作品的延续与圆满结局的设定。《第七天》中,余华依然选择描写现实的残酷性,但通过“向死而生”到“向生而死”的转换,让之前诸多作品中死亡的遗憾在该书中得以弥补,即让人物在虚无的存在中得到永生。而后者,“因绝望而永生”则可理解为“不生生者生”,换言之,对生的世界之绝望,也就不执着于生死的界限,自然不存在所谓的死。余华笔下这些无辜的死,所谓的“他杀”而遗留于“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并没有因为死的无辜而抱怨、而恼怒,在死的伊甸园中,他们是在对生的绝望中平静、安详地接受死的永生。对于生没有过多的执着,阴阳相隔的亲人的生使他们满足,忘记现实对自己的不公,以德报怨,使其得到了永生。
“以死写生,是余华小说创作中的一次有意义的超越性的前行。”⑨可见,余华在《第七天》中并非简单地跨越对以往死的理解,而是在对现实深入探寻、刨根问底后的选择,是对“活着”有了更深体会后的表达。“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的融合转换,是余华将西式的人生立场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相互融合的结果,既延续了他对于苦难的描摹,对于生的思考,又突破了死即是人生终结的写作瓶颈与思想瓶颈,从而延伸出更加广阔的叙述世界,使死成为虚无世界的永生。“向死而生”到“向生而死”的转变是探究余华《第七天》的主题意义所在。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②张清华、张新颖等,《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第111页。
③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启明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④余华,《活着》,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页。
⑤路文彬,《向生而死》,《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2期,第第86页。
⑥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著,吴蕙仪译,《从存在到存在者》,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⑦⑧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分别引自第215页,第143页。
⑨王达敏,《一部关于平等的小说——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4期,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