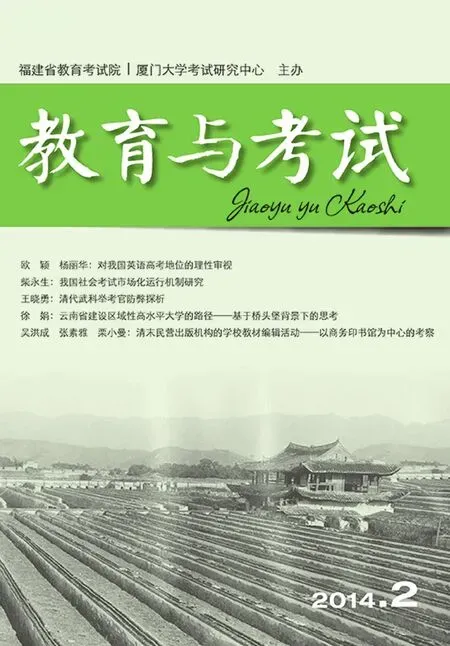试论我国教育改革的风险及其规避
邹 英
国际著名教育改革理论专家哈维洛克 (R. G.Havelock)曾对“教育改革”作过如下定义:“教育改革就是教育现状所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转变”。可以说,教育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教育、培养人才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和核心战略。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教育改革更是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对其风险及规避的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教育改革风险存在的原因分析
一般认为,风险(risk)是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等是其基本构成要素。换句话说,风险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段内,人们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与实际出现的结果之间产生的距离。当今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风险社会,异常情况随时发生并时常伴随危险。特别在传播手段和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的“媒介化”时代,风险传播视域下的舆论安全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独特作用,成为影响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人们的行为始终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主观风险”〔1〕,教育改革作为一项人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风险的存在也成为一种必然。
如果说社会风险的客观存在是教育改革风险存在的外在因素,那么教育体制本身的缺陷或不完善则是其存在的内部、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教育体制是教育机构与教育规范的结合体、统一体,包含机构体系与规范体系两大系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体制改革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有力推手。可以说,没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就没有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谈松华、谢维和两位学者认为,从总体上讲,当前教育还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教育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如: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政府教育管理职能转变亟待加强;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尚不健全;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体制不利于学生全面和谐发展和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等方面〔2〕。为了尽可能地少走弯路,使教育改革的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教育改革,做到统筹谋划,系统设计,循序渐进。
二、教育改革风险存在的具体表现
(一)“软”风险——对教育专家的过分信任与依赖
所谓专家,“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制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3〕正如各类专家分别是不同领域的权威一样,教育专家也成为教育改革方向的引领者、决策的咨询者、过程的推进者和效果的评价者。在专家已经深度介入教育改革并获得广泛认同的现代社会,政府或者普通民众都很愿意相信专家提出的任何建议和要求,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专家的观点也具有个人的局限性,不可能所有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不能把它作为衡量事实的唯一标准。对教育专家过分信赖的“舆论风险就是一种‘软’风险,诸如社会认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危险。因‘软’风险的隐蔽性,人们对‘硬’风险往往比较敏感、重视,而对‘软’风险相对关注不大。贝克、吉登斯所谓的‘风险社会’主要关注的是‘硬’风险。而在全球化与媒介化时代,‘软’风险已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巨大威胁。”〔4〕
(二)“泛”风险——网络风险传播与扩散的加剧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继传统大众媒体后的又一新兴“舆论场”。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关数据表明,我国民众对网络舆论的关心度及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依赖度和期望值均居各网络大国之首。与传统媒体舆论相比,网络媒体舆论具有传播无界、即时互动、隐蔽难控等特点,它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权和知情权,在风险事件发生及处理过程中,网络舆论易起到干扰和鼓动的作用,具有分散处理风险事件注意力的“干扰器”的负作用。教育工作涉及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任何地方的教育改革举措通过网络都能很快地传递给大众,对于负面的新闻人们尤其关注,并且加上自己的理解,由于缺乏专业的知识和良好的判断力,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或者是批判。如2008年江苏省高考改革,在网络上搜索关于这次改革的问题,能获取到大约2万条信息,其中大部分是批评性评价。在5.12地震的时候第一个先跑了而不管学生,被称为范跑跑的某名牌大学毕业的教师范美忠,就招致了大部分网友的批判,发表了《范跑跑是豆腐渣教师》、《范跑跑挑战国民容忍度,引发道德大批判》等评论。因此,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的传播迅速和影响范围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大教育改革的风险。
(三)“潜”风险——民众对风险的敏感度增强
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玛丽·道格拉斯(M.Douglas)等认为,在当代社会,风险其实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仅仅是被人们察觉、意识到的风险增多了,这是人们认识能力提高的表现。大众借助媒体报道与舆论形成判断感知风险,当传播的风险信息失衡造成舆论严重偏向,就会大大超出公众对风险及其预期的感知承受力,导致公众对灾难和危机的认同先于感知发生了。这种混杂着风险想象、风险猜测的情绪可能被那种不可控感所操纵、加剧,演变成更加严峻的心理危机和社会危机。就我国的教育改革而言,随着信息传递的迅速与便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获取大量与教育改革息息相关的信息,促使人们对改革的关注度增强,特别是直接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以当风险来临时,人们会很快的觉察到,这样对于教育改革的要求就更加严格,同样也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和风险。〔5〕
三、教育改革风险规避的策略探讨
如前所述,尽管教育改革的风险不可避免,但基于风险传播理论的相关认识,仍然可以采取一定的策略或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小风险,进而促进和保障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
风险传播理论认为,规避风险的首要策略是营造制度理性的风险文化氛围。制度理性即制度的均衡状态,是以社会理性为基础,从对社会使命负责的视角,对社会规范本质的、整体的和内部联系的概括反应,表现出对某种社会秩序和规则实现的诉求。教育改革风险防范的根本要求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制度的规范性对于教育改革风险防范目标的实现起到稳定和保障的作用。由于风险社会中的教育改革风险主要是改革决策所导致的未曾预料的副效应,所以要从制度理性的角度强调决策中的风险伦理和责任伦理,引导人们把风险意识作为日常生活和职业实践的一部分,保持反思性。当前专家决策中伦理问题被忽视或边缘化,在风险文化的氛围内人们都会自觉地考虑如何控制将来发生的事情,同时提醒专家或者制定政策的人能够对自己的决策做到自省、反思和质疑,唤醒和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
其次,风险传播理论在风险的规避策略上十分强调决策制度的完善、问责制度的高效以及有效舆情调控的落实与实施。在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中,要使教育改革决策者的责任具体化、透明化,并承担决策不当带来的风险,建立权责相关的风险分配机制,避免以离职转岗等方式摆脱决策者理应承担的风险责任,纵容他们的不负责任。在教育问责中,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进一步明晰各自的职责和职能分工,建立科学的责任分担体系和责任追究机制,避免“舆论失效”;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公众听证制度,保证教育政策相关利益群体了解和参与决策过程,避免“诉求失效”。同时还要进一步提高政策设计的有效性、科学性,积极构建社会主流舆论,排除各种因素干扰,实现社会活动的积极价值导向,构筑舆论安全。
此外,风险传播理论将以人为本作为规避风险的重要指导思想,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只有秉承这一思想才能使其和谐发展。教育改革的和谐发展大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之间的和谐。即教育改革的发展应与一定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科技等社会改革协调一致,彼此促进,避免出现“此起彼伏”的现象。二是教育领域内各组成部分的和谐。如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协调发展,缩小其自然的、人为的差距。
教育改革是一项发生在教育领域的人为行动,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发展,最终将带来社会的发展。一个以公正为价值取向的教育改革应该给予社会处境较差、较弱的个体或群体以更多的资源与利益,这既是对受教育权的尊重,也是对教育起点公平的承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这项改革是基本成功的。所以,当风险成为整体社会背景时,更强调社会个体参与集体性决策的能力与判断力,切实帮助那些由于诸种原因而处于弱势、无法参与的人,这无疑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1〕〔美〕格雷姆·萨拉曼,戴维·阿施.战略与能力——持续的组织变革〔M〕.锁箭,等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36.
〔2〕谈松华,谢维和.教育改革与制度创新研究〔J〕.教育研究,2010(7).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4.
〔4〕张涛甫.作为一种“软”风险的舆论风险〔DB/OL〕.http://news.fudan.edu.cn/2009/1009/22444.html.
〔5〕余秀兰.教育改革的风险及其防范〔J〕.教育发展研究,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