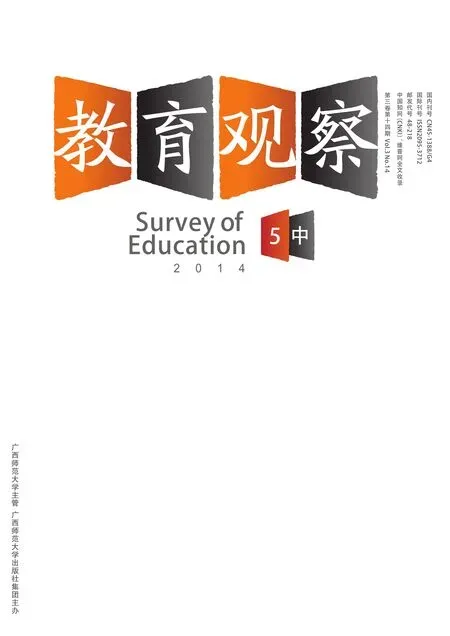夏昆:窗边的守望者
谢 云
(绵阳市涪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四川绵阳,621000)
夏昆是我师弟。这话没别的含义,只是事实陈述:大学时,我们同在狮子山,同读中文系,只是他低我一届。一届近200人,我们原本不认识,后来不小心认识了,交往也不多——系上有个“影评协会”,与市里几家电影院有联系,可免费看电影。为这种“午餐”,我在协会里混过。他成“会长”后,我们伙同看过些电影,为了完成任务,也写过些影评,有一两篇,自己满意,他也觉得不错。但仅此而已。
然后,我毕业,他大四,交情原本不深,所以我们似乎不曾告别。
当时,朋友老瞿在我留言本上写过一句话:“很多时候,我都看到,朋友转身,也就是死了。”老瞿一向被称为“女巫”。她这句话,就很“女巫”:青春不会永远,友谊也难——朋友都一段一段的,很多时候,转身就像不喜欢读书的人翻书:上页翻过,下页不知从何开始。倘若“挥手自兹去”后,星汉遥隔,时空遥距,彼此的生活再没有交集和碰撞,那么除了曾经的记忆和遗物,差不多“也就是死了”——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很多只生活在“过去时态”的朋友,就这样一点点“死”掉,连挣扎也没有。
照理,夏昆会“死”得更快、更彻底的,当时那点可怜的交往,就像一壶寡淡的酒,哪禁得起岁月的挥发和蒸发?但是他,居然成了例外——睽隔多年,他又卷土重来,出现在我生命的江湖里,像一个“死而复生”的传说。
“5.12”地震前夕,我久不去的新浪博客里,出现一张“纸条”。来者坦然标明身份和姓名,说是大学旧友——那张纸条,成了岁月的还原剂,记忆的显影液。我立刻想起20多年前的那个家伙:瘦长,眼镜儿,依稀的长相和印象,斑驳的岁月和记忆。遗憾的是,按他留下的方式,一直没联系上。几次电话,他似乎都不在。然后,是惊心动魄的地震,紧张兮兮的生活。那些刚沉渣泛起的记忆,又暂时被搁置,沉淀在平静的水底。
但我已从网上知道,那个叫夏昆的故人,已化名“摩西”(与《圣经》“十诫”有无关联,一直没有考证),而他工作的地点,距我,不过一小时多车程。
2008年10月,在南昌得见张文质先生,通过多喝两杯啤酒、外加套近乎的方式,“巧取豪夺”到一本心仪已久的《明日教育论坛》。那期刊物上,正好有摩西的行踪——他的长文《一意孤行》,细述毕业后的教育流年,其间种种经历,看得人感叹连连,唏嘘不已。这让我痛下决心,哪怕他化名本·拉登,也要把他彻底揪出来。
巧的是,南昌回来,落草“一加一”,居然在那里发现他的行踪,而且是真名示人。“确定肯定以及一定”后,是互联网方式的“勾结”——电话,短信,QQ,那个人和那段岁月,便“复活”得栩栩如生。接下来,我们曾有机会重逢,却被我因公务一再错过。重逢的约会,只好一拖再拖,尽管彼此的喉咙、肠胃,早被预计中的话和酒,给勾引得蠢蠢蠕动。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我再次深表遗憾时,他在QQ里说,明天就过来,我说非常OK。第二天出发前,他在QQ里丢下一个网址,点开,《关于我和那把刀》——仿佛,他是怕我淡忘了往事和交情,并因这淡忘而将对他的绵阳之行有所怠慢,所以预先对过去的岁月和交往,作了回顾和提醒。或者,他是要我用这些文字和记忆,预先温酒,或暖心?
一个半小时后,他开着那辆七成旧的二手弗乐尔,慢慢奔驰过来;我根据车牌号和他说的“最破、最脏”的标准,作出不标准的交警手示,指挥他停车。然后,就看到他的光辉形象——粗壮的块头,茂密的胡子,宽阔的额头,长而乱的头发,极其陌生的脸孔和人——实在说,要不是照片里已有“间接经验”,把他放大街上走,我顶多想起腾格尔的模仿秀,绝不会把他和自己、和那段青葱岁月联系在一起。他想“复活”,怕也是痴心妄想。
酒,话,夜色,酒话,歌声。12月27日,从下午三点到深夜的那段时光,为行将结束的多灾多难的2008年,抹上了一道亮色——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虽然尼采宣布过“上帝死了”,但他没宣布过摩西死了,所以摩西来了,带着这道亮光——当然,他也带来一张并不熟悉的脸,一道模糊的身影,一个依稀的故人,一份遥远的亲切。他让那个叫夏昆的人,借助这道亮光,“复活”在我的生命里,在他“假死”近20年后。
更为重要的是,顺着这道亮光,在绵缠的酒意和唠叨的叙旧里,我更深切地了解到他的“假死”经历——这个据说跟我当初一样“桀骜不驯”的家伙,大学毕业后,也跟我一样,被发配到偏远的地方教书,先是峨眉的一个小镇上,后是西昌的一所子弟校。《围城》里,钱钟书说方鸿渐到三闾大学时,曾引用西方某古国的一个说法:“这个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像他和我这样的教书,真是不折不扣的“假死”了。难怪,在那么漫长的20多年时光里,我们会长久“失联”。
在西昌铁中,夏昆才真正“走入教育”。那时,他教龄已满5年。不过,他所“走入”的,只是“竞争白热化的应试教育的修罗场”——带着最烂的班,面对最酷烈的竞争,他不得不关注考试,关注分数。以我的经历,为“考试”而教,实在不算太难,所以,聪明的他,一举成名——虽天下不知,但全校有份儿。
但是,他显然知道,成绩并非教育的全部,分数更非教育的唯一。“短暂的成就感”后,他陷入“深深的迷茫”,还有孤独。为排解这迷茫和孤独,他在继续钻研考试的同时,开始了真正的阅读生涯——听取一位长者的建议,从《二十四史》开始,他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作了一次看似毫无意义,实则别有深意的溯游和梳理。他后来对唐诗、宋词的研读,包括《唐诗的江山》出版,应当与此番阅读经历有关。
但一个鲜活、旺盛、有创造力的生命,显然不能只有历史这样一个出口,就像一盘棋要活,不能只有一只“眼”,一口“气”。他开始在网络里出没,在BBS和聊天室里,像游魂一样飘荡,“学着发帖、跟帖,学着吵架骂人,学着呼朋唤友”。那段网络游侠的生活,让他对自己从事的所谓的“教育”,有了持续的疑惑和初步的思考。
促使他更深入思考的,是一个女孩的鲜活生命。在他带的2001级班上,有个叫可可的可爱女孩,她一直非常努力,非常刻苦,也非常在意自己的成绩。但是,因为高考失利,她服毒自尽了。我的师弟,那个满脸络腮胡的夏昆“在所有的人面前痛哭失声”——
后来,有同事劝我:“可可是回来之后自杀的,不是在你教她的时候自杀的,你没有什么责任。”我说:“当她为了成绩而哭泣的时候,我把她当作全班的榜样,当她过分看重分数的时候,我认为她可以成为一个极好的范例来教训学生,我是有罪的。”这时,我想起一个朋友的文章里的一句话:“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我们,都是有罪的。”
“我们,都是有罪的”——这话,说得多么沉痛,多么悲壮,多么真诚。很多时候,在荣誉面前,我们似乎都愿意自己能够“与之有染”,但在责任和负担面前,在痛苦和耻辱面前,我们都巴不得它与自己“毫不相干”。我们甚至可以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平庸的恶”开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非情愿,迫不得已;上级的命令,我必须服从,领导的要求,我必须落实,早已拟定的“规划图”,我必须执行……
但,真是这样的吗?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疑惑和沉痛,他写了那篇随笔:《我不愿意做这样的老师》,我在编一份区域教育内部资料时,曾专门推荐过——其实,他所不愿意的,他所拒绝和反抗的,不过就是很多人一直做着的“反教育”“反常识”的事情,而他所愿意坚持的,不过就是回到人性、回到常识,回到一个教育人的本分。“虽然很多时候,我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去做这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我想,即使我不能完全抗拒,但是,只要我和我的朋友们曾经这样做过,哪怕几次,中国的教育也许会有更民主、更科学、更光明的未来。”他说。
同样是基于这沉痛和迷茫,他改变了自己的工作环境:放弃公办教师身份,放弃既得的利益和声名,他从西昌“出走”到成都,又从成都“出走”到新都。用他的话说,他与体制作了彻底的“了断”,他带着自己的痛苦和梦想,“私奔”了。
他或许并不知道,走到哪里,都是走在教育的梦魇里。就像贾平凹说的“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套用我的“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的说法,他的每一次“出走”,其实都是基于对内心安顿的渴求,但是,每次“出走”后,他都不得不面对悲观而悲惨的现实——在教育并不景气的背景下,哪怕他像“假行僧”一样,不断东奔西走,也难以找到教育人所期望的“世外桃源”。
逃无可逃,无须再逃,就像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他干脆继续坚持“一意孤行”,继续坚持“率性教书”(他后来以此为题,出过一本书)——痛感于“愤然者开始失望直至绝望,苟活者开始顺服并且屈从,逍遥者开始怀疑然后放弃”的现状,他选择了坚持讲台,再不退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做一个“窗户前的守望者”——除主课语文外,他为学生开设了“诗词鉴赏”“音乐鉴赏”“电影欣赏”,他期望通过自己所谓的“国子监四门博士”的努力,给学生打开除教材知识外的更多“窗户”。
他的“诗词鉴赏”,源于一个美丽的“错误”:课前五分钟演讲时,有个学生讲了孟郊的《游子吟》,学生用雷鸣般的掌声作为回报。他突发奇想,能否把自由演讲,改为主题式的诗词鉴赏?他尝试着改变,结果出乎预料:“就是那些平常看来最不起眼的孩子,都能在诗词鉴赏中给我、给大家以惊喜。”就这样,一次次鉴赏下去,一届届鉴赏下去,古诗词、现代诗、歌词、电影音乐、精彩文章,都成了鉴赏对象。鉴赏成了美好的分享和交流。
他说,刚开始的想法很功利,就想学生多接触诗歌,为高考作准备,但是渐渐地,想法改变了:“人生如果有美的东西相伴,不管这美的是音乐还是诗歌,是绘画还是舞蹈,那么,人生都会因此而更精彩。当毕业以后,学生回忆高中生活时,能够想起那么多美丽和温馨的瞬间,那就是教师最大的成功。”
他的梦想,不是教育,而是音乐。遗憾的是,他只能教语文,庆幸的是,他能以语文教师的身份,给孩子们做音乐鉴赏——他从自己熟悉的摇滚开始,引领学生慢慢回溯经典。他给孩子们赏鉴的音乐,包括《梁祝》《春江花月夜》《动物狂欢节》《天鹅湖》《胡桃夹子》《1812序曲》,以及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合唱》等。用他的说法,这“只是在学生紧张繁忙的学习生活的空隙中见缝插针的一个启蒙”。
见缝插针——我想起我曾说过的:“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发展,必须坚持,哪怕生存的环境再逼仄,哪怕现实的土壤再板结,也总有空间可以让我们见缝插针。”
他为学生做的电影欣赏,以“爱:永恒的主题”“艺术惊鸿”“艰难时世”“另眼看教育”“自由与救赎”“尊严”等主题,引领学生先后欣赏了《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海上钢琴师》《活着》《死亡诗社》《勇敢的心》《肖申克的救赎》等优秀电影……
从1998年开始,他开设的这三门课,坚持了15年。“我教过的数百名学生,都同样受过了这诗词、音乐和电影的三重洗礼。”更重要的是,“我的选修课不但没有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反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激发了他们学习的兴趣,大部分学生成绩还稳步提高”。
现在看,这三门课其实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课堂——随着“窗户”渐次推开,学生的世界得到拓展,体验得到丰富,精神境界更加敞阔,他的课堂气象也更加浩大,辽远。正因如此,他在《教室里的电影院》出版后,又迅速结集了一本《语文课》。
“在一条没人走的路上,一意孤行……”这是他当年在“新思考网”的博客签名。在多年的执意行走和坚守后,他感叹:“不管环境如何恶劣,我们总还是能做点事情的。”因为这样的坚信,他说,“我明显感觉到坚冰的融动,虽然很慢,慢得也许我们根本无法在有生之年看到本质的改变,但是有融动总比一直铁板一块要好些吧。”
因为这种感觉,他始终站在命定的窗边,就像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