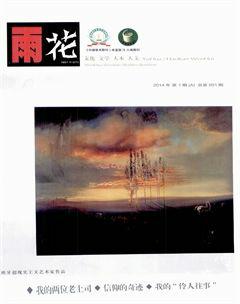高晓声卖画
●章辰霄
高晓声卖画
●章辰霄
高晓声和董欣宾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但他俩的形象仍时不时地闪现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他们留下的那300300多万字的作品和一万余幅书画,将长久地活在他们的朋友和读者的心中。
高晓声“卖字”,世人皆知,且十分的成功。1978年底复出后,他曾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一口气出了七本小说集。他笔下的“陈奂生”成为新时期文学画廊中最具光彩的典型之一。权威评论家认为,高晓声是继鲁迅和赵树理之后,又一个为中国农民画灵魂的高手。但高晓声在主业之外曾“客串”卖画,知道此事的人不多。事情还得从他和画家董欣宾的交往说起。
两个人虽说都在南京,但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画家,是行驶在两股道上的“车”。风云际会,1985年的某一天,两“车”相遇了——
那天,董欣宾和另一位画家朋友到常州来寻高晓声求助。董欣宾说,他们在南京已想尽了办法,现在唯有你高老师能帮这个忙了,以让姚迁能在阴间瞑目。姚迁生前是南京博物院院长。但他上吊了。起因是说他剽窃,随之而来就是遭到外界有组织的批判。姚迁带研究生,所以发表有关课题的论文中就有他的署名,还总摆在前面。这是一个既可说成“延安”亦可说成“西安”,既可说得清楚亦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事情。姚迁在全国文博界名头很响,行政级别亦很高,但生活中有的是更响和更高。姚迁申诉未果,“士可杀而不可辱”,终于做出了这个悲怆而壮美的选择。按我们多年来的思维定势,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死了不光白死,还要加倍地批判。
面对两个年轻人的企盼目光,高晓声的内心一定不平静。对于被冤,他的感受比谁都深。1957年,他才29岁,还未成家,在上级的“吹风”下,他与陆文夫、方之、叶至诚、陈椿年等几个志同道合者因筹办“探求者”文学社而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因为“探求者”的宣言和章程是高晓声起草的,他被打成“极右”,带着肺部8公分的空洞被开除公职发配回乡。“探求”18天,蒙难21年。在大灾之年的六十年代初,他有3个月每天只能吃到4两糠,亦在那个时候他老毛病复发,切掉了两叶肺。差一点就去见了阎王。
静水深流,乍暖还寒,高晓声面临艰难的抉择。最终,他还是听从了灵魂的召唤,毅然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他也要找朋友帮忙。这位朋友就是著名学者、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王教授告诉高晓声,碰巧中央权威媒体的一位主任在上海,他马上去找。就这样,“姚案”终于捅破了天,震惊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批示彻查,有关高官因之而落马。
对这样一桩义举,高晓声十分地低调。高晓声曾应董欣宾所邀,为1986年8月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欣宾画集》作序。在序中,他讲了与董欣宾的交往。“我同董欣宾的认识,是他做了一件使我难以忘却的事情。我有一位颇可信任的同志(应该说是知己朋友),遭受到严重的冤屈,我对此事知道大概,却未过问。仔细考查自己的灵魂,是出于两怕,一怕麻烦,二怕得罪人,但据此便置朋友于不顾,当然说不过去,因此尽量想把朋友受的冤屈看得轻些(毋用紧张),再把自己受过的冤屈尽量看得重些(不是也过来了吗),来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平静。这时候却来了个董欣宾,他同我素不相识,同我那位朋友也只是泛泛之交。可是他知道我同我的朋友相知,跑来把实情告诉我,向我进了一言。这一言使我无可再遮掩,才做了些勉强对得起朋友的事。只此一点,便可以看出自家灵魂上蒙的灰尘有多厚,欣宾则明显地比我负担轻得多。”从序文中,高晓声对自己灵魂的自省与拷问,愈加显出他灵魂的高洁与不凡。
疾风知劲草,危难见真情。自此,高晓声与比他年轻12岁的董欣宾结为莫逆。
董欣宾是中国画坛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无锡人,画作署名“张泾人董欣宾”。他自幼跟随画坛老前辈秦古柳学画。1959年他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附中国画班。中学毕业他投笔从戎到山东。在只能读“四卷书”的年代,他迷上中西方古典哲学,一头扎进《易经》、《内经》、《孙子兵法》……为此他被遣送到连云港花果山“劳动改造”,砍树、挖坑道、扛大包。1968年复员到南京新华印刷厂搞胶版印刷,两年后转到连云港新海印刷厂搞设计,不久,他又在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干起了中医的行当。1979年,他考进了南艺,成为刘海粟大师暮年唯一的山水画研究生。刘海粟先生在给南艺领导的信中称赞:“董欣宾能诗,知医,画也不错,前途无量也。”毕业后,董欣宾入江苏省国画院,任理论研究室主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在画坛上刮起了第一阵龙卷风。他独具功力又变幻莫测的墨线艺术被誉为“南线”的代表。同时,他在艺术理论研究领域亦有杰出的建树。他曾闭门7年,与学生郑奇潜心著述,出版了《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中国绘画六法生态论》、《太阳的魔语——人类文化生态学导论》等长篇巨著,是中国画学科性建设的开创之作。他曾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评为1992年世界杰出人物,同时被选为国际杰出人物协会委员。他还是一位武林高手,曾与东西南北的多位武术高人过招过。
董欣宾是个不易读懂的人。他特立独行,狂傲不羁,是个艺术苦行僧。“我不搞名利人生,我有很丰富的艺术人生。”在官场,在艺坛,他也与人过了不少招,陈丹燕说过,董欣宾是画坛上少有的文化斗士。他虽然清贫,却十分好客,所以陋室里常是高朋满座,大多是他的学生。当他得知高晓声的大女儿要去日本留学时,他把家里所有的日元都给了高蜡英,“这是董叔叔赞助你的”——当然,待女儿在日本成功创业后,高晓声马上叫高蜡英还了这笔钱。
高晓声对守着金山过苦日子的董欣宾十分地不解,他跟我议过:董欣宾这么穷,还要充“大佬倌”,不肯卖画;非但不卖,甚至还反收购昔日送人的、现在被画店“低价”挂售的自己的画,是不是画家们都有这种“病”呀?我说董欣宾在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他说过,把中国文化贱卖是一种可耻,中国画应该和油画有一样的价格。
对苦日子有着切肤之痛的高晓声终于干涉起董欣宾的生活了。他要帮他卖画,做他的义务“经纪人”。也许是碍于亦师亦友这种关系,也许是不好意思“驳”大作家的面子,桀骜不驯的董欣宾居然接受了高晓声的安排。董欣宾在高家一连画了六天,其中头四天是一直蹲着,把宣纸摊在水泥地上画的。他说,他的蹲功是在学生时代练就的。第五天,高晓声才在床底下找来张钓鱼用的小折凳,让他坐着画。
高晓声的“宏图大志”是要以每幅100元的价钱为董欣宾卖100幅画。这样,他就造就了一个“万元户”;他意向中的买主就是改革春风下“发”起来的“陈奂生”们,他们再也不是“漏斗户主”了,经过“承包”、“转业”、“上城”、“出国”,已经“发”起来了,该有新追求了。
高晓声踌躇满志,志在必得。高晓声对自己在1947年进上海法学院读书就选择经济学系一向都十分的自得。可这次高晓声失算了,面子丢大了,用当下的一句时髦话说,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是颗粒无收。更有甚者,竟说书店里卖的年画,五颜六色的,也比这画在宣纸上的黑不溜秋的水墨画好看,而且只要角把钱一张。董欣宾很大度,从不过问高晓声的销售业绩,就当没有这码事。这些画,至少有部分的画,后来被高晓声当礼品送朋友了。我就帮他送过两幅:一幅给李怀中,一幅给宜兴紫砂二厂厂长,现在的宜兴紫砂协会会长史俊棠。1988年2月,高晓声曾应密歇根大学联合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去巡回讲学,他送给负责接待他的梅仪慈教授的礼品也是董欣宾的画。
说起那次卖画,倒是让我捡了个“元宝”。那年,我服务了一辈子的常州拖拉机厂的一幢四层办公大楼落成,常州书画院阙长山院长为单位的生存与发展,曾屈尊上门联系为大楼作书画布置。因为我跟长山相熟,所以厂长就安排由我接待和负责此事。恰在这时,董欣宾来常州看高晓声了,真是鱼来网凑,我就请两位来厂作客并顺势向董欣宾提出,能否为我们的贵宾室留幅压轴之作。他不好意思拒绝,终于答应了。
当天下午,董欣宾就开始在高家的水泥地上泼墨挥毫了,画面是他最熟悉的太湖。想当年,他就凭着一幅长达2丈的《太湖全景图》,打动负责招生的著名画家叶浅予之子叶善禄的心,考进南艺附中的。此画他同时画了两幅,落款也一样:“太湖舟影晨雾浓,渔歌破晓清入云。乙丑年画于常州桃园新村无锡张泾人董欣宾。”画,一幅交我,一幅就抵了“饭钱”;此画曾在高晓声的卧室里挂了好几年。我送此画去书画院时对长山说,此画就算我替你组稿,你从布置费中给点稿费吧。长山问我数目,我说就给300元吧;你们去付,我付他不一定会收。两三个月之后,我曾随车去取回画,谁知接待室主任独爱那些外单位送来的闪闪发亮的贝雕工艺品,而把我带回的当时常州名头最响的四位老先生的作品连同拖把、笤帚一道长期搁置于储藏室,任其受潮和发霉。那才是真正的斯文扫地呀。
再后来,办公室已盛行挂岗位责任制,墙上已容不下这些纯艺术的东西了,书画一事从此作罢。后来我就去了书画院,把300元钱放到长山院长面前。我说,免得瓜田李下说不清楚,现在我退你钱,你还我画;就这样,《太湖渔歌图》收入了我的囊中。本想为企业作点贡献,到头来却“肥”了自己,真是世事难料啊——难料的事还有呐,当年我向董欣宾求画时所极尽炫耀的国家级“双金牌”企业,十年后居然跌落进尘埃,被浙江的一家为我厂做链条配套件的老板“负资产”收购,那位“末代厂长”也终于把自己“玩”进了班房。我想《太湖渔歌图》为我所藏也许是命里注定,是最好归宿。既是我之所幸,亦是画之所幸。
在2001年,无锡有位周姓画商曾数次来常州搜集董欣宾的字画,只要是真迹,最低收购价5000元一幅。他对《太湖渔歌图》的开价是15000元。我笑笑说,朋友的画是拿来看的,不是拿来卖的。
据今年3月《现代快报》独家发布的江苏艺术家指数,董欣宾作品当前均价为每平方尺41466元,总拍品322件,成交比率50.4%,成交价纪录是2006年北京翰海拍出的汉鼎白梅镜心,55万元成交。对此画价,我想作者生前也许会料到也许会料不到,但我敢肯定高晓声是无论如何也料不到的,他若泉下有知,他一定会后悔当年怎么就这样“贱卖”了骄傲的董欣宾;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穷困潦倒了大半辈子的高晓声眼中,100元一幅已经是在“印钞票”了。他吭哧吭哧地(晚年他写作时常要停下来吸氧)写了数年的,他的第二个长篇《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在1991年出版时才卖了3800元钱。记得在1994年的春天,他曾不无感慨地对我说,前不久他到苏州陆文夫那里去,“老陆对我说,老高,看来我们是学错生意了,应该学书画。”那次,高晓声还从南京带来两幅字。一幅给他的侄子小明,“艰苦创业乐在其中”,他侄子正在办厂;送我的一幅是“乐在其中”,他说,挂在你的书房里还是蛮合适的。相识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写字送人,尽管他在“探求者”诸同人中学历最高字写得最好。所以,我当时跟他开过玩笑,我说,看来你准备改行啦,不过觉悟得有点晚。
高晓声生命的脚步止于1999年7月6日,他没能跨进新世纪,离开他71周岁生日还有2天。他发病的起因是5月底南京上空那场莫名其妙的“怪雾”,中央电视台都有报道。当然,现在它已有了正式的名字,叫“雾霾”,叫“PM2.5”。高晓声那半拉子肺对“怪雾”特别敏感,当天就被折腾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他还是跟以往一样,以老经验对付老毛病,那就是,我惹不起但我躲得起。所以他在医院里只住了一天,就连夜叫机关的车把他送到他所熟悉的坐落在太湖边上兰州铁路局的疗养院。以往犯病,他在这里住上几天,呼吸呼吸湖边上的新鲜空气,气就慢慢地会顺起来的。但这次他失算了,而且是被新账老账一起结。6月9日夜里他病情开始恶化,他被送进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在随后的二十多天里,虽经南京无锡等地专家教授的多次会诊,终因肺性脑病,最后,晓声仍归于无声。他是带着深深的痛苦和遗憾走的。他到死,都不肯放下手中的笔。他的同乡挚友唐炳良从南京赶到无锡去看他时,他已无法开口,他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两个字:“很苦”。
在高晓声走后的第3个年头,他的这位画家挚友,由于长期的超负荷的精神和肉体承载,终于演化成躯体的裂变,铸成了他的悲情人生。董欣宾也是肺上出的毛病,于2002年10月15日在上海长征医院逝世。董欣宾才63岁呀。在世道安定,医学先进的今天,这个年纪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正如我国著名的美术评论家李小山在董欣宾死后的第二天所写的悼文《他仍然活着》中所说:“他那么充满生命力,充满激情和才华,在我的经历中,没有遇到比他更神奇更令人敬重的人。”“老董是当代中国画坛最棒的画家,他是他的同代人中最杰出的,他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也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然而,时间将会证明,用北岛的名言说,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老董的才华体现在各个方面,他是画家,是理论家,还是思想超前的先行者,他的消失只能说天妒英才,天妒英才啊!”
高晓声和董欣宾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但他俩的形象仍时不时地闪现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他们留下的那300多万字的作品和一万余幅书画,将长久地活在他们的朋友和读者的心中。